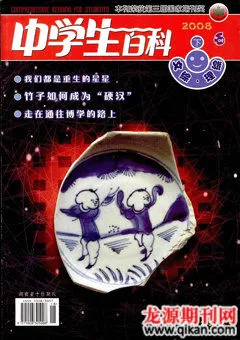乞討權算人權嗎
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討論——乞討權算不算人權?有些人不假思索地提到:乞討是一個人的權利。他們說這話時,似乎是在天經地義地描述一個絕對真理。但實際上,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沒有一條提到人有乞討權。
中國對于人權的定義是這樣的: “所謂人權,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所謂人權,就其完整的意義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或者說,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權利。”
人權的第一要素是“每個人”。以乞討為生,實際就是不勞而獲。如果將乞討視為人權之一,無疑就是認可每個人都有不勞而獲的權利。這個權利如果普遍化,整個社會乃至人類和世界還能生存嗎?因此,不能人人都行使的、不能普遍化的“乞討權”,也就不能成為基本的人權。
人權的另一個要素是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以乞討為生,某種程度上就是以放棄個人尊嚴為代價,換取不勞而獲的好處。一個放棄自己尊嚴的人,至少在放棄尊嚴的這個行為過程中,就不該獲得完整的人權保護。而在乞討行為中,乞丐的尊嚴不是他人剝奪的,是他自己自愿放棄的。如果承認乞討權屬于人權,就等于允許正常人自甘墮落。
人權還有一個要素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實施乞討行為就是,只享有自由而放棄平等。正常人都會反抗一種常見的不平等,就是少數人比多數人高出一等,少數人享受更多的權利,從而剝奪了大多數人的某些權利。而乞討行為正好相反:乞丐自愿比常人低一等,從而使少數人“強加”給大多數人某種義務,這種義務就是同情和施舍。換句話說,乞討行為也可以視為利用自己的悲慘、可憐,對正常人的善良和同情心實施要挾,向社會的良心實施要挾。也正是由于乞丐自愿放低身段的行為,使得正常人難以產生反抗這種不平等的念頭。但是,面對乞丐,正常人不管是出于同情還是出于無奈。確實多負擔了一份額外的義務。
所以說,乞討權不能成為人的基本權利。
2000多年前,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宰相管仲曾經說過:在我的管理范圍內如果有人乞討,是我做宰相的失職(原話懶得查了)。按照管仲的這個觀點,今天我們可以說,如果承認“乞討權”,就等于政府在逃避應有的責任。大千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各自遭遇和能力不盡相同,難免會產生有些人無法自我保障最起碼的生活水平的情況。面對這種現象,作為社會的管理者,不應該以贈送“乞討權”的方式,逃避自己的責任。
舉一個相關的例子。父母收入低微,無力承擔孩子上學的費用,父母有沒有權利不讓孩子上學?現在的法律已經明確規定,任何人都沒有這個權利。我們為什么沒有把“不讓孩子上學”視為人權的一部分?因為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就是免費的義務教育,而不足允許這些孩子去做童工,幫助家里減輕負擔。同樣,如果有人確實生活困難,就不應該用允許乞討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是應該增加社會保障。
當然,在不太富裕的社會,社會保障可能難以覆蓋全體人群,乞討現象難免會發生,因此,在理論上否定“乞討權屬于人權”之后,還應該有一些階段性的應對措施。這種應對措施最重要的內容是,區分真實乞丐和行騙乞丐。對于真實乞丐實行有條件地、階段性地允許,對于行騙乞丐堅決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取締。
現在都市里的人,大多都遇到過乞丐,也聽到過很多假乞丐靠乞討發財的故事。但是,我們如何才能區分?當我們面對一個具體的乞丐的時候,給還是不給,確實煎熬著我們的良心,也拷問著社會的誠信。那么我們有什么方法能將他們區分開?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最著名的乞丐名叫武訓。武訓從20歲開始以乞討為生,到他死去的時候,他的財產是2所學校和1000多畝良田。武訓小時候隨母親乞討時到過河北,等他自己單獨乞討的時候,根本沒有出過山東,大致僅在現今魯西北幾個縣的范嗣之內。武訓因乞討辦學被清朝皇帝嘉獎之后,短暫地到過濟南,但是,他到濟南,主要是賣他自己做的兒童玩具。武訓在一個較小的地區范圍內就可以通過乞討獲得如此巨大的財富,可見,如果只是為了起碼的生活保障,乞討活動不用跨越幾千公里,在附近就可以。
總之,乞討不是一個人天經地義的權利,乞討行為能夠被接受的唯一理由是,一個人確實沒能力自己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時,政府的保障又沒能實現。如果一個人說他的生活水平必須不低于每月3萬元,而實際收入只有2萬8,差了2千元的缺口,所以他就有權利去乞討,那么,全社會所有月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人,只能把他當作一個天堂里的笑話。
編輯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