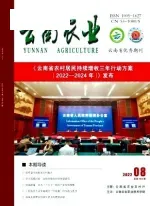不同藥劑對麗江雪桃縮葉病防治效果研究
習惠珍,馬桂明,汪朝陽,楊春震,和 巍
(麗江市植保植檢站,云南 麗江 674100)
麗江雪桃是近年開發出來的桃樹新品種,利用麗江市特有的優越自然條件、生態條件和氣候條件,選用一種玉龍雪山下獨有的山毛桃樹為砧木,經過多年精心優化培養出來的目前國內較為高檔的新型水果。但由于病蟲害的影響,尤其是雪桃縮葉病,嚴重制約了雪桃產量、品質的進一步提升。
雪桃縮葉病的病原物為畸形外囊菌,主要為害新梢及葉片,嚴重時也為害花、幼果。嫩葉剛伸出時就顯現卷曲狀,顏色發紅;葉片逐漸開展,卷曲及皺縮的程度隨之增加,致全葉呈波紋狀凹凸,嚴重時葉片完全變形;花和幼果受害后多數脫落,直接影響雪桃產量。為有效防治其危害,我們開展此組試驗,旨在通過試驗篩選出有效防治雪桃縮葉病的高效低毒的藥劑,供生產上使用。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
試驗選擇在玉龍縣具有代表性的雪桃重要生產基地拉市鄉海東行政村農戶木士光家的果園進行,試驗田所選果園面積約3333.3m2(5畝),土壤類型為紫色黏壤土,地形平整,土壤肥力上等,灌溉條件好。該桃園雪桃樹齡為6年,屬盛果樹齡。桃縮葉病發生較為嚴重,2010年調查桃樹的發病率均在5%以上。采用小區試驗的方法,各試驗小區的栽培條件(例如土壤類型為紫色黏土、肥料上等或中等、耕作精細)均一,而且與科學的農業實踐規范化栽培相一致。
1.2 試驗處理及藥劑
共設5個處理處理,A:70%丙森鋅800倍(安泰生)(德國拜耳公司);處理B:60%唑醚代森聯 (百泰)1500倍(德國巴斯夫公司);處理C:25%吡唑醚菌酯(凱潤)1500倍(德國巴斯夫公司);處理 D:75%百菌清500倍(山東大成農藥股份公司);處理E:空白對照(CK),清水噴霧。3次重復,共15個小區,隨機區間排列。每小區選擇2棵雪桃樹,并在邊行設2棵以上的雪桃果樹為保護行。處理區按設計濃度現場配藥噴霧,畝用水量75kg。整個試驗過程共施藥三次:4月15日調查在試驗田內出現少量病癥桃縮葉病發生時第一次施藥,隔10d4月25日施第二次藥,5月10日施第三次藥。
1.3 調查方法
每小區調查2株,每株按東、南、西、北、中固定5個點,每點調查20片葉片。每小區共調查200片葉,記錄是否發病。
藥前4月15日調查基數,藥后7d、14d和最后一次施藥(6月 24日)后的 30d(7月 24日)進行三次藥效調查,計算發病率和相對防效。計算公式:
式中:pt0——處理區藥前
Pt1——處理區藥后CK0——對照區藥前CK1——對照區藥后c.顯著性測定采用DTTR法
2結果與分析
調查統計以及應用生物統計方法計算分析試驗,結果附表 1、表 2、表 3、表 4。
1)藥前調查與藥后調查結果相比較,各處理病情都有明顯變化,病情變幅0~88.5%。
2)方差分析結果區組間(重復間)F值差異不顯著,說明病害發生程度在試驗區內分布均勻,試驗結果正確可靠。

表1 麗江雪桃縮葉病藥前病情調查結果記錄統計

表2 雪桃縮葉病藥后病情調查結果記錄統計

表3 雪桃縮葉病病葉記錄統計

表4 雪桃縮葉病平均病葉F測驗方差分析

表5 雪桃縮葉病平均病葉新復極差測驗
3)各處理間新復極差測驗(t測驗)結果表明所有農藥品種的處理組合中處理A(70%丙森鋅800倍)、處理B(60%唑醚代森聯1500倍)、處理D(75%百菌清500倍)與對照比較病害發生程度差異均達到了顯著水平,說明這三種組配農藥品種對雪桃縮葉病有較好防治效果;而處理C(25%吡唑醚菌酯1500倍)與對照無差異,說明該藥劑品種對雪桃縮葉病無防治效果。
3結論與討論
本次試驗從安全性方面來說,各處理對作物無藥害,其生長正常,無明顯影響。試驗農藥70%丙森鋅800倍、60%唑醚代森聯1500倍、25%吡唑醚菌酯1500倍、75%百菌清500倍4個處理,對雪桃真菌性穿孔病、白粉病、褐腐病有明顯的防治效果,試驗區上述病害發病都較輕。
從防治效果來看,通過比較及新復極差測驗比較,60%唑醚代森聯(百泰)1500倍對雪桃縮葉病防治效果最好,達到88.5%,其次是70%丙森鋅800倍(安泰生)防治效果也達到79.2%,接近80%,在生產上可作為防治雪桃縮葉病的主要藥劑使用。而75%百菌清500倍雖然防治效果不及上述兩種藥劑(防效69.8%),但其優勢在于價格低廉,防治成本低,因此可作為輔助、輪換藥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