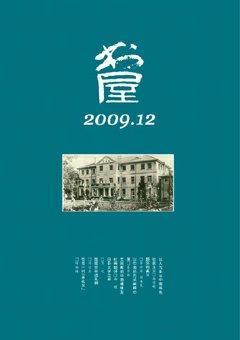以中國的方式闡釋中國
羅威廉(William T. Row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系主任,著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會共同體,1796—1895》、《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等。任美國《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 )雜志主編,美國《近代中國》(Modern China)和《城市史雜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編委。
姜異新(以下簡稱“姜”):作為一位生長在美國的中國史學家,二十幾年來,您一直孜孜不倦地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尤其是社會史學和城市史,收獲了厚實的成果,也產生了深遠的學術影響。促使您研究中國的動力是什么?
羅威廉(以下簡稱“羅”):1967年,當我從美國Wesleyan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專業畢業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到大學做一個英國文學教授。畢業后,我先到美國海軍部隊服兵役,做信息兵。在一次政府計劃中,我被派到菲律賓,在那里待了兩年,主要是在電臺工作,負責輪船之間還有與基地的信息溝通,這是我第一次踏上菲律賓的土地。在一個休息日,我向主管告假,去了趟農村。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水牛,我非常驚訝,在我學英國文學時的想象中,在我從紐約長大的經歷中,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動物,它使我對世界的看法和對自己生活的思考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使我不自覺地將所見到的與自己所處的社會時時進行比較。以前,我以為我生長的紐約,我在大學學習的英國文學就是全部的世界,現在我發現那只是一部分生活,還有一種我完全沒有經歷過的生活存在在這個世界上。之后,我決定回去就讀研究生院,并且打算從事東亞地方史的研究,這就是我走上中國史研究的最初原因。我最感興趣的是中國地方史。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國人無法到中國去。事實上,即便是在我于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1976—1980年間,美國的學者也無法到中國去。所以,在寫有關漢口的研究著作時,我根本無法去當地考察,只好到臺灣、日本、香港的圖書館,還有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查閱關于漢口外交的資料做研究,那里的資料的確非常詳盡。1980年春,我獲得了博士學位,在畢業之后的1980年12月和1981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我得到了可以到中國做研究的項目資助,我立刻就去了。首站是北京故宮,因為那里有關于明、清時期非常珍貴的資料。然后,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最想去的地方當然還是漢口。我的關于漢口的書,也是我的第一本書是1984年出版的,我寫的時候沒有機會去武漢,但修改的時候就抓住機會來到了武漢。截止目前,我共去了中國大陸八次,第一次只去了幾個星期,是在武漢大學;在研究麻城時,我主要去了華中師范大學。
就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喜歡中國文化,特別喜歡中餐。不過,什么事情都不是絕對的,我個人不喜歡中國音樂,對京劇也了解很少。盡管我很喜歡中國文化,但我走向中國史研究卻與此不相關,而是因為我發現這個領域非常有意思。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這個領域有那么多復雜的歷史事件在發生,這是很有吸引力的。在研究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學到了很多。
姜:2007年您的《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出版,目前還沒有中譯本,能否談談您為什么要把湖北麻城作為研究的對象呢?
羅:我的第一本書研究的是武漢這樣的大城市,但實際上,我最想研究的卻是農村社會。并且,我還很想去探索一個有許多暴力的地方。我擔心以前自己在著作中所描寫的清史畫面太寧靜、和平、美好,以致會把這個畫面延伸到整個大清王朝,實際上,在那個朝代,還有很多的人冒著生命的危險掙扎在生存底線上。所以,我把研究的焦點聚集在有更多暴力的地方,而麻城正是這樣一個區域。
當我在武漢做研究時,我第一次關注麻城,我發現有很多麻城人搬到漢口去。實際上,在十七世紀的明、清時代,由于連年征戰,四川人口大量的減少,大量麻城居民移民至四川。我讀過一本關于中國四川的書,那本書上說,自元朝開始,到明、清幾個朝代,都有麻城人口的流動現象,這是因為那里有很悠久的暴力傳統。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它屬于“鄂豫皖蘇區”,竟然是一個有七十年歷史的現代中國著名的革命圣地。生于湖北黃安的董必武,其一生就有很長時間是在麻城度過的,他是麻城初級師范學校的教師。黃安和麻城是毗鄰的縣,這些地方都是革命老區。喜歡研究地方史的我非常想知道:為什么中國一些特定的地區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暴力?為什么這些地方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的方式?當把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熔爐——“蘇區”置入一個長遠歷史視野去考察時,中國革命看起來將會有如何的不同?我想,麻城是個很合適作此研究的區域。2004年,我去麻城當地考察,但沒有待很長時間。麻城現在很富裕,很明顯,中國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來建設麻城,并保護好了當地的革命文物。由于漢語說得不是太好,我沒有采訪當地居民,尤其是一些經歷過革命的老人,這個比較遺憾。但我閱讀漢語的能力很好,我翻閱了從1530年到1997年七部麻城地方縣志,時間跨度很大。我希望通過對麻城從元末到抗戰爆發七個世紀間所進行的長時段考察,對中國農村社會歷史上的暴力現象提供一個宏觀的理解,并把中國革命與其所萌生的土壤聯系起來,追尋中國農村社會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姜:通過對麻城自元末到抗戰爆發七個世紀間所進行的長時段考察,您認為在麻城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方式的內在動因是什么?它反映出中國文化對暴力有什么獨特的認識?
羅:中國幅員遼闊,每一個地方有每一個地方的特點,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國。麻城并不比別的地方更能代表中國的暴力歷史,但麻城畢竟不是蘇州,不是西安,與其他地方相比還是有一點暴力代表性的,但我并不認為它是個典型案例。我想麻城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方式的內在動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個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大別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這座高山的要隘。清政府對麻城的戰略地位向來很關注,唯恐發生任何可能演變成大規模反清民變的騷亂。對于統一的中國來說,整個國家和平的話,麻城就會很和平。但如果發生戰爭的話,每支軍隊都想從那里經過,就會給麻城帶來動蕩。
第二個是政治文化。麻城歷史上存在很多有暴力傾向的強權人物,民間有紀念他們的傳統,迄今為止我不認為這種情況有多少改變。地方文化、集體記憶和當地歷史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麻城的一種暴力傳統。在當地民間傳說和歷史遺跡中,流傳著許多有關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志編撰者也為各自的政治目的,時而把其間的人物描繪為英雄人物,時而又把他們貶斥為盜賊土匪。
在研究中,我發現從元末到抗日戰爭爆發,麻城經歷了兩個繁榮時期。一是明代中期,外銷性農業的發展帶動了科舉和文化的成功;二是盛清時期,商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雖然兩個時期都遭受經常性暴力,但它們卻顯示了麻城權力的不同結構。在前一時期,中心和西南地區富裕的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地方士紳組成巨大的、相互通婚的宗族;在第二個時期,雖然大宗族仍然握有財產,但他們的權力受到受教育程度遠遜于己的地方強人的挑戰。這樣,大宗族逐漸成為地方社會組織中最重要之勢力,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初仍然如此。而十七世紀初持續的動亂,促使麻城當地精英為了自身安全高度武裝化,營造更大山寨,這種以山寨為中心的聚居地,成為麻城基層最重要的地方組織。該縣各地都有此類山寨,如東山地區形成了一個山寨聯盟,史稱“四十八寨”,但實際包含了數百山寨。這一類山寨在明末獲得了極大程度的自治,在清代才逐漸瓦解。
第三個是階級結構。從清朝中期開始到上世紀三十年代,麻城存在很多奴婢,這不只是相對于富人和窮人、地主和雇農的關系而言,而是指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很多地方存在著完全失去自由的人,這是由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的,為此麻城經常發生“奴變”。與全國其他縣相比,麻城佃仆數量最多,這一點到民國時期仍有體現。“奴變”是明清更替之際造成麻城血腥動蕩的主要原因,前后持續了二十余年。
姜:能否具體談談您在研究中發現的人們的歷史記憶有什么有趣的地方?那些不斷撰寫的地方志和其他文化記憶載體,如民間歌謠、傳說、地方戲、詩歌、武術和民間宗教傳統,還有各種歷史遺跡與遺址,它們共同建構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暴力文化?
羅:通過研究,我感到麻城的暴力傾向是為晚期中華帝國和民國的官員和文人所欣賞的。這種欣賞與大眾文化和大眾宗教相聯系,并與集體記憶、地方史的記載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麻城歷史上,有兩個特殊的暴力文化模式,一是崇尚英雄、武俠、好漢;二是對鬼神的敬畏。在《紅雨》里,我試圖通過分析歷史記憶,觀察一個事件是怎樣被記敘的,怎樣傳下來的,又怎樣為人們所解讀的。不同的記敘、傳播以及解讀反映了人們的政治目的和現實語境。
這里有一個我最喜歡的傳說,是關于張獻忠的。晚明的張獻忠叛亂,已為流行史學傳記所熟知,作為四川的屠戮者,他幾次大規模地血洗縣城,奪去了很多寶貴的生命。盡管,他那時致力于贏得大眾的認可支持,但肆意的血腥屠殺并沒有使他得到麻城歷史的關注,即便是最左翼的分子。當地有一個傳說,與紀念碑一起,后來被改編進了1993年縣志。在傳說中,張獻忠被描述成不僅非常具有同情心而且成為當地人的驕傲。據說,年輕的時候,張獻忠在四川販馬為生,他被盜賊綁去見官,審判他的陳法官是麻城本地人,他為張獻忠相面,斷定他將來能做大事,于是就把他放了。張獻忠發誓將來的某一天一定報答他,就問這位官員住在哪里。這時,官員一下子變得小心翼翼起來,神秘地回答,“在湖廣地帶,屋檐上掛著成捆的燈芯草,樹上掛著干草,沒有河流經過卻有兩座橋,這就是我所住的地方”。幾年后,張獻忠的軍隊占領了麻城。當看到那位官員當年說的懸掛著的成捆的燈芯草和干草時,張獻忠內心忽然充滿一種歉疚感,他下令建了一座墻和一個祭壇,并在此祭奠已經死去的陳官員。這座墻從此以祭奠墻而出名,直到1939年它還被地方充滿感情地持續關注著。當日本兵意識到它對當地居民的潛在激勵精神后,就把它給毀壞了。
還有就是麻城歷史上的“名吏”于成龍。這要從麻城歷史上的“東山民變”說起,從中可以看出生態和社會環境怎樣造就了一個地方的暴力行為。“東山民變”是十七世紀七十年代三藩之亂時以麻城為中心地區歷史上的一個插曲,說的是,一個名叫黃金龍的“妖人”多年來往返于各地山區,宣揚反清復明思想,試圖發動一場民變。1674年新年剛過,黃金龍便出現在麻城,揮舞“寶劍”,手持“天書”,宣稱自己通神。東山強權人物劉君孚將其庇護在自己的山寨中,該山寨位于麻城與黃岡縣交界的曹家河村。雖然他有時樂意庇護像黃金龍這樣的亡命之徒,但也會讓手下把一些進入其勢力范圍的匪徒押送報官,以獲官府信任。劉青黎是劉君孚的外甥,熱衷于參與反清活動,據說此人曾拜謁過吳三桂,有可能因此劉君孚獲得吳三桂的偽札,命其在東山起事響應。隨后,劉青黎利用當年四十八寨反抗的歷史鼓動并依靠黃金龍多年來建立的信眾網絡,有計劃性地尋求鄂東以及豫、皖、贛等省鄰近山寨強人的支持,宣稱這是“官逼民反”。由于劉君孚認為這有助于增強其權威,從而被外甥拉入反叛,據說他間接地控制了數萬人的武裝。關于劉君孚即將起事的傳聞四起,加劇了麻城社會內部的分裂:當地精英與縣衙官吏之間、效忠清廷與效忠明朝的士紳之間、縣城士紳與山寨強人之間、長期不和的山寨之間等等矛盾開始激化。起事計劃被另一山寨的仇家報官,劉君孚不得不倉促起事,而其他各寨主,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起事者,都率眾退入山寨。麻城的官吏在得知“東山民變”發生后,猶豫不決,竟在縣城坐等有可能發動的圍攻。
1674年仲夏麻城民變醞釀之時,湖北巡撫張朝珍將于成龍從鄂南召回以平息叛亂。于向各寨堡主發布一系列告示,保證不會派大軍圍剿。張朝珍接受于成龍的建議,宣布赦免悔過的士紳。在記述招撫5月劉君孚起事的官方文書中,于成龍幾乎沒有提及劉君孚的反對清政府行徑,以免妨礙對劉君孚等人的任用。他也沒有提及“妖人”黃金龍,更未提劉君孚助黃金龍潛逃,以免將劉君孚與三藩之亂聯系起來。但對于人數眾多的“叛仆”參與,于成龍要求奴仆忠于主人,嚴厲懲罰俘獲的叛仆。于成龍的新盟友劉君孚和其他地主武裝幫助鎮壓反叛,成千上萬的叛民及其家人被殺。雖然于成龍一再要求他們不要濫殺,但收效甚微。10月底于成龍抓住了黃金龍,為平亂劃上圓滿句號。于成龍將他問斬,砍下頭顱送武昌邀功。11月,于成龍在黃石鎮召集百姓,告諭民眾:“龜山已平,龍潭已清。既耕且織,萬世永寧。”
平定“東山民變”之功,成為日后對于成龍供奉祭祀的主因。從乾隆朝以降,于成龍的事跡就被列入方志,歷次編撰者不僅強調于成龍短期內平亂的謀略,而更頌揚其依靠當地民團挽救麻城,避免了朝廷對地方的重賦。為紀念于成龍對“東山民變”的理智處理,當地人修建了于公廟,還寫了大量關于他的詩歌,其事跡廣為流傳。正如1935年縣志編撰者所聲稱的那樣,于成龍深受民眾愛戴。然而,也有歷史編撰者認為1674年的英雄并非于成龍,而是堅持反清最終失敗的義軍領袖鮑世榮。盡管歷次精英所編寫的方志對他并不青睞,但其英勇反抗的傳說還是被傳頌下來,后來還被社會主義史學家重新定義為“農民起義”領袖。事實上鮑世榮出生麻城望族,很難被看做是農民。
就這樣,地方文化、集體記憶、歷史根源共同推動了這一地區的暴力傳統。不僅僅是于成龍這樣的官方人物,即便如鮑世榮那些反叛者也都被紀念,民歌、地方戲都為這一傳統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以來的歷屆政府官方史家、方志編撰者都不斷地強化這種暴力傳統,他們的歷史敘述和研究經常各有其目的,將歷史人物貼上各種英雄和盜匪之標簽。
姜:讀您這本書有很強烈的現場感,很多文學式描寫也很吸引人,對一般歷史愛好者也是很好的理解中國革命的讀物,能否談談您寫作這本書的方法?
羅:我的《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一書的大部分章節是在分析政策,只有第一章,是在講主人公的故事,后來,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忽然發現自己很喜歡這一章,讀起來很輕松,于是就決定在自己的下一本書里,一定要講故事。而我在閱讀有關史料時,發現麻城是個充滿精彩故事的地方,很自然的,我就開始講故事。或者說,《紅雨》是一本“敘事史”(narrative history),采用了編年史的方法,傾向于文學式描寫,而非科學性的分析。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特殊的人的經歷及其復雜性上,但我并不認為它是一本微觀的社會史,因為它研究的是一個時段,而且麻城的人口也有幾十萬。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以中國幅員之遼闊,麻城的確又只是一個小地方。所以,這本書也是一部地方史,用長時段的眼光可以同時揭示一個小地區的文化持續性與歷史演變、身份認同、城鄉關系、地方社區認同、對外部控制的抵制、霸權與受制系統、集體行為發動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的話語等。我很關注普通人們的生活,力圖理解他們的經歷,但不是撰寫“沒有事件的歷史”,而是對地方的重要事件進行了系統研究,從元末的紅巾軍、明末的白蓮教、清軍入關、清初的三藩之亂、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和捻軍起義,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國民革命、三十年代的國共內戰,均不曾遺漏。我希望這種努力能使讀者感受到中國歷史在“現場”的意義。
姜:在您這些大部頭的史學著作中,你最滿意的是哪一部?最近又在著手哪方面的研究?
羅:我最滿意的是《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個人以為這本書是我所有的學術著作當中最成功的一部。為了寫作這本書,我共花了十年時間,這本書的目的是書寫一個在西方入侵之前的清朝盛世。在我關于武漢的那本書里,我寫中國是如何抵抗西方入侵的。而實際上我對那個時代的政府中人思想些什么非常感興趣。比如,他們是怎樣看待他們所處的世界(universe)和社會,也就是指他們所存在的空間?他們怎樣認識這個世界和社會的潛力和局限?而他們這些人在“拯救世界”的努力中的能力和局限是什么?他們所理想的世界到底是何圖景?作為一個學者型的官員,陳宏謀的確是一個代表, 他代表了當時政府的態度,屬于“正統精英”(official elite),或者說,“官方精英”,也就是那些受過正統教育、而且關切治理國家(也可以說治理地方)的知識分子,而不在于他們是否擔任過官職。比如,像顧炎武那樣拒官不做的學者,還有曾短期任過下層官職但以詩聞世的袁枚,都屬于對治國之道很有見解的精英階層。陳宏謀不是典型的精英知識分子,他是很實際的學者型官員,是十八世紀清帝國最有影響的漢族官員。在1733年到1763年的整整三十年間,他歷任十余省的道臺、巡撫、總督等官職,其任巡撫時間之長,據稱整個清代無人可望其項背。
在中國,關于陳宏謀的研究成果不多,可以說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魏源編撰《皇朝經世文編》,收入陳氏著述達五十三篇之多,僅次于顧炎武的著述。陳并非獨創性的思想家,其從政生涯與其他同時代的干練才俊也并無迥然不同之處,但其精力和對其使命的理解卻是首屈一指的。陳宏謀是我研究大清帝國,研究十八世紀中國歷史的最好窗口。通過陳宏謀,我第一次關注大的研究客體,去觀察1725年至1775年間(即雍正乾隆時期)的“盛世”,了解造成這種盛世局面的因素,特別是探索正統精英的思想狀況。在研究中,我發現陳宏謀關于人和社會認識的基本點,與啟蒙時期的許多歐洲學者十分相似,他所涉及的主要方面,也是當時歐洲社會文化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如由于印刷技術發展而導致的文化程度的提高,社會生活中男女角色變化所引發的爭論,職業的復雜化、身份等級觀念的淡化以及社會流動的加快等等。從經濟方面來觀察,他與歐洲同道的相似則更為顯著,如陳贊賞地方經濟的貨幣化以及追逐利潤的動機。陳將耕地所有權作為經濟的基礎同時又明確支持“市場原則”,從而使他非常接近十八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在政治領域,陳非常強調行政的標準化、強調工作效率,這正是早期近代歐洲還在逐漸形成的觀念。集權的經濟控制、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都是早期近代歐洲精英意識發展的重要成果,但這種發展并非歐洲的專利,雖然清中期的正統精英并沒有把這些觀念發展到歐洲那樣的系統和圓滿,但足以證明,清帝國相對歐洲而言并非是“停滯的”和“落后的”。十八世紀的亞洲和西方交往日益增多,分別都在發展,如果這兩個世界在精英意識上毫無共同之處,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
目前我正在著手兩部書的寫作。第一部是清朝通史,是哈佛大學出版社“中華帝國的歷史”系列叢書之一。我這一卷的題目是“大清帝國:早期現代世界中的中國”。這本書力圖刷新我們對清朝的傳統理解,包括對“中亞的轉型”、“歐洲的轉型”乃至早期現代社會史的觀點。這個項目基本結束了,書稿大約要到2009年底或者2010年初出版。我這些年對清朝學士在政治思想中的創新,非常感興趣。《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把陳宏謀及十八世紀寫完了,現在的研究課題自然就進入十九世紀的改革家、文人學士包世臣(1775—1855)。包世臣提出了清朝中央、省府、及地方管理體制上應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革,目的是為了恢復和振興政府財政力量。關于包世臣的觀點,我寫了一篇論文,是關于他引進紙幣的可能性對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道光衰微時期的一個補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