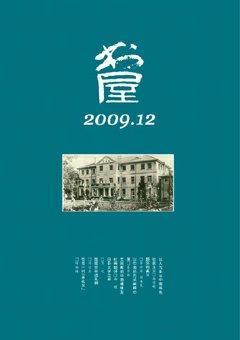德國精神的現代之光
葉 雋
作為現代哲學的重要大家之一,卡西爾(Cassirer, Ernst, 1874—1945)在希特勒上臺后曾有名言:“這是德國的末日。”隨即棄漢堡大學校長之冠冕如敝屐,流亡去也。事實當然證明了卡氏的預見性和洞察力,但問題在于,希特勒以其暴行將極端的不名譽加予德國及其民眾,這樣的后果極為嚴重。至少,在二戰后相當的長時段內,德意志民族必須承受“惡名”,這一點,從聯邦總理勃蘭特的“下跪”之舉中我們多少當可體味這其中的“悲涼”。作為留德學人的賀麟,曾在二戰結束后這樣評價德國文化:“德國的先哲尊重人類自由,教人自立法度,自己遵守,而希特勒抹殺人類自由,奴役人民。德國的先哲崇尚理性,發揚文化,而希特勒摧殘理性,毀滅文化。德國會產生希特勒這樣的敗家子,闖下滔天大禍,真是德國文化的不幸。凡是愛好德國文化的人,都應同感悲傷。只有一些無知淺見的人,才會由于見得納粹的失敗,因而根本懷疑德國燦爛時期的文化和哲學本身。”〔1〕當然,誠如史家所言,“德國文化和傳統的各種力量匯集在一起,使得納粹主義在德國生活中被接受和傳播開來”〔2〕。可賀麟型的說法,畢竟在舉世滔滔之際而獨標德國傳統及文化的偉大,自然是卓有見地。
我這里再舉兩個具體的實例,來說明德國文化的偉大傳統的另類途徑。這樣一種源自德意志精神傳統的現代之光,在兩個人身上得到最具普世限度的散發,即衛禮賢與史懷澤。作為“非洲圣人”的史懷澤,因其人道主義的偉大實踐而廣為人知,更因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光環而幾乎成為“人類愛”的代名詞;另一位人物即作為“中國心靈”的衛禮賢,以其對中國經典的德譯事業與對中西文化的深層把握,也同樣值得予以充分的關注。
由于這兩位偉大的同時代人物的存在,就足以表明,德國的精神之光并未黯淡,即便是在威廉二世到希特勒的“世界帝國”時期,德國依然出現了這樣的能夠代表人類精神的杰出人物,德國理當自豪。雖然德國人全體并未能在暴政之下醒悟過來,但恰恰是衛禮賢、史懷澤這樣的人物,起之于阡陌,而光耀寰宇間,他們所成就的事業和折射的人性之光,理應得到世界的矚目和敬意。
他們所處的時代,可謂是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他們都有過戰爭乃至被俘的經歷。衛禮賢在一戰中不得不在青島面臨日本占領軍的炮火和威脅,而史懷澤則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即便他是“敬畏生命”的醫生和圣人,也曾有過被俘的經歷。德國人難道不是在風雨飄搖之中嗎?無論是衛禮賢時代的一戰慘敗,還是史懷澤面臨的二戰結局下的民族瀕危,對于一個民族而言,都近乎致命性的打擊,對于個體來說則涉及安身立命的根基的摧毀。可他們在做什么呢?他們在堅守自我,他們在追尋世界精神的脈動。衛禮賢對于西方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原則性選擇,“疾風知勁草,板蕩見忠臣”,越是在危急存亡的時候,越是能考驗出一個人的意志品格。說實話,這要比梁啟超不斷“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要高出一籌。歷史可以證明,當德意志民族整體都因戰敗而深蒙屈辱之時,1953年一位德國人卻榮膺諾貝爾和平獎。相比較同時獲獎的美國人馬歇爾,史懷澤似乎更孚眾望,這或許已經是對德意志民族的最大獎賞,也可以是看作中國現代留德學人對德國精神認同的最佳證明。如果衛禮賢未曾早逝的話,他的光芒未必就會遜色于史懷澤,因為他們都是德國文化托命之人,是德國精神灼灼閃耀的現代之光。而之所以能如此,我以為至少有三點特別值得關注。
其一是西方宗教精神的滋潤。衛禮賢與史懷澤,一位在亞洲,一位在非洲,都以傳教士的身份而來到遙遠的異鄉,但他們不是簡單地傳布基督福音,而是本著虔誠的向真之心,努力尋求真理,這就使得歌德那代人的世界理想,有了一個具體落實的著力點。更重要的是,他們并不僅僅滿足于具體實踐層面的事功,而是努力達致一種思想的高度,通過著述和思考,來扮演一個真正的“殉道者”的角色。從表象看,兩者都是傳教士,都似乎為了一種西方的宗教精神,尤其是基督教精神而走向世界,可就本質言,他們都是最優秀的人類精英,他們都超越了“一系獨尊”的基督教狹隘教義,而成就了自己作為人類精神殉道者的書寫過程。
其二得歸功于德國文化傳統的養成。我們不可忽略的是,他們兩位都是德國人,都是非常有教養的德國知識階層中的人物。他們都非常自覺地繼承了以歌德為中心的德國精神傳統,并從實踐到精神方面努力契合之,這是特別值得關注的文化深層現象。史懷澤這樣理解歌德的知行合一:“不管他(指歌德)從事怎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從不以為不從事與此平行的實踐性的工作,便能做它,而且這兩者,在他絕非被統括為同樣使命、同樣種類的事物,它們是互為乖離的,它們之所以被統一,專靠他的人格使然。敲動我的心弦的是:他是從事精神方面創造者之中的偉人,這樣的他,不管是怎樣的工作,從不以為對他的品格來說是太卑微的;不管是怎樣的實務,從不說他以外的人,由于稟賦與職責,可以比他做得更好,他是在實踐性的工作與精神性的形成這兩者的平行之中,尋求使自己的人格統一。”應該說,歌德思想中“二元互補”的關鍵處是被史懷澤觸摸到了,而且他進一步肯定了歌德作為精神創造偉人的地位;衛禮賢更是將歌德與孔子、老子等中國賢哲相提并論,并且能更深一層進行比較:“他(指歌德)十分清楚地指出,如果生命的節奏搏動過速的話,本來具有互補性的東西方之間必然會產生對立。直到今天我們才完全清楚,他在這方面不僅超越自己的時代、而且超越后來的歷史學家有多么遠。”實際上,歌德努力在開辟的是不同于哲人的一條“古典思脈”之大道,誠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歌德的思想或許代表了人類現代文明的一個尚無法攀越的高峰。”而這個高峰的脈動,是被史懷澤、衛禮賢這樣的德國精神的現代之光都捕捉到了,這是很了不起的。
其三是他們對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的自覺親近。衛禮賢對中國文化的介紹不遺余力,奠定了現代德國甚至現代西方的精神根基,他毫不猶豫地質問道:“我們歐洲人還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嗎?或許我們將被其他民族所取代?這些民族繼承了我們文化中技術上的東西并且比我們消耗更少,它們不是談論其文化的沒落,而是感到自己的文化正在重新復興。”而他提出的方案是:“我們必須檢查自己的精神武庫,嘗試發現哪些是歐洲思想路線中需要保持的,哪些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另一方面要弄清,歐洲思想在哪些地方出現了斷裂,不能再長期維持下去。”這樣一種非常“有我”的思路決定了衛禮賢的中國文化觀具有極強的當下與本土意識,而這并沒有導致他的極端化,他堅定地拒絕所謂的“東方化”,強調“簡單照搬東方思想既不受歡迎也行不通”;他極富智慧地指出:“只有通過有機地發展自己擁有的財富資源,才能富有起來。”他主張立足西方思想(歐洲思想)的核心所在,汲取東方思想的精華,為我所用,實現西方的復興!歸納言之,我將其總結為衛禮賢的“西體東用觀”。有趣則在于,史懷澤同樣對東方思想,包括中國文化極感興趣。更重要的是,史懷澤的中國利用,有其特殊的思想史背景,“他繼承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傳統,在思想上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懷抱。這樣做的結果幾乎就是使自己的思想自然同中國思想連接了起來”。這個判斷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史氏和十八世紀的歐洲哲人一樣,他看重儒家,認為其“對理智之力的崇信”(glauben an die macht des geistes)可以激發人們“對自我進行思考”(nachdenken über sich selbst);他不是將中國作為一個尋求純粹學理知識的對象來認知,而是力圖向其尋求一種道德上的支撐,即一種“倫理文化”(ethische kultur)發展的基礎。但如果僅止于此,也不見出其思之高明,史懷澤還進一步接觸到道家,認為其能破除簡單思維(如“普遍的善惡觀念”)、促使自身思考(selbstbesinnung)。更重要的是,他揭示出“天人合一”思想之外的“天(自然)-人”差異性:“世界觀和倫理觀之間沒有密切關系,這是中國思想的特色……在孔子和孟子看來,倫理學是獨立存在的。世界觀是倫理觀的背景,而不是源泉。……對于中國人來說,世界上倫理秩序(sittliche weltordnung)的存在只是倫理學存在的一種背景,并不意味著倫理學要依靠這種秩序而存在。世界上倫理秩序是一種基本的和聲,在這個和聲上倫理學的動機可以自由發展……”所謂的“倫理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指一種世界精神境界的開辟,它是超越民族-國家層次,而擁有一種博大的人類胸懷的。史懷澤認識到中國倫理學的一元論特色,即道德生活與自然秩序理當相一致,而非二元論立場的一神論宗教所認為的那樣相左。至于衛禮賢,他對中國的認知更是相當全面、極富洞見。
今天,我們談理解德國精神,不僅是蔡元培、馬君武那代人所理解的“世界學術德最尊”、“德國文化為世界冠”而已,甚至也不僅是日后的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所代表的“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且理應包括以衛禮賢、史懷澤為代表的德國精神的現代之光,甚至可以說,正是以他們為代表的“行動中的精英”,才給我們展示了德國精神最光輝耀人的一面,至少他們應屬于歌德傳統的那個偉大譜系之中。
當代世界,經濟發達似乎已成為大國崛起的標志,連國人自己也不例外,這當然也可視作自信凸顯的象征。可問題在于,相比較衛禮賢、史懷澤給我們展現的精神高度,我們是否真的就認為中國現代文明已經真正可以產生這樣偉大的人類心靈?捫心自問,可有慚愧?當中國經濟崛起于世界之際,我們是否出現了這樣的偉大心靈、偉大人物?找出距離,或許,我們真的就有了可以努力的方向!
注釋:
〔1〕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64頁。
〔2〕(美)科佩爾·S·平森:《德國近現代史》,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6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