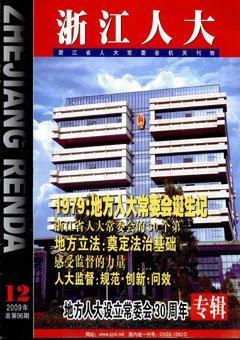1979:地方人大常委會誕生記
裴智勇


1979年,在新中國的政治民主進程中,銘刻著一段值得珍藏的記憶。這年的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首次規定我國縣和縣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孕育:三次動議
回顧歷史,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設立坎坷曲折。伴隨著中國民主法制的沉浮進退,在25年間歷經了三次醞釀。
雄雞一唱天下白。1949年,苦難中國迎來了春天。經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國人民終于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
1949年9月,《共同綱領》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新中國政體。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沒有立即普選產生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原主任顧昂然解釋說,當時普選的條件還不具備,因為軍事行動還沒有完全結束,土地改革還沒有徹底實現,各界人民群眾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
1954年9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但地方人大常委會并沒有同時設立。對于是否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從最初的討論、醞釀,到最后的決定、建立,歷經了漫長的歷程。1954年、1957年、1965年,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的提議,由于種種原因均未被采納。
第一次“孕育”發生在1954年制定憲法前后。1954年,憲法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人提出,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也應該和全國人大一樣設立常委會。這個意見沒有被采納。劉少奇同志對憲法作說明的時候作了解釋,他說,全國人大的職能,它的任務量更大,有繁重的立法,有監督,還決定國家重大的事項,任務比較多,地方沒有立法權,其他的任務量也沒有全國人大這么大。所以,當時考慮地方可以不必設立常委會。
第二次“孕育”發生在1957年。由于地方人大不設常委會,很快出現了問題。比如,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人民委員會行使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和執行機關雙重的職權。1957年上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如何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秘書長彭真同志提出,省、市、自治區和縣人大沒有常設機關,在大會閉幕之后,沒有一個對政府工作進行經常監督的機關。他認為,在縣級以上地方人大有考慮設立常委會的必要。彭真的意見受到中央的關注。但由于后來的反右斗爭擴大化,這個動議被擱置了。
第三次“孕育”發生在1965年。196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實際需要,又提出了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委會的問題。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我國地方政權機關的任務十分繁重,需要提拔一批年輕力壯的干部到政府工作。另一方面,設立常委會可以在人大閉會期間開展經常性工作,對地方一些重大問題及時討論并做出決定,特別是可以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監督。這時,各方對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已經取得基本一致意見。不久,“文化大革命”發生,方案又被擱置下來。
誕生:上下同心
鄧小平批示:“我贊成第三個方案”。 他說:“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一個重大改革。”
在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沃土上,進步的制度和觀念一旦孕育,就會生根發芽。
1979年,國家有關部門第四次提出了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的動議。
這是一個撥亂反正的關鍵歷史節點。中國向何處去?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國人痛定思痛,重新思考這個多難民族的前途。
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吸取歷史的教訓,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這一重大歷史任務。
197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了一個對中國民主法制建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工作機構——法制委員會。由80人組成,彭真掛帥。
3月8日,曾擔任過彭真辦公室秘書的顧昂然來法制委員會報到。3月19日,法制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彭真在會上談了法制委員會的任務和當前的工作。一些老同志主張開務虛會總結“文化大革命”教訓。彭真說,立法任務很重,一般的務虛會就不要開了,要結合立法工作總結經驗教訓,有針對性地在法律中作出規定,這樣從法制方面來防止這類問題再發生。當前工作就是加緊制定7部法律。這7部法是指刑法、刑訴法、選舉法、地方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3月31日,彭真找顧昂然談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問題,提出主要考慮三個問題:改革命委員會問題、地方立法權問題、地方人大設常委會問題。
彭真當時已經70多歲,當年5月曾生病住在北京醫院,還把顧昂然找到醫院去研究問題。
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也成為地方的呼聲。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在征求對地方組織法修改意見時,許多地方也提出,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人大應建立常設機關。
顧昂然說,把修改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當時也有人不理解。事實上,“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損失,就是因為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壞。從1966年8月到1974年12月,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委會沒有開過會,地方人大由革命委員會代替。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1979年5月17日,彭真專門向中央寫了報告,提出關于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的問題有三個方案:一、用立法手續把革命委員會體制固定下來。這樣做,不贊成的人可能很多。二、取消革命委員會,恢復人民委員會。這樣做,在名義上雖然取消了革命委員會,但對于擴大人民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實質性的幫助和改進。三、縣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并恢復人民委員會作為行政機關。這個方案可能比較好些。
5月17日,這個報告被送到當時的中央秘書長胡耀邦的手上,胡耀邦看了以后,當天就批給黨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鄧小平看了以后很明確地批復:“我贊成第三個方案”。
據顧昂然回憶,彭真帶回鄧小平的意見,大家深受鼓舞。鄧小平對彭真說:“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一個重大改革。”
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等7部法律。這是民主政治和法制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一個非常大的政治舉措。這次會議通過法律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
1979年下半年,在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進行人大代表直接選舉試點的基礎上,首批66個縣級地方人大常委會在試點中產生了。
1979年8月,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率先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設立了人大常委會。同一年,新疆、河南、北京、江蘇等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相繼召開人代會,選舉產生了本級人大常委會。另外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在1980年設立。兩個后設立的省級行政區海南省和重慶市,也分別在1988年8月和1997年6月設立了人大常委會。
起步:摸索前行
彭真說,人大常委會是權力機關,也是工作機關,不是“養老院”,而要依法行使權力,進行工作。
“如今,市人大常委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監督政府,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變化多大啊!”
2009年5月22日,站在建國門南大街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辦公樓前,74歲的李源富感慨地說。1979年12月7日至13日,北京市七屆人大三次會議召開,選舉產生了第一任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作為北京市組織部干部,李源富參與這次會議的籌備。后來,他調到市人大常委會工作,擔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代表聯絡室副主任。
當時,北京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設在北京市臺基廠大街8號院,是一棟歐式的2層小樓。1980年1月,李源富和同事一起從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領回國徽,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牌子一同掛在辦公樓前。
1979年12月24日,北京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李源富回憶說,當時,這個會到底怎么開法,主任們也不清楚。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賈庭三決定一切程序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方式辦。李源富專門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秘書局要來一套會議工作程序文件。
顧昂然說,地方人大常委會是新生事物,如何開展工作需要研究。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的同志專門來到北京,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請教。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決定,請地方來列席會議,召開座談會。1980年4月8日,省級人大常委會負責人第一次列席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
開始的時候,地方人大常委會老同志比較多,社會上也有一些議論。彭真就此說,人大常委會是權力機關,也是工作機關,不是“養老院”,而要依法行使權力,進行工作。
1980年4月18日,彭真在座談會上說,縣、省級人大設立常委會,在人大閉會期間,人民通過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來管理國家。這樣,9億人民就把國家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上一級人大常委會與下一級人大常委會要加強聯系,但是,它們之間沒有領導關系。
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是什么關系,顧昂然說,可以概括為三個關系:一是法律上的監督關系,二是選舉上的指導關系,三是工作上的聯系關系。
中央高度重視地方人大常委會建設。顧昂然說,1980年后,中央專門發了幾個文件,轉發了彭真的幾次講話。1981年4月,中央文件規定:“縣以上地方各級黨委要把加強對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領導,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定期研究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凡是按照法律規定應當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事項,都要提交人大常委會討論。黨委研究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時,可以通知人大常委會負責實際工作的黨員領導干部列席會議。”
“這些文件都是有針對性的,解決實際中的問題,譬如黨委和人大常委會的關系問題。有這些文件,就有章可循,理直氣壯。”顧昂然解釋道。
后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又根據形勢的發展幾次修改了地方組織法,制定了代表法、立法法、監督法。這些法律對地方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做了具體規定,為它們發揮作用提供了進一步保障。通過長期的工作,人們認識到,人大雖然不是火線,但也不是二線,人大是一線,是在民主法制建設的一線上。隨著形勢的發展,大家的感受越來越深。
30年來,地方人大常委會依據憲法和法律規定,結合本地實際,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工作制度。比如,一些省級人大制定了關于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關于行使監督權的規定、關于行使人事任免權的規定、常委會議事規則、常委會主任會議議事規則等等。
1979年12月29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包括《關于加強集市貿易管理的布告》等3個地方性法規。這是我們國家最早的地方性法規。
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設立和賦予地方人大立法權,對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顧昂然列舉一系列數據,截至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我國共制定了現行有效法律231件,現行有效行政法規600多件,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近8000件。初步統計,90%以上的地方性法規是由地方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從零起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30年,縣級以上地方人大常委會的發展歷程,成為中國政治文明進程最生動的片斷,最美麗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