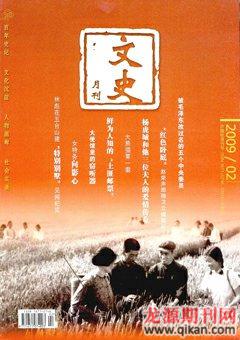鄉村女人
2009-02-05 10:21:08陳文芳
文史月刊
2009年2期
陳文芳

村里的娘們兒,在暮色四合的時候點燃灶火,裊裊的炊煙從屋頂的煙囪冒出,煮熟晚飯后,就來到村頭招呼自己的孩子回家。長一聲短一聲,呼喚聲交織在鄉村的夜色里,伴著晚風,凝成了許多人關于童年的溫暖記憶,哪怕白發皓首,哪怕天涯飄零,那些聲音也不絕如縷,永遠在天堂回蕩。
那些“做了娘的女人們”,在男人們這樣的稱呼中憨厚一笑,埋下頭,繼續著柴米油鹽的勞作。一輛馬車、拖拉機或者汽車加上鑼鼓把她們載到一個陌生的村莊,從此,命運就成了拴上線的風箏,一端牽著自己,一端交給了男人,提到她,人們習慣說“誰誰的媳婦”。婆家雖然沒有了“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的無奈與壓制,但生活在公婆以至村人的眼神下,謹慎也要有幾分。紅妝未曾褪盡,就坐在灶旁一把一把往鍋底添著柴火。
兒女誕生后,“誰誰的媳婦”變成了“誰誰的娘”。誰誰的娘,心都在孩子身上,她會毫無顧忌地敞開衣襟,讓孩子含住自己的奶頭。她把羞澀丟掉,也丟掉了女孩的天真與拘謹,她變成了鄉村原野上最普通的一株高粱,生長在玉米、大豆、棉花的中間,為爭取陽光和水,不停地向高處生長。
村里的娘們兒眼睛緊盯著土地,乘著朝霞上路,伴著月色歸來,沒有詩意,沒有浪漫,只有莊稼的長勢與收成。孩子讀書是一項任務,做娘的要督促完成,上學惹事要打屁股。村里的娘們跟著村里的步調,不超前也不落后地走著,好像那句順口溜“莊稼活,不用學,人家咋做咱咋做”。……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