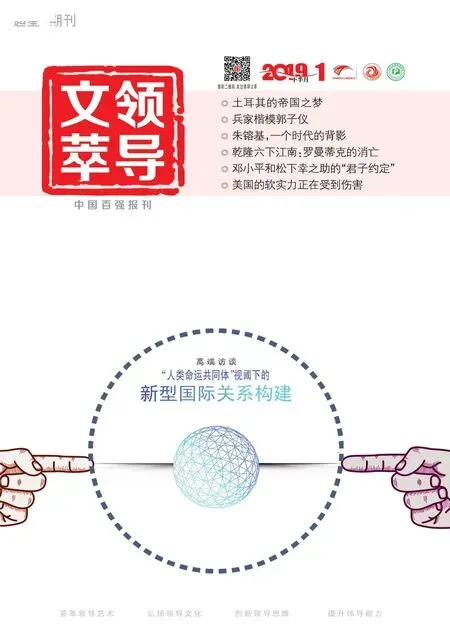毛澤東與劉少奇在農村問題上的分歧
杜潤生是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70年代末80年代初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80年代中期以后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一書(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以親歷、親聞、親見,記述了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變革的有關情況。本文即選自該書。
在延安時期,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是劉少奇首先提出來的:“我們黨已經找到一個自己的當之無愧的領袖,就是毛澤東”。在七大前后,反對王明教條主義,毛劉是完全一致的。后來,劉少奇和毛澤東發生爭論,就農村問題來說,首先是在1951年。山西提出試辦初級合作社,動搖私有制基礎。劉少奇認為,這是空想社會主義,不符合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路線。此事給我的感覺,辦幾個合作社就叫做空想社會主義,批評話語顯得重了一些;但他堅持新民主主義戰略,是正確的。
相反,毛主席卻否定自己提出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張。從1951年起,發展手工勞動的農業合作社,動搖私有制。1964年后,進而把“消滅資本主義使其絕種”作為總方針,直至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當時在黨的上層,只有劉少奇能夠提出,也最合適提出異議。但劉少奇始終不愿意把自己放在與毛澤東對立的位置上。在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大問題上,毛對劉已有成見,不聽他的,劉只好檢討。
劉少奇選擇了一個作檢討的場合,是在1953年初。為公布《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協議》,專門召集了一個十多人的會,我是代表中央農工部去的。劉說:“在合作化問題上,高崗同志是對的,我是錯的。”并說自己在認識上行動上有缺點錯誤。盡管劉作了檢討,在1953年夏天的財經會議上,高崗發動了“批薄射劉”的非黨活動,指桑罵槐,舉了許多事例,都不是指薄一波,而是指劉少奇的。鄧小平讓我參加會議,我去聽了,已察覺黨內要出問題。果然這個會后,在中央組織工作會上,饒漱石領導“討安(安子文)伐劉”。此外,高還搞了非法串聯,因此成了“高饒反黨集團”。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得到毛澤東的支持。為了表明他的擁毛立場,劉又在合作社問題上作了檢討。
在此之前,東北全境解放后,東北局向中央報告,提出農村保存富農,暫不搞集體化,仍按新民主主義戰略規定的政策措施。這是張聞天的主張。劉少奇是支持這個主張的,曾以中央名義加批轉發全國。本來,七屆二中全會和建國初的政協《共同綱領》,都是沿新民主主義路線闡明有關政策。毛、劉、周的講話也都是一個口徑。然而從1951年開始,毛親自指導了有關互助合作兩個文件的起草工作,未見劉參加。毛的一些意見,都是由陳伯達傳達。
毛主席幾次召見中央農工部同志談話,談合作化的問題。為分配合作社發展數字,召集過兩次會議,即杭州會議、北京會議。此前,少奇主持中央開會聽取農工部匯報。在1955年4月20日,鄧子恢剛從國外考察回來。譚震林、鄧子恢、我先后發言,引出劉少奇發言,說:我贊成搞100萬(毛要擴大),到時候關一下門,要中農來敲門。我們把這批辦好,更具有吸引力,事情就好辦了。這些話,表明劉少奇是支持中央農工部的。鄧小平的意見也是把重點放在鞏固上。
1955年5月中旬,在杭州召開的南方各省會議上,毛主席主張合作社要增派數字,派多了不行,不派自流也不行。這時上海的柯慶施提出指控:30%的干部對合作化不積極,是受中央農工部影響。同時毛聽到浙江“砍社”一事,不高興。6月14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中央農工部關于合作化的方針,劉少奇當場批評了鄧子恢的一些言論,認為鄧消極,不夠積極,還有一些原則錯誤。這與劉前一段的態度亦有所不同。
在7月會議上,毛主席發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提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大風暴就要到來,有些同志在這個風暴面前,像小腳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此時,劉進一步支持毛。在10月末舉行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劉少奇尖銳批評中央農工部是“發謠風”,用語也比毛、周都重。但是,盡管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毛,他還是堅持生產關系要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思想。這表現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寫上了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實質是生產力發展不能滿足這一要求的矛盾。毛對這次大會報告稿親自過目,做了多處修改。但是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卻提出八大報告對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錯誤的,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
1956年,周恩來、陳云提出反冒進問題,此時劉少奇是支持周、陳的。毛批周、陳,也等于批劉。
大躍進興起,劉、毛是一致的,未見分歧。但引起大混亂以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在劉領導下準備了書面報告。毛說報告稿可以發給大家,可離開稿子講一講。劉就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毛內心可能不以為然,但在大會上沒有講出來,還是強調讓人講話,發揚民主。“白天出氣,晚間看戲,一天三餐,兩干一稀,皆大歡喜”。但林彪替毛說了話:毛主席思想是一貫正確的,所以出問題,主要是在于“左”或右的干擾。會后毛就南下了,把醫治大躍進后果這個擔子,交給了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人。
結果惹來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批“三風”: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1962年初,為醫治三年困難的后果,自然要審視過去,吸取經驗教訓,要讓人講話。
為此,由劉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樓召開了有關方面領導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講了一些比較嚴重的情況,劉少奇說:估計嚴重比估計不足要好,更主動。陳云說:要退夠。鄧子恢趁此提出包產到戶。毛主席從外地歸來,當面責備劉作為第一線主持人,本應給予引導,為什么不能壓住陣腳,反而助長這股“黑暗風”。因此,1962年北戴河會議的準備會議,原意醫治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后果,就因為出現“三風”這類政治傾向,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還有一個關于“四清”的矛盾,劉主張通過“四清”,反四不清,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毛則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6年以批判《海瑞罷官》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不點名地指出:1962年的右傾,1964年形“左”實右,1966年派工作組鎮壓學生,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身邊等等。黨的十大時,進而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盡管劉少奇委曲求全,多次修改自己本屬正確的主張,進行檢討,維護毛的權威,最終仍得不到諒解,還是帶著“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帽子含冤而去,寫下黨內斗爭的一幕悲劇,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才予以平反。
彭德懷和毛澤東之間也有許多分歧。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反對大躍進,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毛深為不滿。毛澤東在廬山反擊彭德懷時提出:是爭奪領導權還是路線是非問題?是要我毛澤東,還是要你彭德懷?此話一出,別人只好三緘其口,能作的選擇也就被這樣“規定”了。
其實1955年在北京,1959年在廬山,毛一表態,彭德懷都作了檢討。因此,可以說黨內的決策制度、“議事”制度,在50年代后期存在著不夠民主的缺陷。面對著像“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改造”和“大躍進”這類重大的問題,如果真正發揚民主,爭辯一番,也許更有利于黨內認識的統一,更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發展,少走彎路。(摘自《杜潤生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