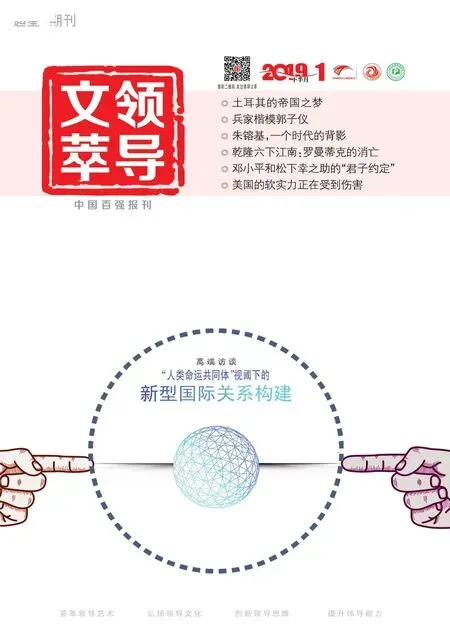和諧社會拒絕“風險家庭”
穆光宗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已經形成一種“低生育文化”。“低生育文化”包括了政府主導的“獨生子女文化”和草根自覺的“兒女雙全文化”。理性的生育求的是“好”與“福”。兒女雙全是為“好”,衣食無憂是為“福”。但過去那種“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基本上沒有了市場,很多調查可以支持這一判斷。顯然,這“好”與“福”存在著天然的聯系。無兒無女怎么可能“好”?有兒女卻無后的不叫“好”(如大齡獨生子女傷殘病亡),獨生子女也難稱“好”,因為這“好”字左邊是“女”右邊是“子”,合在一起才叫“好”。在倡導“生男生女都一樣”的今天,我們對“好”的新詮釋就不再局限于兒女雙全了,而是兩全其美。中國人的“子福”觀包含著對人生真諦的樸素理解。在沒有性別選擇的情勢下,僅僅從生育的數量和構成來看,“兒女雙全”可謂大福,“兩個孩子”可謂中福,“一個孩子”可謂小福。在理論上,我們探詢到的生育幸福的底線就是“兩個孩子”,就是“兩全其美”。作為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責任政府需要維護的就是這種生育的幸福。在基于生育幸福理論的兩孩政策框架里,至于一個家庭究竟是生育一個孩子還是生育兩個孩子,那可以是悉聽尊便、自由選擇的私權。
有一個事實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風險越大。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家庭開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轉變為“高風險家庭”。我們已經有了幾千萬獨生子女家庭,其數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恐怕是驚人的。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存在一定比例的獨生子女,但倘若獨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為主體,其潛在的風險無論如何都是不應該被忽視的。潛在的風險一旦爆發就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帶來預想不到的嚴峻挑戰。
從現在的眼光看,“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的命題大致包括三個視角九個層面的理解。首先,對獨生子女來說,其風險包括獨生子女的成人風險、成才風險、婚姻風險和養老風險;其次,對獨生子女家庭來說,包括獨生子女家庭的兒女養老風險、結構缺損風險;再次,對獨生子女社會來說,包括發展風險、國防風險和責任風險。具體來看,其含義是:
第一,獨生子女的“成人風險”是指獨生子女傷病殘亡的風險。其風險性就在于其唯一性。特別是大齡獨生子女死亡對一個家庭及其整個親屬網絡精神上的打擊均是十分沉重的。
第二,獨生子女的“成才風險”是指獨生子女缺乏一個良好的可以實施“同伴教育”的成長生態,難以全面發展,智力素質與非智力素質發展的不平衡幾乎成為共識。
第三,獨生子女的“婚姻風險”有三種情勢:一是成婚難,因為獨生子女容易以自我為中心,個性強,生活能力卻不一定高,現實生活中已經有父母親自為成年獨生子女找對象的新聞了;二是婚后沖突會比較多;三是婚姻壽命可能比較短。
第四,獨生子女的“養老風險”是指獨生子女所擁有的養老資源更少,有兩種情勢:一是他們沒有兄弟姐妹,所以親屬的養老支持幾乎是不存在的;二是獨生子女群體對不育和獨子生育的偏好可能更強。
第五,獨生子女家庭的“兒女養老風險”是指獨生子女作為唯一的養老責任主體,注定了獨生子女的養老責任重大、心理壓力巨大。俗稱的“四二一”家庭結構是脆弱的家庭結構。從長遠來看,幾乎所有典型的獨生子女家庭或多或少都會面臨經濟上支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養老風險。
第六,獨生子女家庭的“結構缺損風險”是指結構完整的三角形的獨生子女家庭可能因為遭遇獨生子女的成人風險而出現結構性的缺損,嚴重者可導致結構的瓦解。獨生子女家庭的結構缺損風險是獨生子女成人風險中最嚴重的一種。簡單地說,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推演過程中,獨生子女風險家庭可能進一步轉化為殘缺無后家庭,成為家庭和社會的傷痛。
第七,獨生子女社會的“發展風險”是指這么一種擔心,由于有的獨生子女缺乏團隊精神、缺乏吃苦精神,因此,可能會在未來時期的一定范圍內影響社會發展的人力供應。
第八,獨生子女社會的“國防風險”是指在非和平時期,獨生子女群體的戰斗力是讓人懷疑的。獨生子女群體是家庭和社會神經的敏感點和脆弱點。家庭的牽腸掛肚構成了社會的共同關注和政府的小心翼翼。
第九,獨生子女社會的“責任風險”。這里說的責任風險是指一個文明社會的政府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越是大決策,越有大風險。風險決策必須承擔起責任風險,這是文明社會的基本通則,所謂損失者補、犧牲者救、受害者助。在鼓勵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導向下,政府必須為獨生子女家庭和社會可能遭遇的各種風險承擔起防范風險、規避問題和補償代價的三大責任。
上述九個方面構成了無法掙脫的風險鎖鏈,就好像生態學上講的“蝴蝶效應”,其連鎖反響是巨大的、不可忽視的。應該承認,風險只是發生問題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變的。但在繼續鼓勵“只生一個孩子”的導向下,風險的放大卻是必然。所以,“獨生子女文化”一旦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繼續風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總和生育率低于1.3,即育齡婦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數不超過1.3個)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長的內在活力,那將是十分危險的事情。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暫時的勝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等于獨生的做法已經并將繼續使我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毫無疑問,我們需要的是“健康家庭”而不是“風險家庭”,我們追求的是“和諧社會”而不是“風險社會”。風險家庭越少,社會沖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會和諧越多。“健康家庭”獨有的結構和功能使其具備抵御各種風險的結構性力量。在理論上,生育兩個孩子是計劃生育的底線倫理,但考慮到中國人口過多的事實,這一倫理的底線在多數地方也同時可以理解為政策的上限。雖然決策屬于政府的責任范疇,求真屬于學界的責任范疇,但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無論如何是決策科學化的首要前提。
(摘自《社會學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