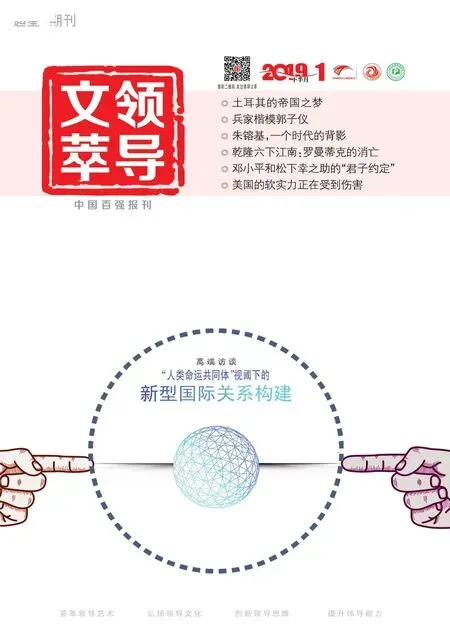什么知識,改變誰的命運
田 松
張藝謀拍了一個系列公益短片,主題叫做“知識改變命運”。這話抽象說來應該是不錯的,我們常常引用的培根說的就是這事兒,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可以改變命運。然而,知識怎么就改變了命運?什么知識,改變誰的命運?
每當城市人來到“貧困”山區,看到那里“貧困的”人民,正面的反應是要生出同情之心來,幫助他們進步、發展,而看不到那里曾經存在的乃至依然存在的文化傳統。而對于為什么貧窮,當下流行、典型的解釋是,因為你落后,因為你不發達,所以窮。對策同樣簡單而一律:教育投入啊,科技投入啊,招商引資啊!教育投入,提高人民素質,就能掌握先進生產力了;科技投入,招商引資,就能開辦工廠了,就能往外賣點兒什么了,就有錢賺了,于是就進步了,發展了,富裕了!
然而,李昌平早就說過,農民的貧困是制度性貧困,科技未必能夠幫助農民致富,反而會讓農民更加貧窮;教育也未必能夠讓農民在未來致富,卻極有可能讓農民在當下致貧。
在傳統社會中,一個地域的人們如果能夠祖祖輩輩在那里生活下來,必然掌握足夠的生存智慧,可以與這個地區的環境達成和諧的關系,并可以在這種生活中獲得生存的意義,獲得幸福。在自然的環境中,哪怕不是風調雨順,一棵樹只要活下來,也會越長越高。具有漫長歷史依據的人類的生存智慧,也應該會使農民的日子在本山本水之中,一天天地好起來。但是現在,在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幾十年后,卻看到很多地方的農民無法靠種地為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們靠進城打工,靠撿垃圾,有的甚至靠賣血為生。
曾看到《上海證券報》楊斌的一篇文章《財富是如何從農村源源不斷流向城市的》(2007年7月23日),楊斌指出:“農民負擔不僅僅只是納入農村稅費改革視野的農業稅、農林特產稅,三提五統,稅外稅費和攤派(可稱之為‘老三重負擔,有的專家估計這些負擔全國每年約1800億),農民負擔的主要部分是目前尚不為多數人所認識的間接稅費負擔(每年近5000億)和‘暗稅負擔(本文稱之為‘新四重負擔)。”
楊斌先生的原文很長,這里只能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新四重”負擔的第一重是間接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等)……間接稅稅含價中,人們在購買商品或消費服務時不知不覺已經將稅收繳納了,比如農民花了100元購買工業日用品,實際上已經繳納了17元的增值稅……間接稅是可轉嫁稅,納稅人不等于負稅人。流轉稅形式上看,主要是由城市工商企業繳納,但實際承擔稅收負擔的不是企業而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消費者,他們在購買商品或進行消費時,將含在價格中的稅收一起支付了。并且我國間接稅(流轉稅)實行生產地課稅制度,納稅人以城市工商企業為主,工商業越發達地區其稅源也越豐富,獲得的流轉稅也越多,這樣工商業集中的大中城市獲得的流轉稅就占最大的比例,通過分稅制分得較大的份額,并作為城市公共產品的財力來源。中央政府、省特別是大中城市政府獲得的流轉稅收入,并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費者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農民消費者支付的。對城市居民而言,他們負擔的流轉稅,通過獲得政府提供的各種服務(包括義務教育、城市基礎設施、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等)而得到補償。但農民負擔的流轉稅卻主要轉到了城市,他們居住地政府并沒有獲得這部分由其轄區內農民負擔的流轉稅,從而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公共產品的財力來源。這就形成集中納稅和分散負擔的非對稱性。財富由農村、由縣鄉源源不斷地流向大中城市。
這還只是“新四重”的第一項。加上其余的如工農剪刀差、征地補償不足等幾項暗稅,根據2002年的數據,農民直接或間接貢獻的稅賦近8000億元。文章讀過,觸目驚心。財富在制度的安排下源源不斷地由農村流向城市,當然就會產生李昌平所說的制度性貧困。8億農民,平均每人每年的承擔的稅賦達到1000元之多。這意味著一個三代五口之家,其負擔將達到5000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就有農民孩子上了大學,父親因無力承擔學費乃至自殺的消息。知識在改變命運之前,先要了人的命。
于是我們看到,所謂“知識改變命運”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在社會底層的某個個人因為苦心讀書,龍門一躍,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從而命運得以改變。這些故事對于某一個具體的個人,可能是成立的。但是,一個山村的整體,卻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而得到改變。正如一個打工妹,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成為打工女皇,居于跨國公司副總裁的高位,但是打工妹這個階層的整體,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改變命運。又如我們某一個人,可以通過考托考G,出國留洋,享受現代化上游的生活,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把自己整體變成美國。
相反,當下全國一統秉承冥尺(一種超越民族、地域和文化傳統的文明尺度,就如科學定律一樣,仿佛存在于冥冥之中,即冥冥中的尺度,簡稱為冥尺)邏輯的制度化學校教育,會對農村的傳統文化構成致命的打擊。在這種教育的價值體系中,傳統的生存智慧必然是原始的、落后的、愚昧的,于是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教育悖論:受學校教育越多的人,越看不起自己的傳統。在這種教育中成功地被格式化,“學有所成”的,他們最好的出路是進入大城市,成為或中心或邊緣的現代人。而剩下的絕大多數,卻失去了學習本鄉本土的生存技能的大好時機,成了“浪費鋪蓋卷的廢人”。
于是,一方面,當下的制度化教育把傳統文化的潛在傳承者變成了工業文明的候補勞動力,抽去了傳統文明的釜底之薪;另一方面,當傳統地區失去了傳統的知識體系,接受了冥尺邏輯之后,也會主動地從下游加入到工業文明的食物鏈中,為其上游提供自然資源及廉價勞動力。傳統的人文生態以及與之相依存的自然生態難以為繼。其結果,生態日益惡化,傳統日益消失,而農村則更加貧窮,命運更加艱難。
農村命運的真正改變,是讓農民掌握自己的命運,恢復其自組織的能力,獲得對自己事務的主導權。一旦農民身上的嚴重負擔得到解脫,農民的生活會逐漸好起來。這時,所謂現代科學,也可能成為這種地方性知識的有益補充。(摘自《博覽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