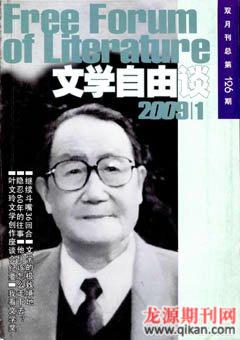短序兩側
金 梅
《李叔同為什么
出家?》序
一代宗師李叔同,對推動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進程,做出過諸多開創性的貢獻。但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正在醞釀并漸露端倪之際,需要其在這方面成就更大業績的時候,他卻芒缽錫杖,一肩梵典,毅然決然地遁入了佛門。對于李叔同的這一舉動,國民黨元老、曾經執教于李叔同母校南洋公學的吳稚暉,說過這樣一句話:“李叔同可以做個藝術家而不做,偏去做和尚!”不只當時,即在過去了90年后的今天,還是有許多人,其中包括李叔同的一些崇敬者,對于這句話,依然抱有同感。就是說,在人們的心目中,“李叔同為什么出家”實在是一個“世紀之謎”。這也表明,人們是在期待著能夠解開這個“謎”的謎底。然而,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從李叔同入佛的那天起,他的朋友、門生、追隨者、仰慕者和研究者,一直在試圖探索和解開其出家之謎,但常常因了失之于偏頗而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我們看來,惟有以社會科學的眼光,從李叔同生活的時代、社會環境以及當時盛行的思潮,他的家庭、身世、經歷、個性、氣質、心理、生理、接受的教育、從事的學術活動(職業、愛好)、人生態度、思想特征,以至人際交往,等等方面,進行綜合性的研究,方能得出合理的解釋和結論。正是本著這一思路,我們編撰了《李叔同為什么出家?》這本書(筆者注:該書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希望在探索和解開這個“世紀之謎”的過程中,能對讀者有所參考與啟發。
戊子年春寫于津門
《傅雷傳》修訂本自序
傅雷先生是我國“五四”后成長起來的一代知分子的杰出代表。
他的受人崇敬與推許,固是因其學識的淵博,藝術鑒賞力的高超,尤其是作為譯壇巨匠,其在譯事上的輝煌成就。——可以說,正是通過傅雷的大量譯著,我國的廣大文學愛好者,才開始領略了巴爾扎克、梅里美、羅曼·羅蘭、丹納、莫洛阿等等法國近現代文學藝術家及其代表性作品的內涵與神韻。然傅雷之令人看重與長期懷念,自當不獨以此為限亦顯矣。
傅雷之可貴,還在于他對國家民族懷持著深深的愛,和由這種愛所產生的綿長不絕的憂患意識;他待人處世的光明磊落,真誠坦蕩;他于世間事物之善于獨立思考,不理解者或不合己意者,從不首肯與阿附;他于文于藝,始終堅持德藝俱備、人格與文格之統一;他將人格之獨立與尊嚴,視為自己立身行事的最高準則……凡此種種,他的道德品格和思想精神境界,以及其在教子成才方面的良苦用心,都堪稱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范。
出于對桑梓的熱愛和鄉賢的敬重,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寫作了《傅雷傳》一書。這本傳記,先后在臺灣和大陸地區印過多次。有位香港讀者曾為文指出,從本著中看不出作者對法國文學有過專門研究。他看到的是事實,我除了讀過傅雷先生翻譯的作品和其他一些法國文學名著,與“法國文學研究”這樣的專門學問,確實不沾邊。不過他之言下,似乎還有這樣的意思:傅雷先生的傳記,由法國文學研究家來撰寫最為合適。應該說,他的意愿,也正是我的意愿。我之當初寫作《傅雷傳》,本意之一就在拋磚引玉,希望最終能有一部由法國文學研究者撰寫的,內容更為系統完備,質量亦上乘卓越的傅雷先生的傳記文本出現。只是時至今日,此愿好像仍未得償。于是,本傳還得留存一段時間。這真應上了中國的一句俗話,“沒有朱砂,紅土為貴”了。
北京航空航天出版社既有意重印這本傳記,我便利用這個機會,將全書修訂一遍,補充了一部分先前未曾見過,或是雖曾見過而被忽略,被粗疏地處理了的史料,也改正了初版本中不夠準確的一些描述。但限于我的學識與水平而無法克服的缺點,就只能再請讀者原諒與指正了。
戊子年中秋寫于津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