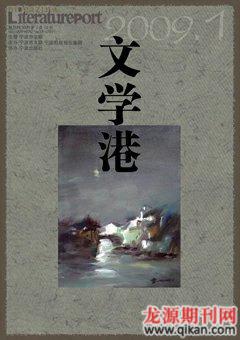我與兒子的大學生活
復 達
一、皮箱包與木箱子
兒子要上大學,箱包就成為必需品。妻子說要買兩只,我一愣,學校里放一只皮箱不就夠了嗎?放假時有一個背包就行。妻子說,一只大的固定在寢室里,一只小的作為活動式用,放假回家或旅游都可帶上,兒子要帶著的東西會很多。知子莫如母,兒子也定然會如此這般地要兩只箱包,哪像自己上大學時那樣呀,便欣然贊同。
那天剛好去市里辦事,妻兒便一同前往購箱,還非要我陪同參謀。市一百的箱包銷售處占了一個樓層,大大小小、色彩紛呈、樣式不一、質地各異的箱包,一排排一層層錯落有致地擺放著,除了行走的過道,成為琳瑯滿目的箱包世界。臥著的臥在貨架上,臥出了一種安逸;立著的立在磚面地上,立出了一種優雅。仔細察看,制作箱包的材料,有純皮也有仿皮的。在滑輪和拉桿的配制上,特大型的箱包只有四只滑輪而無拉桿,大中型的兩只、四只的滑輪皆有,拉桿俱全,小型的既有兩只滑輪,也有輕巧的拉桿,靈活自如,方便行走,將箱包內的重量消解在便攜之中。品牌的多樣也令人眼花繚亂,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有著名商標的,也有未曾聽說過的,讓人很難揣摸其真偽。
箱包的繽紛多樣確是難為了我們的選擇,猶如籮筐里揀花,一下子難以定奪。本想讓兒子挑選那些名牌箱包,又想他剛上大學還用不著有那么強的名牌意識,再說難以分辨這些所謂的名牌箱包是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何況這些名牌箱包又貴重,花錢多是一回事,兒子四年大學畢業后今天所買的箱包肯定不會再用,于是便讓兒子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兒子走來拐去,一只只地挑選,妻子也將自己看中的推薦給他。不同品牌的售貨員更是忙不迭地將箱包拉出來,邊示范拉桿和滑輪,邊順口解釋其優點,還拉開箱包展示里面的容積和夾層,也算是公開公平地競爭吧,卻搞得我們有點不好意思。最后,還是讓兒子定奪。一只大的黑色的和一只小的黑藍的箱包于是被裝在了車上,大的將固定安放在兒子的寢室里,小的就作為兒子每次離校回家或外出旅游時隨身所帶的載體。
兒子這一代確是無憂無慮的幸福一代,別的不說,單是箱包就用得如此暢快,巧妙地一拉便能緊隨身后抑或推在前面,悠然自得地行走在街路上。想想自己三十年前上大學時的情景,當真是天壤之別,兩重生活。這就是時代的差異吧,是當時的我無法與現在的兒子相比的。
那一年當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興高采烈的心情自不必說,卻讓父母在高興之余也為難起來。那時父親在村里當出納,是家里生活的主要支撐,母親勞作在田地,補充著家庭日常開支,三個兒子都在上學,就如嗷嗷待哺的雀兒很需要營養的攝入,靠著父母微薄的收入只勉勉強強地過著日子。我上大學的費用就是一個額外的支出。雖然當時學校有伙食補助,也不用交學費,但是書費要自掏,作為一名大學生總要穿一件新的衣服,戴一個手表也好像是大學生所需要的。自然還有那貯放衣物的箱子更是必不可少。最好是購置一只皮箱,如此才仿佛與大學生的身份相吻合。
那個時候,十六七歲的我很純樸,也很懂事,我只要能上大學就行。上大學才是我的愿望,其它的就顯得無足輕重。我便將新衣服呀手表呀統統撂在了腦后,包括耀眼亮麗的皮箱也顯得可有可無,只要有一只木箱子就行。就這樣,我的第一塊手表是在第二年父親托跑貨運的朋友從溫州購買的雙獅牌走私表,我上大學時的一件最好的衣服也是第二年父母從牙縫里省下的錢為我所做的一件藍色的中山裝,我的第一只皮箱是若干年后我送給那時還是戀人的妻子上大學進修的梅紅色小皮箱,這是后話,也是題外話。
木箱子的事就提上了家里的重要日程。父親將家里僅有的木板挑了又挑,請木匠精心地制作了一只長方形的箱子,又叫一個做漆匠的熟人抹上了紫紅色的油漆,再配上一把幾毛錢的小鐵鎖。于是,一只具備皮箱裝物功能且外表光亮鮮艷、四角圓潤的箱子在幾天內擺放在了我的面前,讓我眼睛一亮,好生喜歡。我想,那樣一只漂亮大方的箱子,想必在同班同學中也不會差到哪里去。至今想來,那時候全然沒有想到過皮箱上有密碼鎖,有滑輪,有拉桿,還有帆布、尼龍布、牛津布等也可制作箱包的,現在的箱包當真是繽紛多彩,功能俱全,方便攜帶。而我,去上學的那一天,用一根海藍色的塑料繩系好木箱子,留出一個手提的繩圈,在父親的提攜下,我肩背一個泛黃的軍用挎包,手拎一只廉價的塑料拉鏈包,跨海過洋去學校。一路上,我從未想過將在幾年時間里安置于寢室里的木箱子是不是寒酸,假期來回要提的包是不是太蹩腳,我只感心滿意足,心花怒放的情緒也時不時地洋溢在臉上,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上大學就如鯉魚躍龍門,其它的全然踩在了腳底下。
時過境遷,斗轉星移。時代的發展確乎讓當時的我根本所想象不到,物質財富在膨脹的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人的觀念的轉變,更不用說像我兒子這樣的下一代自是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變化。我這樣的所謂過來人,不服也不行,不緊跟時代的節奏更不行。這就是現在的生活。
二、寢 室
陪兒子上大學時,兒子所住的寢室寬敞得令我的眼光發亮,室內日常生活上一應俱全的設施設備更是讓我嘖嘖稱奇。油然想起自己當時所住的寢室,仿佛是兩個世界,心里不由泛起陣陣感嘆。
兒子就讀的是上海某大學的一所獨立學院,這類獨立學院算是近幾年市場經濟的產物,收費相對較高,單是住宿費每年就需三千元。這樣的一筆錢,自然該給學生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于是,我看到的是幾棟高高矗立的學生公寓,與教學樓、綜合樓一起組合成校園中的高樓大廈群。十七八層高的學生公寓,由幾部電梯馬不停蹄上下往返,每一層的寢室便是它們的目的地,只有在上課和夜深時才能喘一口氣歇息。三十年前我所讀的也是一所剛辦幾年的大學,想來是由師范學校升級的吧,主樓充其量只有四層,所住的三層樓寢室憑著我們年輕人快捷有力的步伐,三步兩腳就能跨上去,便捷得如走家門一般,哪見過如此這般的高樓,連學生公寓的名稱也從未聽說過。
兒子的寢室寬大得可容納下五張上下鋪的床鋪,卻安放著只有三張鐵架子的上下鋪,六個人住。每人一單桌一方凳,門邊還有一大櫥,分隔成一人一小櫥。室內布置著一間洗漱間,有洗漱臺,也有淋浴盆、座便器。即使這樣,整個房間還是給人空曠的感覺,寬敞,明亮,舒適。空調高懸在窗頂上,露出得意的笑。飲水機立在大櫥的角落邊,穿著乳白色的新衣,仿佛在迎接新生的到來。電話機掛在洗漱間外墻上,微笑著靜候新生們的撥打。寬帶的接口不動聲色地閉合在墻裙邊上,等待著電腦接線的貫通。寢室便像個小賓館的房間,讓住宿的人感受到在家中生活的方便自如,更有一種集體公寓的味道,充塞著現代生活氣息。
回想自己當時所住的寢室,當真是屬于簡陋一族。雖也擺放著四張木架子上下鋪的床,住八個人,但那床鋪緊挨著排列在狹小的房間里,只有靠門的邊上放一張破舊的課桌,供我們放置刷牙用的搪瓷杯。兩張方凳涂抹著污垢般,仿佛就為了上鋪的人隨意踩踏上去而安放,坐人便要墊上報紙。公用的洗漱間辟在樓梯的邊上,一個樓層里的學生常常要排隊洗漱,更多的人則在晚上將水用臉盆盛著,早晨起來時蹲在走廊邊上,將刷牙洗臉的過程濃縮在大半盆水里。廁所在樓層的頂端,早晨便人滿為患,有性急的干脆跑到校園的廁所里去舒暢,最怕寒冬時的半夜里急解,從熱乎乎的被窩里跳出來,穿著短褲汗衫,穿過昏暗的走廊,在寒冷的夜色里倒也能暢快一番。寢室里的燈在十點熄滅,整幢樓便變成一座龐大的黑影,這對我們喜讀書的人來說,是最大的不便和制約。住宿條件差些可以接受,電燈限制著,卻將我們的心路阻塞了一般難受。雖然無需我們付費,但要是如兒子現在這樣可以自己付電費用電,也該多好。后來雖換了間六人住的寢室,卻更狹小,床鋪之間的空間還沒有一張床鋪大,六個人站著可能也會嗅到對方嘴里呵出的氣息,只有床上才是自在的空間。于是,客人來了坐床沿上,書購買來了放進床里邊,下課回來跳進床鋪,床上成了我們的自留地。那時候的寢室,就連現在十元錢一個晚上的廉價旅館還不如。當然,這只是與現在兒子的寢室作比較才感受到,那時候的我們也就習慣了這樣的寢室,更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那天下午比兒子早到寢室的已有兩名學生,一是江蘇蘇州的,一是浙江杭州的。蘇州的學生早上八點鐘就一個人攜帶著兩大編織袋和帆布袋,再拉著一只小皮箱來到了學校。杭州的那個在他父親陪同下于中午時分到達,也是一大一小兩個箱包,住在兒子的上鋪,能說會道,也很機靈,或許是早已將學校的環境摸了一遍,介紹起來頭頭是道。同一省份的兩名同學住在上下鋪,也算是一種巧合。翌日上午,上海本地的三名學生在各自家長的陪同下也先后提箱攜包來到寢室,看上去都還算本分,也與兒子一樣喜歡打籃球。如此,六個同室的人或許就將住上四年。然而前兩天兒子吞吞吐吐地說,最好是住四人一間的。問其原因,回答竟是晚上同室的人總是聊天,要等半夜十二點左右才能睡著,也因為早上起來洗漱時總要排隊等候,解急更是燃眉一般焦急。同寢室的人聊天自是因為晚上可以任意亮著燈,有燈光就有話題。倘若同寢室的人約定一個時間睡覺,就不成其為問題了。排隊解急卻是由于缺乏耐心,稍能注意一些生活規律的話,比如提早十分鐘起床不是解決了問題?六個人住著這么舒適的寢室,卻還是不盡兒子之意。喜耶?憂耶?
我們卻在擁擠的寢室里度了過來,昏黃的燈光陪伴我們走過了幾個春秋。晚飯后的身子自然移向閱覽室和教室,待到熄燈后,被窩里的手電筒就悄悄地盛開著花朵,將一頁頁自己喜好的書翻過在明亮抑或微弱的電筒光里。寢室是一個增長學識的地方,海闊天空的知識,五花八門的信息,乃至捧腹大笑的趣事等,都在寢室里流淌著,泛濫著,可以學到書本上所學不到的東西。寢室也是個增進同學之間情誼的場所,幾年的室友生活對每一個人的了解將更深切,同學之間更有一層親近關系。盡管這些大多窩在床鋪上慢慢演繹著,有時還是目視書本、耳聞趣談的一心兩用,至今想來卻韻味悠長,猶如一首遙遠的老歌在回響。集體寢室里自有集體生活的樂趣,與同室者稍有齟齬或存有芥蒂自是很正常,別太在乎就能愉悅著一起走過大學的生活,畢竟是室友嘛,就像一片林子里挨得近的幾棵樹,樹枝總要斜伸到旁的樹上去,卻都向上生長著,樹還是樹,林更是林。
寢室是大學生活的歇息之地,也是放飛自我的自在之地。寢室的條件便不必去過分講究,有人性化的設施自然更好,用公用洗漱間公用廁所的也將就著過吧。順其自然的心情,比寢室空間的大小、有否空調電話桌椅洗漱間等來得更重要。只要能安頓自己就行,別太在意條件的好壞,猶如一艘航行的船總要途經港灣,只要能靠泊就行。
三、食 堂
兒子的大學生活已經一個月了,我最關心也最擔心他的,是吃的問題。食堂里的伙食自然成了我掛念的焦點。
兒子是個很偏食的人,這大概與我們做父母的也偏食有關,但后來的有關吃食方面的發展,卻全是他的理念和決心所致。比如吃肉,他僅吃純精的豬肉,且需紅燒的;牛排也喜吃,只是家里不會制作,只能偶爾食之;羊肉只吃與飯燒在一起的,肉上的皮呀筋呀全去得一干二凈;也曾吃過炒雞塊,后來不知為何不吃了。比如海鮮,他只吃小的蝦,水白蝦、竹節蝦、滑皮蝦,以鹽水煮為主,對蝦、基圍蝦大多只吃鹽焗的,粗壯一點的蝦就不吃,每餐飯桌上總離不了蝦;其它的海鮮中,魚類只吃紅燒剝皮魚與咸腌的馬鮫魚,偶爾也吃一點小鯧魚之類的干鲞,石鉗蟹倒也喜吃,蒸熟后的梭子蟹卻只吃一兩塊,海瓜子、芝麻螺是貝類中才吃的品種。蔬菜的種類極有限,青菜、白菜、芹菜、芋艿等而已,像是吃著苦味似的,挑揀著只吃細細的一縷。叫他多吃一點,或者能吃的都吃一些,他說人要胖起來的,要減肥。可他才一百二十來斤呀,看上去還瘦著呢,怕是看周杰倫、謝霆鋒們看得入魔了,也想做一個奶油小生吧。
其實,這樣的食譜,要說簡單也確乎簡單,菜場上皆有,烹調也無需高超技藝,了解他食欲的妻子會餐餐給他調配好;要說復雜卻又復雜得很,下不了飯時,他便寧愿少吃,尤其是到了大學里,哪有如此這般合他吃食的心意?
食堂便成為我關注的場所。
碰到兒子時,便問他食堂的情況。他們的食堂上下兩層樓,每一層看上去空曠得很,像是大會場一般,一張張桌子整齊地排列著,能讓人有一種舉辦宴會的感覺。上下層的菜價不一樣,上層的比下層的貴,比如同樣一盆蝦,下層的才四元,上層的卻要七元。七元一盆的想來必有其中緣故,比如是活蝦,新鮮一點,或者盛得滿一點,原來現在的食堂也在結合著市場經濟的手段放開著搞活呢。問他還吃得慣否,他說沒問題,每天都有蝦的。吃不好了,就到外面吃日本料理、韓國料理。雖說是偶爾去調節一下口味,卻讓我亮了眼睛,現在的學生多有口福呀。菜碟飯盆食堂里都配置著,下了課徑直到食堂即可,仿佛吃自助餐一般。最惱人的是排隊,一長串的人等候著,待買到飯菜,常常無座位了。好在二樓如無座位了,就可打包回寢室食用,還真夠方便。食堂便有著現代社會的特性,市場化中糅合著那么一縷人性化,令我感嘆連連。
那時我所讀的大學規模較小,食堂便新建在校外馬路的對面,一層平頂,圍墻將馬路擋在了外面。食堂里的方桌子想是原來師范學校遺留下來的,陳舊得只可劈柴燒火用,一張張擺在寬敞明亮的大廳里,猶如一枚枚布丁排列著,打好飯菜便只能站立在桌邊狼吞虎咽。一遇下課,便從課桌中拿出碗匙,邊急匆匆地快步趕往食堂,邊將匙子敲打著碗,一路奏響著丁丁咚咚的交響曲。排隊自是一種慣例,插隊也時有發生,直到距一格格賣菜的窗口不遠處,隊伍才安靜起來,賣菜的師傅好像除賣菜之外,還兼管著買菜的秩序。飯菜票都是學校發放,一般情況下每月基本能滿足肚子的需要,若有親朋好友到學校吃飯,那個月剩余的一兩天就得自己掏錢購買。女同學的飯菜票自是月月有余,有的送了些給需要增購的男同學,有的積蓄著到學期結束時換了白糖。我雖然也有點偏食,但除了肉類都能吃一些,即使拌過豬肉的湯汁,也不影響我的口味。食堂里的菜也如現在一般普通,只是獅子頭頂替著大排,冰凍的海鮮頂替著冰鮮的。有時實在想吃獅子頭下面浸漬過肉湯的青菜,就買一盒,將肉末拌和著淀粉什么的獅子頭送給同學。大學生活的甜酸苦辣,也將食堂濃縮成一個篇章,讓人回味。
食堂就像人生路上的一個驛站,進進出出的皆是過客。設施環境好一點也好,簡陋不潔的也罷,菜肴合胃口也好,價格貴一點也罷,就隨遇而安地將就著吧。要改善一下飲食,街上隨處都是賓館飯店快餐廳,川菜粵菜湘菜家常萊的任意挑選,連西餐廳料理館的也可隨時造訪,比我們那時的打牙祭不知爽幾倍了。
大學的食堂就是一個大驛站,就需在這個驛站里適應著生活。拿熱眼觀望,食堂里的風景將會銘記于心。
【責編 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