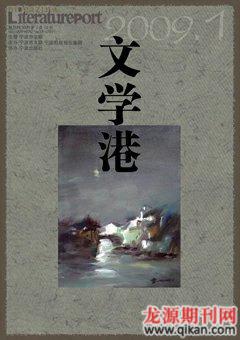堅硬的飛翔——畀愚訪談
王 姝 畀 愚
1.我看你的作品,常常感到一種堅硬的質地,就像是與堅硬的生活接觸著。你的小說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情緒、不是氛圍,而是這種質感。請問它來自何處?這些人物、這些故事是發生在你周遭的真實嗎?你怎么理解“真實”這個詞?
答:我想所謂的“質感”是小說的一個基礎之一,它來自兩個方面,對生活切身的感受與對生活無盡的想象。先說想象,我可能更喜歡那種平實的想象,就是讓想象在現實的平臺上起飛,再回落到生活這塊平臺上,或者緊貼著這塊平臺前行。想象是不存在方向的,但我又覺得想象是有根的,它深扎在生活這塊土地中,更多時候它是不需要飛翔的。反過來再說生活,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生活在很多時候遠比想象要精彩,一個小小的開端就能為我們提供無數的過程與結局。小說源于生活這句一點沒錯。至少對我非常適用。
說到這些人物與事件的真實性,我想它們基本上是虛構的,這也是小說家必備的一個技能,善講故事的人應該比好的說謊者更高明,編一個永不被戳穿的謊言。小說家的一個功能就是圓這些姑且稱為謊言的東西,讓它們在相對中具有絕對的真實性。我覺得小說就是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2、你說的“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是個很有意思的說法,而且我記得有篇小說你就取名《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怎樣成為“相對中的絕對的真實”呢?
答:我想這個“可能”與“不可能”是基于對小說的理解上的,也許是因人而異的。可我始終覺得小說這種形式為創作者提供的就是無限的可能,作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自己小說的上帝,是萬能的。在小說中只要我們想到,就一定能做得到,它可能是有悖于自然中的一切的,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這本身就是小說的一個功能,讓不可能變為可能。小說從另一個意義上創造了另一種生活,一種我們可能永遠抵達不了的生活。
3、除了生活的質感之外,我還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呈現在你文字中的生活,帶著一絲冷酷與殘忍的氣息。這與你對世界、對生活本質的看法有關嗎?
答:是的。這是生活給我的最直接的感受。也許你很難想象,但確實是這樣的。也許偶爾也會有一絲溫暖,但我相信那也是離開很遠之后一道回望的目光。當然,感受不是一成不變的,我知道我有時候也在變,但這種變化更大程度取決于我們存在的這個現實,它不冷漠了,它不殘忍了,我想一個小說家的心靈會最先感受到,也會最先溫暖起來。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感受更多的還是溫情表象下的冷漠,這可能是件比冷酷更殘忍的事。冷漠主導著大多數人的感情。可能有人會反對,但我真的這樣認為,因為我總覺得激情與溫暖在今天的現實中其實只是腎上腺素的一次發揮,而冷漠只怕是早已植根于人們的靈魂深處了。這個我們看社會新聞就不難發現。
我覺得用冷漠這個詞更合適。
4、如果說生活是堅硬而殘忍的,你筆下的人物則有一種無奈感。甚至你都不太直接寫他們內心的感受,而讓生活本身推動人物向前。他們各自有切實可行的目標,不是什么精神理想,就是最簡單的生活目標,但連這都被一次次地粉碎,只能陷入命運的再一次輪回,像《煲湯》、《羅曼史》等。你覺得你賦予了你人物什么,你對他們的態度如何?
答:我想無奈是絕大多數人在面對現實時的一種態度。舉例說:一個貧窮的人在金錢面前的無奈,一個富有的人在權力面前的無奈,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在更大權力面前的無奈,哪怕一個什么都擁有的人在健康或是死亡面前的無奈。因為我相信每個群體中的人對無奈都有切身的感受,而我只是選擇了那些人物在無奈中跌跌撞撞而已。任何一個想擺脫無奈的人都是不現實的,說得嚴重點都是有點愚蠢的。至少現實教會我的就是無奈與忍受這種無奈。
關于精神其實是我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我總覺得精神是與物質緊密聯系的,沒有物質的精神是空乏的、虛假的,至少也是不真實的。而且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很難說有高級狀態的精神,或者說價值觀。不能說今天的中國沒有價值觀,它只是很混亂,但混亂的價值觀也是價值觀,而更多的人是出于需要,在力圖推行某種所謂的統一的價值觀,但價值觀能統一嗎?
跟精神比較起來,物質生活才是主要的,而物質在今天只怕是衡量生活惟一的標準吧?我想只有當物質在生活中不那么重要了,人們才有理由去追求精神吧?可反過來說,我覺得在一個物質相對豐盈的時代里的精神跟物質貧乏時的精神并無區別。不管我們怎么去追求,用何種方式追求,都需要積淀與洗刷。我也不覺得有純粹的精神,再純粹的精神也只是一種精神。
人沒有精神只是空虛,人沒有物質卻是饑餓。而空虛是可以忍受的,饑餓是誰也忍受不了的。
在《煲湯》與《羅曼史》中我賦予人物更多的應該是嘲笑,并不是說我蔑視這些人物,因為我覺得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命運,不見得是她們走錯了路。有時候我們可以選擇道路,但行進的過程往往是不能自主的。我總覺得有時候是路在推著你往一個方向走,而且這個方向常常要走到頭了才知道早已不是你原先認定的那個方向。我想對于失敗者是這樣,對于成功者也是一樣。至少對這些人物我并沒有同情,說穿了是我逼著他們走到這一地步,我需要他們這樣,因為我覺得現實就是這樣的。
如果這些人物在現實中確實存在,我相信他們需要的也絕不是同情與憐憫。
5、還有些作品,帶了強烈的反諷色彩,敘述很具力度,像《褲腰帶》《楊角的年關》等。這是你的一種本質態度,還是一種多樣寫作風格的探索?
答:我的本質態度決不是這樣的。
應該算是一種寫作風格吧,因為除了反諷我不知道怎么面對我當時要表達的,我不是一個喜歡弄得太過沉重的人。不過,我已經改變了這種敘事,從《胭脂》、《鑰匙》還有剛完稿的一個叫《瑪格麗特》的中篇,我覺得我已經擺脫了這種敘事,我自己都有點厭煩了。這個世界還是需要溫情一點的,哪怕這個世界本身并不含情脈脈。
我覺得我的寫作正在從人與社會的矛盾中逐漸轉向,更多地關注人與人的矛盾,人與自我的矛盾。
6、張懿紅在看到上海首屆作家研究生班小說專號之后寫下了《學院派+中產階級:寫作的可能與隱憂》一文,文中提到了“中產階級寫作”的概念:“缺乏底層生活信息,多為燈紅酒綠、香車美女的小康生活圖景。作品所表達的主體精神是高級層次的情感欲求、心靈體驗等精神需要,超越生理需要等低級的基本生存需要,代表中國目前已經脫貧致富的社會階層的精神追求。……大都表現出去意識形態化的特征。”
你目前也在作家研究生班學習,但我看到你的寫作,和上述張文定義的中產階級寫作不同。在你的作品里,更多描寫的恰是底層生命的悲歡離合。然而我又隱隱約約覺得,你和近年所提倡的底層寫作、底層意識也很不相同。你在寫底層的時候,好像仍然在表達對世界的絕望與拒絕。本質上,你不是用底層題材來表達對諸如農民工、妓女、下崗等社會問題的關注,而是通過這樣一種生存狀態傳達你的疲賴、厭倦和一種荒謬感。換句話說,是用底層題材表達后現代主義式的中產知識階層意識。
你是否認可我對你作品的這種感覺?
答:首先,我不是張懿紅說的中產寫作,因為中產帶有明顯的物質條件,因此我更有理由說不是中產寫作。但我也不是所謂底層寫作,盡管曾有人將我列入底層作家行列,但我肯定不是的。我那些小說更關注的是人在現實面前的困境。這種困境對每個階層中的人都存在,它適用每個人。你那句話說得很對:通過這樣一種生存狀態傳達疲賴、厭倦和一種荒謬感。我真是覺得世界是荒謬的。
但用階層來歸類寫作也是有點荒謬的,就像用年代來命名作家一樣。
7、暴力、疾患、性等話題常常出現在你的筆下,你用一種克制而極冷靜的筆調敘述它們,唯獨沒有愛。洪治綱在評《我們都是木頭人》時,用《愛到深處是絕望》作題眼,但我總覺得他這篇批評文字還是太著眼于社會學批評,并沒有抵達你寫作的本質。你在選擇這些逸出生活常軌之外的異常事件、底層人物時,真的放棄了愛,放棄了對人類溫暖的信任嗎?
答:呵呵,這問題有點難回答,因為你是女性,所以更留意到愛?
可能我是用性來屏蔽了愛吧。我始終覺得愛是一種太復雜,太神圣的情感,更多是種感覺,不管親情、友情、男女之愛,可能能夠表現出來的愛都是有點輕率的成分在內的吧?至少我覺得都是相對有點膚淺的。不過,我已經開始挑戰它了,呵呵,《胭脂》與《鑰匙》是個開始,接下來的《瑪格麗特》也都是關于愛的。
我想在接下來一段時間,我都會寫點與愛有關的小說,而且是慢慢離開我所熟悉的小鎮生活中的愛。時間、空間決定了愛的方法與方式。生活有太多值得我汲取的經驗,變化是肯定,而怎么變可能要到變了之后再總結。
8、《胭脂》也是你創作中的異數,你突然把題材放到了近代,有點像蘇童、余華他們的新歷史小說。我覺得這篇似乎技巧性的東西大于內心的東西,但畫面也好、節奏也好,甚至人物在歷史中沉浮的無力感,都表現得很到位。似乎一部長篇的容量都讓你在一個中篇里寫完了,特別完滿的感覺,有點無懈可擊。你對這篇作品的看法如何?
答:你說得很對。我用23000字幾乎敘述一個女人的一生,我是把它當成一個電影來寫的,它的每一幕其實都可以變成畫面。有一點不知你注意到了沒有,幾乎我全部的小說都是有關尋找的,這個也不例外,但我寫它時明白了一點,尋找在更多的時候不如等待來的有力。我寫作十年了,也用了十年明白了這個道理。
9、你的結尾常常是一種“不是結尾的結尾”,好像生活還在展開著,又無從展開,無力改變。用的好的,像《羅曼史》、《白花花的茅草地》、《我要回家》、《我不是兇手》等。但有時,如果篇幅太長的時候,好像這種結尾,讓人覺得力氣一下子弱了,比如《女人》的結尾。為什么會用這樣一種結尾?
答:這個問題也有人問過我,可我答不上來。我越來越有種感受,在寫作一個小說的過程中,哪怕是個短篇,這個寫的過程也是不斷推翻自我的一個過程。等到完成后看看,發現這個小說已經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我構思時的那個小說了。結尾也是這樣,我不會去為了一個結尾而結尾,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常常會把就把一個打算好的短篇寫成了中篇,也有過把中篇寫成了小長篇的事。
我是不是要改掉這個習慣?
10、我覺得你小說的節奏控制得很好,但到目前為止,你主要停留在中短篇領域,有沒有創作長篇的打算?打算寫哪方面?
答:我曾寫過一個十幾萬字的長篇,不過那只是個拉長了的中篇,現在正準備從結構與內容上重新充實它,接下去準備寫一個真正的長篇,正在作大綱。這是個讓我充滿信心與期待的小說,因為改革開放三十年,正是我從懵懂走向成熟的三十年,從農村走向城市的三十年,我親眼目睹了它,也切身感受了它。
【責編 艾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