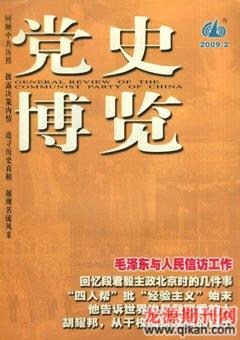我在“中央讀書班”的見聞(下)
劉 巖

遵化參觀引發了兩種思潮的碰撞
1975年6月4日,第四期讀書班學員和教職員工組成200人的隊伍,浩浩蕩蕩路經天津薊縣到達河北省遵化縣。由于路途較遠一天打不了來回,故決定用兩天時間,除參觀原計劃的西鋪生產大隊外,另外增加了“萬里千擔一畝田?青石板上創高產”的沙石峪生產大隊。
西鋪生產大隊的前身是王國藩領導的“窮棒子社”。1952年,河北省遵化縣西鋪村共產黨員?村干部王國藩,把村里最窮的23戶農民聯合起來辦起了一個初級社。社里僅有的一頭毛驢,還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權屬于沒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們把他們叫做“三條驢腿的窮棒子社”。面對冷嘲熱諷,王國藩不予理睬,帶領23戶農民發奮努力,依靠“三條驢腿”,從上山砍柴換農具做起,使生產得到迅速發展。第二年,合作社社員就發展到83戶。沒幾年,糧食畝產從120多斤增長到300多斤。王國藩合作社的名氣越來越大。
“窮棒子社”的創業之舉深深地感動了毛澤東。他寫按語說:“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23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
王國藩歷任西鋪鄉高級社主任,遵化縣建明公社社長,遵化縣革委會副主任,唐山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河北省革委會常委,中共遵化縣委第一書記,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書記;被選為第一屆全國勞動模范,第二屆?三屆?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1960年3月30日,毛澤東親自接見了王國藩。王國藩的事跡被選入當年的小學課本。他的名字在國內家喻戶曉,成為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作為時代風云人物,王國藩的生活卻非常儉樸,始終沒有改變農民形象,也沒有改變自己的農民身份。他到中央讀書班學習,穿的仍然是那身農民的裝束:黑色對襟上衣,黑色土布褲子,老伴做的黑布鞋。從1967年開始,及至擔任了一系列高層領導職務后,他仍然不脫離農村,不脫離生產,不拿工資而記工分。
王國藩在讀書班的學習討論中少言寡語,但在介紹自己的生產大隊時卻如數家珍,滔滔不絕,講得有聲有色。學員聽后,大多數覺得“受教育很深,上了一堂最生動最實際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課”,但也有少數人提出不同意見,引發了兩種思潮的碰撞。
一是如何看待生產隊之間收入差別的矛盾。據王國藩介紹,20年來,西鋪生產大隊通過改良土壤?興修水利?改進技術管理?開展多種經營等措施,增產效果顯著,當年的工分值達到2元,比其他生產大隊高出1元左右。對于這種差別,多數學員認為是正常的,屬于生產力發展范疇的矛盾,解決的辦法是搞好“傳學趕幫帶”,使后來者居上。但也有部分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法權”,屬于“階級斗爭”范疇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是“無產階級專政艱難的任務”。這種觀點的根源來自張春橋的歪論。學員參觀遵化前兩個月,《紅旗》雜志1975年第4期發表了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給“左”傾思想較重的一些人提供了理論武器。他們拿著“資產階級法權”的帽子到處扣,把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之間的差別?生產隊之間自然條件的差別?生產經營收入的差別,統統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數學員特別是絕大多數部隊學員,不贊成他們的說法。
二是如何看待王國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經歷。6月4日下午,王國藩帶領學員參觀一片被改造的農田時,在一棵大樹下即席介紹了西鋪生產大隊的發展歷史。其中提到,“文革”初期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一幫造反派跑到西鋪村,揚言王國藩領導的生產合作社是“假典型”,王國藩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煽動社員搞所謂“揭發”。經過一番折騰,實在無法找到“假典型”和“走資派”的事實根據,就說王國藩是“慈禧太后親戚的后代”,胡攪蠻纏,連續圍攻王國藩好多天,搞得無法生產和工作。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后,于1967年2月5日利用陪阿爾巴尼亞貴賓視察沙石峪生產大隊的機會,去西鋪才給王國藩解了圍。對王國藩的這段經歷,在學員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反應。大部分人認為,王國藩“頂住一小撮極左分子妄圖把‘窮棒子社砍倒,把西鋪大隊打成‘假典型的罪惡企圖,捍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表示欽佩。但少數人卻認為,這是王國藩“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不能正確對待造反派”的表現,表示反對。
“王洪文辦的讀書班”引發調查取證風潮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不久,解放軍除鐵道兵以外的所有單位和部分地方單位,紛紛派人到總政治部調查取證,刮起一陣調查“中央讀書班”學員的風潮。僅我接待過的就有上百批,被查證者達146人。為什么凡是到“中央讀書班”學習過的干部幾乎都要被查證呢?原來,軍隊某領導機關在揭批“四人幫”罪行的大會上以及會議總結?簡報等文件中,將“中央讀書班”改稱為“王洪文辦的讀書班”。讀書班的名稱問題為什么會引來全軍性的查證風潮呢?我們看了下面這個故事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1985年,軍隊整黨接近尾聲。福州軍區某集團軍王軍長在1973年當師長的時候曾入“中央讀書班”第二期學習,回部隊后一直風平浪靜,順利發展。沒有想到,在1985年底寫整黨材料時遇到了麻煩。在集團軍黨委會上有人提出,王軍長曾經讀過“王洪文辦的讀書班,但在整黨材料中沒有交代這段歷史”,因此不投通過票。當時,我的胞兄劉政(濟南軍區某集團軍原參謀長,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被全軍整黨辦公室派往南京?福州軍區“整黨調研組”任組長,參加了王軍長的這次整黨“過關”會。眼看會議陷入僵局,他忽然想到我曾在“中央讀書班”工作過,就打電話問我:“你參加過的那個讀書班,性質到底是怎么確定的?”
我告訴他:“請你們查看《鄧小平文選》第12頁《加強黨的領導,整頓黨的作風》一文的題解,題解對讀書班的性質有明確的說法。”于是,黨委會上很快有人找來《鄧小平文選》,打開一看,題解說:“這是鄧小平同志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這下子參加會議的人們才統一了認識,通過了王軍長的整黨材料。
說起對“中央讀書班”學員的調查取證,真是五花八門,一言難盡。找我們查證者,持什么樣調查動機的都有。概括起來看,可分為三類:一是持客觀態度。因為領導機關宣布了,讀書班是“王洪文辦的”,所以應當到總政治部問問情況。持這種態度的是,你怎么說他怎么聽,不帶任何框框,這是多數。二是想讓你多說“好話”。比如某野戰軍有位副政委,有人說他在讀書班期間與王洪文?七林旺丹單獨合過影。我寫證明材料說:“我沒有看見過和聽說過××與王洪文一起照過相。七林旺丹與××不是同期學員,不可能在讀書班合影。”取證者不太滿意,懇求我寫得“肯定一點,就說沒有照過”,我表示我不能保證在我的視野和聽覺以外發生的事情。第三種情況是帶著傾向性搜集材料。不按他的意圖說事,就反復提問,甚至糾纏,表示不滿。這里不妨舉兩個例子。
有一位研究所的政委參加過第二期讀書班的學習,粉碎“四人幫”后成了被審查對象。1977年11月19日和12月17日,研究所兩次派人到總政治部調查這個政委在讀書班學習時的情況。其中,除了幾件“大事”,比如關于去公安部工作的問題?王洪文是否聽取過有人對他學習情況的匯報?他在學習中是否聯系過本系統的實際?江青是否接見過他所在的工作小組等等,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進行查證是形勢所需,非查不可。但是,調查人員反復查問的另外一件事情,就使人有種“雞蛋里挑骨頭”的感覺了。他們問,1973年10月6日讀書班開學那天晚上,葉副主席點到這個政委的名字時,“問過他什么問題沒有”?對他和他所在的研究所“作沒作過什么指示”?其目的很明顯,如果葉劍英問過什么問題?作過什么指示,他回去沒有傳達,那就會給他扣上“目中沒有葉副主席”?“封鎖葉副主席的指示”的大帽子。因為粉碎“四人幫”以后,葉劍英是全黨和全國的第二號人物,軍內很多單位把對待葉劍英的態度作為區分大是大非的標準之一。這個研究所的調查人員,無疑是想在葉劍英對學員“點名”的這個“雞蛋”里,挑到一點“骨頭”來。
讀書班第二期學員中有一位海軍航空兵師的師長,性格開朗,談吐幽默,善于同人交往。1977年12月24日,海軍政治部派人到總政治部集體了解海軍曾進入讀書班學習過的12個人的情況。我和一起到讀書班辦公室工作的王復初干事經領導審核同意,向海軍介紹了包括這位師長在內的12個人的學習情況,并提供了12人所寫的“學習小結”打印件。但是,這個航空兵師的調查人員并不滿足。1978年1月7日,來人進一步查證,列了10多個問題的調查提綱。我和王復初對其中6個我們知道的問題作了明確回答,并寫了書面證明材料。1月14日,該師的調查人員又來到總政找到王復初干事,查問他們師長“跟莊則棟是否一起照過相”。來查證者是這個師的一名副師職干部,我們從他1月7日的查問中就感覺到這個人有急于將師長整下去并取而代之的圖謀。我們回答說:“莊則棟當時是世界乒乓球冠軍,國家體委主任。周總理還曾到讀書班找他談過工作。且不說我們不知道他倆是否一起照過相,就是慕名與莊則棟照了張相又算得了什么問題?”最后,這位查證者悻悻地走了,以后也沒有再來。
到公安部參加整頓和破案工作
由于公安部是專政機關,加上時任公安部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的李震意外死亡,所以公安部的事情讓大家感到十分神秘。在讀書班學員參加該部工作的問題上,三年之內兩次成為各方面關注的焦點。第一次是1973年10月讀書班組建赴公安部工作組時,受到讀書班辦公室和學員黨支部的高度重視,對去公安部工作的學員和工作人員是經過嚴格篩選才確定下來的。第二次是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讀書班學員去公安部的事情又成了一些單位清查工作的重點。部隊去公安部的9名學員都不止一次地被查證過。地方學員中幾名去公安部工作的學員,如廣東的梁錦棠?遼寧的王景升?北京的張世忠等,也有人找我調查過他們的情況。我作為行政工作人員,奉命跟隨學員工作小組去過公安部十幾次,聽過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對整頓工作和破案工作的介紹,也聽過學員工作組向黨的核心小組的兩次匯報,對面上的大體情況了解一些。這里把當時大家都感覺十分神秘而又非常重要?必須調查清楚的若干情況略述一二。
“學員去公安部是誰交代的任務?”這是每個查證單位共同提出的首要問題。學員去公安部事先并無計劃安排,是李震死亡以后臨時增加的任務。這項任務,從當時的表象看是王洪文直接交代的,但是若干年后李震之死的結論定案后,人們才知道它是周恩來最后拍板的。過程是這樣:1973年10月29日吃完晚飯,學員在上晚自習前,很多人逛商場去了。這時王洪文突然跑到讀書班,要值班的同志立即通知各小組24個召集人到小禮堂集合。我走進小禮堂時,看見王洪文已坐在一張桌子前等待。人到齊后,他開口第一句話就說:“李震被干掉了!”大家聽了都很震驚,一個個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地聽他繼續講。他說:“這個事要保密,你們不要記錄,不要外傳。李震百分之九十九是他殺。中央對李震很信任,重大案件都交給他辦,這是政治上的最大愉快,所以他不會自殺。”他還說,李震“死前情緒沒有異常,死后現場被破壞了”,等等。他說這些話的傾向性很明顯,就是一口咬定李震是他殺的。最后,他要求從讀書班學員中“劃一部分人到公安部去”,參加公安部的整頓和破案工作。
王洪文說完就從禮堂出去坐車走了。王洪文走后,辦公室的兩個負責人和兩個黨支部的領導成員立即開會,研究選擇赴公安部工作組的名單。名單確定后,從第二天開始這部分學員就不再去原來的工作單位了,而是在家里待命準備隨時出發。然而一直等了半個多月,直到11月16日才有了消息,開始進入公安部。
當時大家都很納悶,原先王洪文急急忙忙親自跑到讀書班下達任務,可是前往公安部的第十四組組建起來后卻半個多月沒有動靜,誰也猜不透是什么原因。若干年以后,被周恩來點名調往公安部參與主持破案工作后留在公安部工作的楊貴發表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才讓大家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楊貴說:“在11月1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洪文匯報了派往公安部工作的人員名單。周總理看過名單后說:‘都是工人和部隊的同志,我看還是讓熟悉地方工作的楊貴同志去吧!”原來,這半個多月是等王洪文向政治局和周恩來匯報呢。得到政治局和周恩來認可后,學員便于當天進入公安部。這就是說,第十四組去公安部過程的正確表述應當是:“派學員去公安部,開始是王洪文到讀書班布置的,最后是政治局和周總理通過批準的。”過去,曾經把第十四組學員說成是“被王洪文派去公安部”的。這樣就把他們與王洪文掛上了鉤,使他們在政治上受到牽連,在運動中被反復查證,在精神上增加了不必要的負擔,應當向他們道歉。
提到上述問題,不能不說說王洪文在處理學員問題上的另一件事情。第三期讀書班開學不久,學員中的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王建安上將身體不適,我帶醫生去宿舍看望,一量血壓,高壓200多,低壓100多。醫生說:“王司令的血壓太高了,危險性很大!”我與辦公室主要負責人商量,建議趕快將其送醫院檢查治療。但是王建安不愿住院,提出退學回福州或到總參招待所休息。辦公室主要負責人便給王洪文的廖秘書打電話,讓他請示王洪文怎么處理。過了一天,廖秘書回電話說,王洪文報告了周總理,總理指示:“王建安不要回福州,也不要去招待所,有病可住301醫院治療。”這件事同樣說明,讀書班涉及學員的較大問題時,王洪文是不能一個人說了算的,他得向總理請示報告。在清查“四人幫”時,有的單位對王洪文的權力估計過高,把“中央讀書班”改稱“王洪文辦的讀書班”,就是這種心態的產物。
“去公安部學員的名單是怎么確定的?”這是各單位查證工作中的又一個重點問題。查問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要搞清楚他們單位被查證的對象與“四人幫”一伙人有沒有瓜葛。
從軍隊學員中抽調組建第十四組的工作,是讀書班總負責人?中央組織部的牛樹聲會同總政治部在讀書班辦公室工作的四位同志一起研究的。當時研究時,在桌子上擺了三種學員名冊:一是簡歷名冊,二是學習編組名冊,三是原來參加工作的分組名冊。幾個人在這三種名冊之間翻來覆去查看,所考慮的因素主要有三點:一是在四個學習小組之間抽調要均勻,三個小組各抽2人,一個小組抽調3人;二是在13個工作小組中,從部隊學員人數相對較多的9個小組中各抽1人;三是所抽對象盡量是政工干部,并且頭腦比較靈活?反應比較敏銳。別看區區9人,挑選?搭配起來還真費了一番周折。
“學員去公安部后干了些什么事情?”10月29日深夜,兩個黨支部討論通過所抽調的18位學員名單后,前往公安部的第十四組宣告成立,確定了兩名牽頭人: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三軍副軍長張英才,中央候補委員?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總工會副主任張世忠。下面分編為9個小組,每組由軍隊和地方各一名學員組成,規定進入公安部后以小組為單位活動,個人不得單獨行動,不得隨便表態,不得暴露公安部的秘密。待命半個多月后,11月16日牛樹聲親自將第十四組送到公安部,首先在會議室互相介紹了雙方的有關人員,然后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的同志向學員介紹了李震之死的有關情況,并帶領大家察看了李震的辦公室和死亡現場。
讀書班學員進入公安部之前,李震案件的偵破工作已經開始。參加偵破工作的,除公安部本單位的人員外,還有從廣州?天津?上海?北京借調來的偵破專家。由于王洪文竭力堅持“李震是被階級敵人謀殺的”,所以對一些與李震有關系的人員都進行排查,要求每個人說清楚李震死亡前后幾天自己在做什么?都和哪些人有過接觸?發現過什么可疑現象,等等。公安部機關上上下下都非常緊張。學員在調查研究中開始聽到的基本上是“他殺”的聲調,后來張英才參加了華國鋒主持的一個會議后,回來給大家打招呼說:“對于李震的死,以后不要說死了,他殺?自殺兩種可能性都有。”這以后,學員們聽到的就是兩種聲音了。
12月30日,讀書班學員撤出公安部時,李震死因尚未能作出結論。以后從楊貴發表的文章看到,他和技偵專家經過艱苦細致的反復論證,李震自殺的結論無可置疑。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央正式批準了公安部破案組關于李震自殺案件的報告。
上海組學員到總政治部“放火燒荒”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在動亂歲月——從軍長到黨中央副主席》一書提到:“江青‘放火燒荒,在總政治部的火很快點起來了。王洪文專門派了參加中央讀書班學習的上海金祖敏?周麗琴?萬桂紅?單文忠等人進駐總政治部,直接參與批林批孔運動。”“中央讀書班”上海組個別學員進駐總政治部搞“批林批孔”,從事先的陰謀策劃到進入后的不正常活動,鬼鬼祟祟搞了好多見不得人的名堂。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我多次予以揭露,但由于受種種復雜因素的干擾,沒有能夠充分曝光。他們在總政的“放火燒荒”中暗中搞了些什么活動一直是個謎,我當時所揭露的只是從外表上看出來的四個問題。
一是上海組進駐總政,是王洪文在背后陰謀策劃的。第二期“中央讀書班”開學不久,中央組織部按照有關方面的決定,開列出本期學員參加工作的10個單位,讓辦公室提出各小組分配所去單位的意見。3月18日晚辦公室研究時,大家的一致意見是依照學習小組和所去單位排列的對應順序確定。與上海組相對應的單位是總參謀部,與總政治部相對應的是沈陽組,這樣上海組就分到了總參謀部。19日上午,辦公室總負責人王桂冀找到我說:“老金(金祖敏)提出,他們小組參加工作的單位變一下,改去總政。”我說:“這個組去總政不合適吧。他們組有十二軍副軍長任保俗,現在總政正在揭批李德生和他老婆曹云蓮,最近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李寶琦(總政原組織部長)也被揪回總政參加運動去了。他們都是十二軍的熟人。過去搞土改,工作隊有熟人都要回避,上海組也應當回避吧?”王桂冀聽后說:“是嗎?那給老金說說吧。”不一會兒,王桂冀從金祖敏住的學員樓回來了,對我說:“老金說了,任保俗只是個組員,不負責全組的工作,去總政沒關系,還是按他的意見辦吧。”當天下午,學員支部召開支委和小組長聯席會,金祖敏宣布各小組參加工作的單位時,把10個組工作單位的分配都說成是“辦公室建議”,明目張膽說假話。
二是排斥異己,將陳再道?任保俗趕出第四小組。任保俗回避總政運動本來是我首先提出的,目的是將我不同意上海組去總政作為一種方法,來表明我對上海這幫人的政治態度,根本就沒有打算能夠阻止他們的圖謀。果不其然,3月28日晚上,金祖敏在幾個小組召集人“碰情況”的會上突然提出,他們組的陳再道?任保俗總政熟人多,工作不方便,建議調整。我心想:“不是說不妨礙嗎?”王桂冀也只好無奈地打電話請示中組部郭玉峰,郭表示同意。經辦公室研究確定,任保俗調到天津蔡樹梅小組,陳再道改去總參政治部參加那里的“批林批孔”運動,歸孫玉國小組領導。
三是違犯保密規定,拒絕上繳去總政工作的筆記本。各小組學員參加工作的筆記本都是專門編號發放的,事先明確規定,工作完畢要統一收回繳保密室登記處理。但是,上海組去總政參加運動的筆記本一直不上繳,保密員王長順向我反映,我讓他催繳。催了幾次還是拖著不繳,我便將情況反映給王桂冀。不知道王桂冀是怎么給上海組說的,不久王長順告訴我說,“四組的筆記本他們自己銷毀了”。這里面如果是光明正大?沒有鬼的話,怎么能違犯保密規定“自己銷毀”呢?
四是參加總政運動的工作報告,違犯規定徑送王洪文。各學習小組參加運動的工作報告,規定所寫內容辦公室沒有過問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向中央呈送時,應一律通過辦公室的機要室登記,然后通過機要交通上送。其他各組都是這樣執行的,唯獨上海組對參加總政運動的幾次報告都搞得十分詭秘,既不在機要室登記,也不通過機要交通上送,都是他們自己秘密地單線直接送給王洪文,很不正常。
粉碎“四人幫”后,上海市委?安徽省軍區等單位派人到總政治部調查周麗琴?萬桂紅?單文忠?王樂亭等人到總政治部“放火燒荒”的問題。總政“清查辦公室”每次都不例外地批上“請劉巖同志接待”。我每次都只能重復我從外表上看出來的上述四個方面的問題。“四人幫”在總政“放火燒荒”的主要目標是整李德生?田維新等人,我是跟李德生從軍委辦事組到總政工作的,人家把我劃在“李德生線上”是盡人皆知的事。擔任上海組教學工作的中央黨校教員周養儒?王儒化就曾聽金祖敏說過,“劉巖根本沒有資格來中央讀書班工作”。事實上正是這樣:他們每次到總政機關,所依靠的都是少數“左派骨干”,根本不與廣大機關干部接觸;我是人家的對立面,他們與我格格不入,處處設防,背后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怎么可能知道呢,只有“左派骨干”知曉。然而,“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左派骨干”,一部分人在揭批“四人幫”時仍然還是骨干分子,如果徹底清查上海組到總政“放火燒荒”的問題,勢必“拔出蘿卜帶出泥”。這是上海組到總政治部“放火燒荒”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清查的根本原因。
我干了兩件涉及江青的“玄乎”事
我參加“中央讀書班”辦公室工作期間,江青是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按政治局的分工,她不管讀書班的事情,也從來沒有到過讀書班。但我卻干了兩件涉及江青的“玄乎”事。
第一件,向組織提出吹捧巴結江青的××學員不宜提拔。1974年1月25日,第二期讀書班學員行將結業時,江青在中央直屬機關兩萬人(包括讀書班學員)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聲嘶力竭地喊叫:“孔孟之道有三綱五常,其中一綱就是對著我們婦女的!”1月27日,在政治局接見讀書班學員的會議上,她把兩天前叫嚷“孔孟之道……是對著我們婦女的”的起因抖摟了出來。她在會上宣布,河南省唐河縣有個女初中生(張玉勤),因為外語考試不及格,遭到批評,想不通投河自殺了。她說女孩子是被“孔孟之道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回潮逼死的”,高聲呼喊“我要向全國控訴”!
1974年3月,第三期讀書班開學后,“張玉勤事件”的余波尚未過去。部隊學員中有一個特種兵師的政委,從第二期學員那里得知江青的上述表演后便投其所好,注意搜集積累《內部參考》上登載的關于全國婦女“受迫害”的資料,準備在婦女問題上做文章。為了討好江青,他對讀書班中的婦女學員進行了專門的調查統計,在“學習小結”中寫道:“這期中央讀書班17名女同志中,有11名中委和候補中委,其他有省?市團委書記和各級負責同志。”同時在小結中不惜篇幅?不厭其煩地引用全國各地所謂“迫害婦女”的事例,比如:“有個生產隊,婦女因婚姻不自由,一條繩子吊死三個”;“湖南省漢壽縣一個‘鐵姑娘小組,因得不到同工同酬受歧視,九人集體自殺”;“吉林省發生一起嚴重的拐騙販賣婦女的案件”,等等。他別有用心地寫道:“如果這種陳舊的東西發生在上層,它對革命的危害就更大。”影射之意,昭然若揭。更為離譜的是,他超出了當時“四人幫”的輿論調子,吹捧江青說,“批林批孔”運動這個革命烈火“是敬愛的江青同志親自點燃的”!
我看了他的這篇小結后感到很不正常。作為一個部隊的師政委,黨和軍隊的很多事情不去寫,偏偏在婦女問題上做文章,明顯是為了討好江青,圖謀得到江青的青睞。所以,讀書班結束后,我便將這篇“奇文”交給總政干部部的領導同志過目,目的是引起部領導對這個人的注意。1975年8月,全軍調整領導班子,這個師政委不知是什么人提名,被破格提升為某兵種副政委。我得知這個消息后,在命令尚未公布之前,帶著他的“學習小結”找到新上任的總政干部部部長梁濟民,說:“請你看看這篇東西。這個人品質不好,企圖通過寫學習小結吹捧和巴結上面的什么人(當時不敢直呼江青的名字),這樣的干部不宜重用!”梁部長接過“學習小結”,答應看看。第二天,他將材料退給我說:“軍委和黨中央已經批準這批干部的任免,不好改變了。”
第二件,主張退回江青在天津的講話材料。1974年6月底,讀書班機要室莫明其妙地收到天津市委寄來的150份江青在天津的講話材料,經過查問,原來是讀書班辦公室值班員擅自向天津市在讀書班學習的學員要的。天津的這位學員雖然是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天津市委和市革委會的領導成員,但她是名紡織女工,是以勞動模范的條件進入領導層的,缺乏機關工作經驗,糊里糊涂地轉述了索要江青講話材料的電話。事情的過程是這樣:她和邢燕子等天津的學員收到市委寄給她們有關江青在天津講話的材料后,到讀書班值班室給天津市委打電話(整個讀書班只有這一部能打長途的電話),告知江青在天津講話的材料收到了。值班員在一旁插話說:“也給讀書班其他學員每人要一份吧。”天津的這位學員不假思索地把值班員的話順口傳了過去,并說是“讀書班辦公室要的”。
7月2日,事情的原委搞清楚以后,我向辦公室總負責人提出:“年初‘一?二五大會上批林批孔動員的講話錄音和材料,毛主席不準下發(其中有江青的插話)。江青在天津的講話我們要來發給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就等于是通過我們這個渠道把江青的講話材料發到全國了。所以我覺得讀書班絕對不可以干這種事情。”總負責人問:“那怎么辦呀?”我向他建議,將辦公室有關人員召集起來開個會,指出值班員擅自向天津學員要材料是錯誤的,要他作出檢討,并向天津的學員說明情況,收回索要材料的意見,把材料退還天津市委。但是,總負責人顧慮重重,說:“這可是件大事,得請示王副主席確定。”于是,他向王洪文辦公室作了報告。
7月3日,讀書班辦公室總負責人告訴我,王洪文辦公室回話了,答復是:“請讀書班辦公室定。”王洪文在這里耍了滑頭:毛主席5個月前的批示在案,他不敢公然違背“最高指示”,同意給來自全國各地的100多名學員散發江青的講話,但骨子里又希望擴散“四人幫”的東西,如果讀書班辦公室決定發了,以后萬一出了問題,他可以把責任推給下面。
如何執行王洪文的上述答復,讀書班辦公室當即進行了研究。我旗幟鮮明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其他幾位同志也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這樣就讓機要員王長順將江青在天津講話材料原封不動地退還給了天津市委。(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