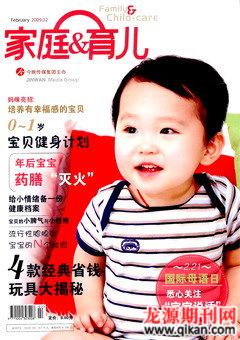讓兒子當一回“媽媽”
桂 陽
晚飯后,兔媽媽對兔寶寶說:“孩子,媽媽要備課,你自己玩好嗎?”兔寶寶點點頭:“好啊!”玩什么呢?兔寶寶東瞅瞅,西瞧瞧。看電視吧!電視機“啪”地打開了。唉!沒完沒了的廣告,無聊!彈琴好了。兔寶寶坐在琴旁,邊彈邊唱:“門前大橋下,游過一群鴨,快來快來數一數,二、四、六、七、八……”
“噓,小聲點。”兔媽媽把食指放在嘴邊。
“噢!”兔寶寶吐了吐舌頭。那么,做什么好呢?有了,建一座動物樂園,多有趣呀!于是,免寶寶用積木搭起了動物園。兔媽媽高興地伸出大拇指說:“OK!”
這是舞臺上的童話劇嗎?不,這是我家的一個保留節目。劇中的兔寶寶由兒子扮演,我呢,自然就是“兔媽媽”了。從兒子三歲起,我們就時常在家里演出類似的童話劇。兒子樂此不疲,一遍之后,他總愛要求說:“媽媽,再演,再演。”因為我要備課,所以也樂意“客串”備課的兔媽媽。
一個星期天的午后,我突然靈機一動,對兒子說:“今天咱們演童話劇,你來演媽媽,我來演你,怎么樣?”兒子一聽這么新鮮,滿口答應。
找來了幾個小碟、小碗,兒子又去屋外弄了些青菜、石子兒,然后翻出他玩具箱里的玻璃球、積木塊之類,開始準備“晚餐”。只見他又是“淘米”,又是“洗菜”,忙得不可開交,我則悠哉游哉地坐在沙發上擺弄起小布熊來。
過了一會兒工夫,我喊道:“媽媽,我的電子狗哪去了?”
“自己找找。”
“我找不到。你得幫我找!”
兒子匆匆從“廚房”沖進他的小房間,找了電子狗遞給我。少頃,我又喊:“我要畫畫,我的水彩筆呢?”兒子這時還不急不躁,真像個好脾氣的“媽媽”,只見他停下手中的“活兒”,找來水彩筆。順便還拿了一張白紙,一塊兒放到我的面前。我裝模作樣地畫了起來。過了一會兒,兒子歡快地叫著:“寶寶,快來吃啊!飯熟了,噴噴香呢!”
“不嘛,我還想再玩會兒。”
“快來吧!要不飯就涼了。”
“等一下,我畫完這只小鹿就來。”接著我又說,“我要吃雪糕。”兒子拿著他的零錢匆匆跑出去。看著他認的玩具娃娃衣服破了,你給我補補吧!兒子找了一根針,扎了一下就遞給我。我說:“這么快,肯定沒補好。”兒子不耐煩地接過去再“補”。這時我讓兒子給電子狗上發條,兒子說:“你自己上。”我說:“我上不動。”兒子無法,只好接過去上好。當他正想再繼續他的縫紉工作時。電子狗停止了走動。我又把它遞給兒子,兒子已是氣哼哼的了,但是只好再上一次。如此三番兩次,看兒子已有些受不了,這時我又故意說,飯煮糊了,快去看啊!兒子終于再也忍不住說:“還是你做媽媽吧,做媽媽太辛苦了!”
這次的游戲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生活中,我們凡事總是先想到孩子,而孩子卻很少能夠關心和體貼我們大人。但其實,不是孩子不懂愛,不會愛,而是年幼的他們,往往并不理解我們的愛心和艱辛。我發現,自那次以后,兒子的愛心似乎被觸動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感冒發燒,頭疼得厲害。兒子找來了感冒藥,端來了水,看著我服下藥后,一本正經地說:“媽媽,給你一個吻吧。”說完在我額頭上親了一下。看我不解,他認真地說:“您不是說,愛就是力量嘛,這樣你的病就好了。”我心中一陣激動,感覺頭疼似乎真的輕了許多,我捧著他的小臉蛋說:“是的,我已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