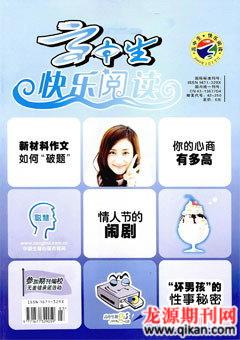奧運長卷春意鬧
佚 名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所展示的中國畫長卷,共有五幅中國畫,其中有兩幅是春景畫,它們是《游春圖》和《清明上河圖》。
《游春圖》的作者展子虔是隋朝的大畫家,擅長畫山水人物,《宣和畫譜》稱他的畫作“咫尺有千里趣”。
細細打量著《游春圖》,我突然覺得我們離自然越來越遠,離“青是山、綠是水”的自然似已隔了一千多年,讓人無端生出郁悶來。面對這樣一幅陌上桃花、江山樓閣、如夢似幻的宏大畫卷,我一時間竟然不知道哪個才是真正的文明了。是我生活的這個現實,還是這幅一千多年前的畫?
《游春圖》的作者以詩人的敏感、細膩的筆觸,畫出早春二月桃李爭艷而又略帶微寒的風景。放眼遠眺,只見青山聳峙、江流無際、萬木爭榮、祥云涌起:細細觀賞,則見坡岸綠了,桃花、杏花開滿了枝頭。游春的人有騎馬的,有踏歌的,個個怡然自得,安適恬靜,人馬一路逶迤,綿延數里。青山外,丘壑深藏,不知有多少勝境。此圖表現出可游可居的詩意,作者手中筆和心中氣是天機,而不是人意。作者的心要清澈見底,才可以這樣輕輕地把人物安于自然中,小如盈豆,而不覺得委屈。
道家說:天地之心本靜。在《游春圖》里,我看到了靜,靜得無悔意,無造作,人也似菩薩的臉,渡過了生死流浪的海,而后若仙。莊子認為人與大自然本為一體,這一思想正是中國山水畫的靈魂所在。
《游春圖》的出現,結束了山水畫的幼稚階段,使其變得青山綠水和工整細巧。這幅經宋微宗題寫為“展子虔游春圖”的畫卷,是畫家傳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為止存世最古的山水畫。
《游春圖》是山水畫中的一個奇跡,奇在已隔了千秋的天意人世,奇在那千秋不變的春意。
觀《清明上河圖》讓我想起一句話:“有限的社會蘊含無限的風景,便是人世。”
每當我寫作時沒有了思路,沒有了感覺時,我便會打開《清明上河圖》,看一看,尋一尋,只見畫上農民在田里耕作,有些人掃墓歸來,路上的馱隊、挑夫、騎馬坐轎的正匆匆進城。汴河上的拱橋如一道彩虹,橋上行人如潮,橋下舟楫相爭,橋頭一匹毛驢被驚嚇,好奇的人在圍觀。城中官府衙門、民居宅院、作坊店鋪、茶肆酒樓,街上車水馬龍,三教九流,百業興隆,熱鬧非凡。我故事里的人物都遺落在哪條街巷、哪家院落?尋常巷陌有笑語聲聲,畫堂朱戶里有賞心樂事。我書里的很多人物都來自于此幅長卷中的深深庭院里。
我想象著宋詞里所有的驚艷與悱惻事,都曾在這里發生,有跌宕,有收尾。我便覺得宋詞的意窄,就又跑過來看看這畫,覺得它更真實,更開闊,更安穩,因為里面不全是才子佳人,還有人生百態。
小時候聽劉蘭芳的評書,記得她是這樣描述城中的繁華處的:有騎馬的、坐轎的、推車的、擔擔的、鋦鍋的、賣炭的、賣蔥的、賣蒜的……我便覺得那真是個好溫柔的去處,是禮樂的人世風景。騎馬坐轎之人與販夫走卒互不相侵,各自相安,各有秩序,這溫柔世景是在人的內心深處的。因為父慈子孝、夫愛妻敬、兄友弟恭,人人都有一個“名”,名必對應、平衡、得宜,人的內心相對平衡安穩,才可能這樣挑著擔子、提著籃子等從容地討一份生活,而不覺得貧賤愁苦。迢迢的人世大道,我從《清明上河圖》里看得到。
我寫古人的故事,總會想起此畫的作者張擇端,覺得他給我布了一個局。我只能讓我心里的人物走出來,在他的畫閣高樓處,聽聽葉底黃鸝的一兩聲叫喚,銷銷魂罷了。我一直試圖找到張先塵香拂馬的城南道,看他在哪里就能如此輕易地遇到了佳人謝媚卿。那佳人在車子里只不過探出頭來,微露了一下臉,就被他看到,于是想象出“斗色鮮衣薄,碾玉雙蟬小”。自此城南一面,佳人難覓,才子夜夜聽那窗外琵琶聲,便入了相思調。宋徽宗夜會李師師時,也曾打馬走過那條街。師師樓里,周邦彥藏匿于屋內,聽著兩人對語,調侃出那首有名的《少年游》:“……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歲月倏忽逝去,風物變遷,人事散盡,不散的只有張擇端這絹上的滾滾紅塵,迢迢遠道,讓人恍然覺得清風明月依舊。
(摘自yzdsb.hebnew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