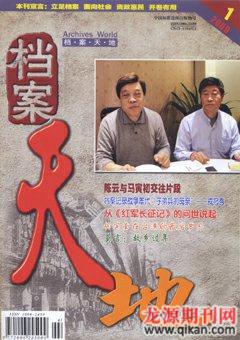愛國詩人聞一多與高孝貞
王樂飛
1912年,14歲的聞一多考上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時,父母為他訂了婚。對象名叫高孝貞,1903年出生在一個官宦家庭,和聞家還是姨表親。聞一多考取清華后,高孝貞的父親認為這孩子有出息,便主動提出要將女兒嫁給他。親上加親,又是門當戶對,聞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便訂下了娃娃親。當時聞一多埋頭學習,并積極從事校內的各種文學藝術活動,對此事并無多大考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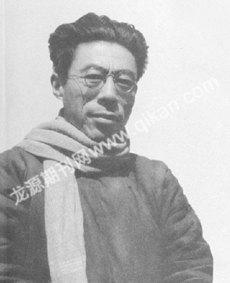
但是聞一多快畢業了,問題來了:父母怕他出國留學,就拴不住了;即便回來,也是二十七八歲了,太大了,而且要讓高家的小姐在閨中等四五年,也不好交代,因此多次來信,催聞一多回去結婚。
然而,在1921年底,一封封催他回家結婚的信從家鄉湖北浠水縣寄到清華園,使聞一多陷入極端的苦惱之中。聞一多據理力爭,無濟于事,這對聞一多是個極大的打擊。
聞一多回故鄉浠水結婚時,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禮,不鬧洞房等條件。父母可能約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所以同意。結婚那一天,一早起來他又鉆進書房看書,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給他理了發,洗了澡,換了衣服,但一轉眼他又不見了。當外面鼓樂齊鳴,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轎已抬著新娘回來時,卻到處找不到新郎,原來他又鉆到書房看書了。大家七手八腳,連推帶拉,才把他擁到前廳舉行了婚禮。聞一多的這種態度,也可以說是對父母包辦婚姻一種無可奈何的消極抵抗。
蜜月期間,他對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熱心于詩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兩萬余字的論文《律詩的研究》。他對婚姻的不滿也并未因結婚而消減。聞一多雖然對婚姻極端不滿,但仍然對妻子采取關心和負責的態度。蜜月過后,高孝貞按習俗回娘家,聞一多于回校途經武昌時,專門寫信給父母,要求讓高孝貞早日回來讀書。
聞一多一向很尊重父母,講話很注意分寸、禮節,但這封信言辭相當激烈、尖銳,足見他對高孝貞讀書問題十分重視。在他的懇求下,父母后來送高孝貞進入武昌女子職業學校。
1922夏聞一多赴美后,繼續關心妻子的學習情況,寫家信時經常詢問和叮囑,而且從精神上鼓勵妻子要有志氣,努力成為一個有學問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舉美國著名女詩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為例,說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學問、大本事,我們美術學院的教員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國女人是這樣,中國女人何嘗不是這樣呢?”
1922年12月21日起,聞一多在美國以五天的時間寫成了包括42首詩的組詩《紅豆》,其中充滿著纏綿悱惻的對妻子的深情思念。應該說,《紅豆》組詩所表達的感情也是真摯的。也許是遠居異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許是承認已婚的事實,理智戰勝了感情?也許兩者都有?但有一點是明確的:聞一多認識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強迫的“嫁接”,都是被“供在禮教底龕前”的“魚肉”,所以對妻子就產生更多的共鳴和同情,從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人本來就是復雜而矛盾的。內心世界十分豐富、感情十分敏銳的聞一多更是如此。他身上存在的許許多多矛盾,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矛盾,東方傳統倫理觀和現代愛情觀的矛盾。他在這許多矛盾中,在自己靈魂的深處,苦苦地搏斗。
聞一多來到美國這個被稱為“自由戀愛的王國”以后,接觸女性機會多了,是否浪漫起來了呢?他在上述致梁實秋的信中說:“到美國來還沒有同一個中國女人直接講過話,而且我真不敢同她們講話”。至于美國姑娘們,他說:“我看見她們時,不過同看見一幅畫一般。”
沒有浪漫過,但感情卻起過一些波瀾。聞一多到美國學的是美術。1924年9月,他轉學到紐約藝術學院,但這時他對戲劇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熱衷于參加中國留學生的戲劇活動。他同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新朋友排演英文古裝劇《楊貴妃》,后來又曾專程赴波士頓協助梁實秋、謝冰心、顧毓琇等好友排演《琵琶記》。
1924年10月,聞一多在給梁實秋的信的最后抄了一首他創作的英文詩以表達對妻子的思念,他還在附言中寫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梁實秋后來在《談聞一多》中談到這首詩時說:“本事已不可考,想來是在演戲中有什么邂逅,他為人熱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總是戰戰兢兢的,在萌芽時就毅然掐死它,所以這首詩里有那么多的凄愴。”
1925年夏,聞一多提前兩年回國,先后在國立藝專、國立政治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武漢大學等任教。1930年8月,應青島大學校長、好友楊振聲的邀請,聞一多和梁實秋一起去青島大學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聞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中文系有位女講師方令孺,教《昭明文選》,又好寫詩,常向聞一多請教。聞一多對她印象很好。當時他們在青島過得很瀟灑。首先由楊振聲提議,每周末聚飲,參加者有聞一多、梁實秋、趙太侔等七位男士。后聞一多提議方令孺加入,湊成酒中八仙之數。
1931年1月,上海《詩刊》發表了聞一多的長詩《奇跡》,徐志摩看了非常興奮,說聞一多是“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他寫信給梁實秋說,此詩是他幫聞一多擠出來的。原來,自從1928年《死水》詩集出版之后,聞一多很久沒有寫詩,好像悄然從詩壇引退。徐志摩很著急,常去信催。現在《奇跡》出來了,他便以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實秋后來在《談聞一多》中說:“志摩誤會了,以為這首詩是他擠出來的……實際是一多在這個時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點漣漪,情形并不太嚴重,因為在情感剛剛生出一個蓓蕾的時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內心里當然是有一番折騰,寫出詩來仍然是那樣的回腸蕩氣。”有人推測,這“一點漣漪”,大概是指聞一多與方令孺之間的關系。
所謂“詩無達詁”。《奇跡》一詩,采用了象征主義的手法,因而詩中的“奇跡“究竟指什么:是真理還是理想?是美還是愛?曾引起過種種的揣測和聯想。這是一首有48行的長詩。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著,不管等到多少輪回以后——”終于,“奇跡”出現了!“我聽見閶闔的戶樞砉然一響,傳來一甩衣裙的窸窣,那便是奇跡——半啟的金扉中,一個戴著圓光的你!”這是否就是梁實秋所說的感情上的漣漪呢?讀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斷。
聞一多和方令孺的來往,引起了一些流言,聞一多也覺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來青島,流言不辟自滅。
1925年聞一多回國到北平國立藝專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兒立瑛接來北平,從此開始過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貞當上了小家庭主婦,雖然比較累,心情卻舒暢多了。
高孝貞是獨生女,她的父親思想開明,不讓女兒纏小腳,讓她和男孩一塊玩和讀書,因此她習慣于自由,活潑開放。嫁到聞家后,受到大家庭的諸多禮教約束,不太適應。現在來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興,對丈夫的照顧也熱情主動。家務之余和丈夫一起讀讀唐詩,逗逗女兒,生活自有一番樂趣。夫妻恩愛親密,進入了婚后戀愛的佳境。
1926年7月,因時局變化,人事糾紛等關系,聞一多離開藝專,攜家眷離開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漢、青島等地任教,和妻子時聚時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華,才過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長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個兒子(立鶴、立雕、立鵬)和兩個女兒(聞名、聞惠羽)。聞一多當時的薪水不菲,住房寬敞,環境幽美,他決心好好教書和研究學問。每周六晚上常帶上全家去禮堂看電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頤和園,或游北海、故宮和動物園,家庭中充滿了幸福溫馨的氣氛。
但是,這樣的日子只過了五年。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日寇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聞一多的家庭,像千百萬中國人的家庭一樣,也被迫顛沛流離。
這年6月間,北平輔仁大學聘請聞家駟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來平,高孝貞攜兩個大兒子隨家駟回湖北探望久別的母親,聞一多則帶著三個小兒女留在北平。7月7日盧溝橋炮聲一響,把他們一家分隔兩地,高孝貞很著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電報,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帶孩子們回武漢。聞一多在北平也焦急萬分:走還是不走?要走,平漢路已不通,只能輾轉走別的路線,兵慌馬亂,路途艱難,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淪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設想。在舉棋不定,心亂如麻的時候,他拿起筆來,于7月15、16、17日接連給妻子寫信,傾吐在危難時刻對妻子的思念和摯愛:“這時他們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在屋里,靜極了,我在想你,我親愛的妻。我不曉得我是這樣無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樣。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罵一個學生為戀愛問題讀書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樣。這幾天憂國憂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邊。親愛的,我不怕死,只要我倆死在一起。”
信發出后不久,聞一多便毅然帶著三個孩子和保姆趙媽,經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時,清華和北大、南開都遷至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臨大)。聞一多接到清華校長梅貽琦的信后,決定推遲按規定應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長沙任教。臨大開學僅兩個多月,戰局急劇惡化,三校又奉命遠遷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聞一多利用寒假從長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關事宜。途經武昌時,老友顧毓琇來訪。顧時任教育部次長,邀請聞參加正在組建的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工作。聞一多認為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興趣,斷然謝絕了。回到浠水說起這件事,高孝貞非常生氣。她希望丈夫能接受這項工作,可以在漢口留下來,和她一起照顧家庭。她擔心萬一日本鬼子打來,要逃難,她一個人帶著五個孩子怎么辦?所以她反復懇求丈夫留下來,但聞一多橫下一條心,就是不答應。她越想越生氣,悶著頭流眼淚,飯也不吃,話也不說,甚至聞一多啟程回長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與丈夫告別。丈夫走后,一個月也不給他寫信。
妻子氣成這樣,聞一多心中也很難過。途經武漢時,他匆匆寫了封便函,請妻子原諒。后來又多次寫信回來,叮囑妻子和孩子們各種注意事項。但是高孝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寫,也不叫孩子寫。這可是對聞一多最嚴厲最殘酷的懲罰。他本是個感情十分豐富的人,如今戰亂時期,不知家中會發生什么情況,心里更是牽掛著急。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責備孝貞和孩子們不寫信來:“何以此次狠心至此!”
1938年2月15日,聞一多又寫了封長信向妻子解釋,說:“這里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學校的教職員,不下數百人,誰不拋開妻子跟著學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沒有就漢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實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應該勉強一個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這封信寫給你,有用沒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轉意,我又有什么辦法?兒女們又小,他們不懂,我有苦向誰說去?”最后說,自己就要隨學校到昆明,“如果你馬上就發信到昆明,那樣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當我已經死了,以后也永遠不必寫信來。”
高孝貞本來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慪氣。現在丈夫來信,把道理講清楚了,而且把話說到“當我已經死了”的程度,她心軟了,馬上寫信。自己寫,也讓孩子們寫,寄到昆明。聞一多和聯大師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離開長沙,經湘黔滇三省,行程3342里,其中步行2600多里,于4月28日抵達昆明。當天聞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歡喜得不得了,馬上回信報告步行的經過,還說:“我的身體實在不壞,經過了這次鍛煉以后,自然更好了。現在是滿面紅光,能吃能睡,走起路來,健步如飛。”寫這些,為的是讓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夠,西南聯大文法學院暫駐滇南蒙自。5月4日,聞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說:“到此,果有你們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賞,于愿足矣!你說以后每星期寫一信來,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來,我發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關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結束,和好如初。雖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東浠水,遠隔萬水千山,但兩顆心貼得更緊了。
日軍占領上海、南京后,繼續西犯,進攻武漢,氣勢洶洶。浠水在武漢之東200多里,是進攻武漢必經之路。孝貞和孩子們怎么辦?聞一多非常著急。逃還是不逃?不逃,日軍野蠻殘暴,后果不堪設想。如果逃,怎樣走?千山萬水,艱難險阻,帶著五個孩子的孝貞身體孱弱,又怎能擔此重擔?憂心如焚的聞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詢問和商量。逃難的多條路線、多種方案都考慮過了,不是有困難,就是有危險。可憐的聞一多萬般無奈,只有寄希望于蒼天了。在6月13日給妻子的信中說:“我一生未做虧心事,并且說起來還算得一個厚道人,天會保佑你們!”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機會終于來了。聯大外語系聘請聞家駟前往昆明任教,這樣孝貞和孩子們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們途經武漢,7月中旬到達長沙,下旬坐汽車前往貴陽。聞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趕緊寫了一封信,寄到貴陽朋友處請代轉給高孝貞,信中說:“……這些時一想到你們,就心驚肉跳,現在總算離開了危險地帶,我心里稍安一點。但一想到你們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來想去,真對不住你,向來沒有同你出過遠門,這回又給我逃脫了,如何叫你不恨我?過去的事無法挽救,從今以后,我一定要專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氣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這封信是聞一多給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書,勝似情書,字里行間滲透著聞一多對妻子的一顆赤誠的心。
同年8月,聞一多到貴陽接家屬,順便在貴州中學教師暑期訓練班講學。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聯大的文法學院也從蒙自搬回來了,聞一多開了《爾雅》、《楚辭》等課程。
經歷了半年多的緊張、焦慮、恐懼之后,聞一多一家總算團圓了,但還遠遠沒有安定下來。
主要是為了躲避日機空襲,聞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為主婦的高孝貞,帶著一大群孩子,擔驚受怕,辛苦操勞,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對家庭生活最經常最巨大的威脅還是物價不斷飛漲。
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為350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種津貼合計,只相當于1937年的8.7元。因此,聯大教授當時都貧病交迫,破衣蔽體,食難飽腹。聞一多要養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經常在半斷炊的威脅中度日。飯碗里半月不見一點葷腥,糧食不夠,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幫。豆腐被稱為白肉,偶爾吃上一點,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營住時,村外有一條小河,高孝貞常帶著孩子下河撈點小魚小蝦。后來她還開了點荒地,種上蔬菜。1940年冬天,書籍衣物典賣已盡,聞一多無奈,脫下自己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賣行寄賣,結果自己凍得發了高燒。高孝貞又心疼又著急,流著眼淚讓大兒子連夜從郊外趕進城,把大衣贖了回來。
越是艱難的歲月越見真情,聞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堅牢了。住在郊外的幾年,聞一多一般每周進城到學校上課兩天,頭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來。附近雖有馬車,但為節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來那天,高孝貞早早就把家務安排好,飯菜準備好,然后帶著孩子們到村邊等候。聞一多一出現,孩子們就飛快投入父親的懷抱,你搶書包,我抓手杖,好不高興。聞一多一邊回答孩子們的提問,一邊給妻子講路上所見和城中新聞。晚上,或教孩子們背唐詩,或講屈原的故事,其樂融融。
聞一多沒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歡喝茶、抽煙。隨著物價暴漲,聞一多決心戒煙,高孝貞知道后,堅決不答應。她對丈夫說:“你一天那么辛苦勞累,別的沒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煙這點嗜好。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難也要把你的煙茶錢省出來。”這席話像一股暖流,聞一多聽了,心里熱乎乎的。
此后,茶雖沒有戒,但降低了檔次;煙則不僅降低檔次,而且改變了品種和形式。聞一多過去抽的是紙煙,為了節省開支,曾試抽用煙葉卷成的卷煙和旱煙,但都因煙性太烈,抽起來嗆嗓子,咳嗽。高孝貞看著心疼,便在農村集市上購買了一些嫩煙葉,噴上酒和糖水,切成煙絲,再滴幾滴香油,耐心地在溫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種色美味香的煙絲。聞一多把它裝在煙斗里,試抽幾口非常滿意,贊不絕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紹:“這是內人親手為我炮制的,味道相當不錯啊!”
“詩人主要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這是聞一多的名言。抗戰期間,聞一多從一個著名的詩人、學者,逐步發展成為愛國民主運動奔走呼號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他有許多為了共同的目標團結在一起的戰友、同志。大家都尊敬他,愛戴他,他也從同志們身上得到溫暖和愛。他把這種同志愛看得比對妻子、家庭的愛更崇高。他曾經對自己的學生康倪說:“對我的家庭,我很滿意,你是知道的,”他指著跟前的小女兒聞翱繼續說,“我愛他們,但這種愛不能使我滿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種愛,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愛。啊!同志愛是人間最崇高、最真摯、最深刻的愛,用什么語言能表達出它的真實的內容呢?”他想了一想之后,用英文重復了一句“崇高的愛”!隨后又感慨地說:“這樣的說法也只能近似而已。”他還說:“當我年輕的時候,整日在苦悶彷徨中,找不到適當出路,讀《離騷》,唱《滿江紅》,也解決不了我的具體問題。在今天……”他沉吟了一會兒又說:“你看到我這兩年變化很大嗎?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組織的力量支持著我,生活在組織中,有一種同志愛。
在聞一多的熏陶、感染之下,高孝貞也從一個他生活上的至親伴侶,逐漸成為他的同志,他的事業的最堅定的支持者。
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在朋友們的推動下,聞一多從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鐵筆,掛牌治印。1945年10月,蔣介石發動昆明事變,把原云南省主席龍云搞下臺,派來自己的爪牙李宗黃。12月1日,李和關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幾百個特務、打手進攻西南聯大等校,毆打、殺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的愛國學生,當場殺死潘琰等四人,打傷數十人。正是這個劊子手李宗黃,附庸風雅,慕聞一多之名,托人送來一枚圖章,并附上豐厚的潤資,請聞一多為他治印,聞一多斷然拒絕。高孝貞也說:“餓死也不要這幾個臭錢!”夫妻都表現出崇高的氣節。
聞一多越來越受到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擁護和愛戴,因而,聞家每天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請他去講演或寫文章,有的向他請教,有的來和他商量斗爭的部署。對所有這些客人,高孝貞都熱情接待,特別是對青年同學,就像對自己的子女一樣。有幾位從淪陷區逃難來昆明求學的女同學(如康伣),一時失去了家庭的溫暖,就把聞家當成自己的家。有的人為了躲避反動派的追捕(如趙沨),有的人一時無家可歸(如莊任秋、彭蘭、張世英),也都住進聞家。雖然住房狹窄,生活困難,但高孝貞總是十分親切、熱情地接待他們,使他們非常感動。這對聞一多進一步做好團結群眾的工作極有幫助。
由于聞一多的才學和聲望,他在當時昆明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起著重大的作用。許多會議和活動由他發起,許多重要文件由他執筆或審定。那時昆明沒有公共汽車,私人沒有電話,通知開會或為文件征集簽名,都要靠跑腿。有時聞一多跑不過來,高孝貞就來分擔,挨家挨戶跑遍了同志們的家。
1946年3月17日,三萬多昆明學生為潘琰等四烈士舉行了盛大的出殯儀式。不久西南聯大也宣布于5月4日結束,三校師生分批北上復校。反動派以為民主力量削弱,可以放手對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屠殺鎮壓了。從五、六月份起他們到處張貼大字報和標語,攻擊愛國民主人士,還篡改他們的名字,什么“聞一多夫”、“吳晗諾夫”、“羅隆斯基”等等,誣蔑他們是拿蘇聯津貼的特務,給他們寄來帶子彈頭的恐嚇信,并在他們家附近布滿特務,還揚言要花40萬元買聞一多的頭……總之,氣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組織和朋友都勸聞一多早走;學生們請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護他;美國加州大學還曾以優厚的條件請他去講學,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離開苦難的人民,昆明還有許多工作等著我做。在作出這些重大決定前,聞一多都和妻子認真商量過,高孝貞深明大義,表示堅決支持。
就在這最恐怖最緊張的時刻,聞一多對暫住聞家的學生彭蘭、張世英夫婦說:“一個人要善于培植感情,無論是夫婦、兄弟、朋友、子女,經過曲折的人生培養出來的感情,才是永遠回味無窮的。”他夸贊另一位學生季鎮淮;不棄糟糠之妻,說:“只有對感情忠實的人,才能嘗到感情的滋味。他未來的家庭一定比較幸福。”說這話時是1946年7月5日,即他殉難的前10天。雖然是說他學生的,但顯然也是自己對婚姻和愛情的親身體會。
7月11日,西南聯大最后一批北上師生的車隊離開昆明。當天晚上,反動派就迫不及待地暗殺了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聞一多的戰友李公樸。有人深夜將噩耗告訴聞一多。他焦急萬分,不顧自己正在發高燒,便要起身去醫院。高孝貞擔心天黑有危險,極力勸阻。他一夜未眠,晨五時趕到醫院時,李公樸已身亡。聞一多撫尸痛哭,一面大聲說:“公樸沒有死!公樸沒有死!這仇一定要報的!”
這時從內線傳來可靠的消息:黑名單里的第二名就是聞一多!但聞一多以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堅持斗爭。高孝貞擔心到了極點,含著眼淚勸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當她聽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則諸事停頓,何以對死者”的回答時,又覺得丈夫講得很有道理,再也說不出一句勸阻的話來,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學致公堂舉行的李公樸殉難經過報告會上,李夫人張曼筠泣不成聲,特務們大聲叫囂,吹口哨搗亂。聞一多拍案而起,發表了氣壯山河的“最后的講演”,痛斥特務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回來”的決心,和“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的信心。下午,聞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門外被特務暗殺。高孝貞奔出大門,撲向丈夫,身上沾滿了丈夫鮮血。
高孝貞繼承了丈夫的遺志,1947年她帶著孩子們幾經周折回到北平,在組織和朋友們的幫助下,住進什剎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這個比較隱蔽的環境,使自己的家成為中共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聞一多的侄子聞黎智當時擔任中共平津地區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他和妻子魏克就以這里為基地,開展革命工作。高孝貞多方掩護和配合。這里還成為蔣管區進步青年前往解放區的一個中轉站。掌握這個關系的是吳晗。吳晗常介紹青年住在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孝貞對他們都像家人一樣,熱茶熱飯,問寒問暖,直到護送人來接走。
1948年3月,高孝貞帶著孩子奔向解放區,被選為華北人民代表。新中國成立后,她先后擔任河北省及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