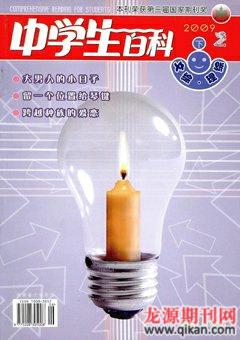歷史的衣裝
胡 堅
1941年春天,日本海軍情報官吉田猛夫以外交官身份進入檀香山,為日本海軍突襲珍珠港做最后的情報搜集工作。從橫濱出發前,吉田依照情報界的慣例,丟掉了一切可能泄露身份的衣物,想重新買套西裝,只是此時,隨著戰事的吃緊,本土物資已開始短缺,日本的市面上已經很難買到毛料的西裝,無奈的吉田只好買了件人造毛的西裝,匆匆出發了。
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國所流傳的西裝技術,在歷史上曾經和兩個國家密不可分——日本和俄國。時至今日,盡管日本還保留有諸多行業協會和工藝大師,但有一點恐怕是日本洋裝界人士不愿意看到也無法阻擋的——西裝開始進入批量生產的時代,他們自己手工西裝技術正在一點一點地消失——在手工西裝的制作工藝上,日派技術的最大特點就是干凈和仔細——沒有英國的傳統,沒有意大利的設計,日本派只能在工藝上精益求精,而這一點,又恰恰是在工藝的傳承過程中最容易丟掉的一環。所以一旦遭逢重大的變故,如二戰戰敗,如成衣興起,日派西裝工藝所受的沖擊無疑是最大的。
但是比日本派更不為人所知的,卻是歷史上的蘇俄派——一般人只能在007之類的冷戰間諜小說里,看到蘇聯間諜經常作為被嘲笑的對象,一個重要的道具就是他們肥大不合體的西裝——也許這樣更適合在口袋里多揣幾把手槍?
偏見一旦形成,就很難澄清。大概是由于氣候寒冷的緣故,蘇俄派的西裝做得都很厚——肩墊和胸襯得就像克格勃一樣強硬,很容易把一個身形健美的猛男撐成一塊門板。20世紀40年代蘇聯紅軍的將帥們在東線留下的照片里,厚厚的軍裝肩墊撐得肩膀幾成一條直線。對服務于“紳士體型”的英國裁縫,講求瀟灑風度的意大利裁縫,簡直就是噩夢。我曾聽過一段有關蘇派工藝描述,十分震撼,當事人多年后向我提起時仍然心有余悸——“我去的時候,他正在熨胸襯,哎呀我的媽呀,大熨斗熨得胸襯上都是印兒。我說,‘都熨糊了,他說,‘不這么熨怎么板正?”
這種硬朗剽悍的作風很容易引起年輕人的好奇心,可再想追問更多細節就沒有了,當事人感慨地說,蘇派手藝做活粗糙,但是肩墊和胸襯很有特點,用在大衣上乃是一絕,可惜在中國早已失傳,多年來沒看見過了。
能見的只能是歷史照片——勃列日涅夫年輕時是著名的濃眉帥哥,這個特征在當年讓他頻繁地出現在歐美和中國的諷刺漫畫上。據說CIA監視他的起居,發現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在鏡子前面臭美。這樣一位愛美的領導人,穿的西裝顯然是頗具代表性的——20世紀70年代他開聯大,見鐵托,和庫利科夫檢閱部隊,穿的都是高扣位小駁頭(西裝翻領)的三粒扣款西裝,更少見的是當年似乎還流行過一種窄駁頭高扣位的西裝,從勃總書記到安德羅波夫,簡直是總書記制服。而且橫跨黨政軍三屆,從柯西金到葛羅米科,甚至連朱可夫都穿著它留過影,也許這種風格才能以最大的面積凸顯他們在肩墊和胸襯上的優勢?
因為有時代的烙印,過去的流行風終于變得不再流行。一個時代的情懷隨著一個大國的解體而煙消云散。今天的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三流小明星的襪子品牌,卻不能確定當年的蘇聯黨政軍領導是在哪里做的西裝,他們個人的生活習慣又會在這其中起到多大作用——英國人福塞斯就在小說里提到過一位在英國薩維爾街定制西裝的克格勃大干部;而同時,退休的蘇軍參謀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和老妻散步的照片里,穿的就是一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西裝,出于對這位老帥的尊敬,我不愿說那件西裝真的很不好。
有一次和前輩聊天,我提出一個疑問:上世紀50年代蘇聯就在上海批量下單加工西裝和大衣了,傳說中的蘇派,會不會在本土也失傳了?對方神色黯然,半晌無語,而旁邊的一位朋友湊過來:“蘇派,你們是在說蘇俄鋼琴學派么?”
我笑了:“安東和拉赫不好說,郎朗穿的,大概得是意大利的杰尼亞。”
編輯/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