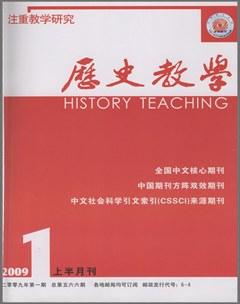陳旭麓的真知灼見(五)
多年來,我們把資產階級分為買辦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這種區分反映了特定時期的斗爭需要,并偏重于用政治因素來解釋經濟現象。政治對經濟當然是能夠起到制約作用的,但政治又不等于經濟。列寧說:“階級差別的基本標志,就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按照他的意思,特定的階級總是特定生產關系的體現者,所以,階級在本質上是一個經濟范疇。階級產生之后,會有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的斗爭,但那是經濟的派生物。我們用“買辦”、“官僚”、“民族”來區分資產階級,并賦以否定或肯定的意義,派生的東西就被強調得過了頭。用過頭的方法來描寫歷史是不免要失真的。1957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引述《中國經濟史全書》的話說:
“中國之資本家,或為大商人,或為大地主……惟于此二者之外,有一外國所不能見之資本家在焉,蓋即官吏是也。東西諸國,官吏而富裕者,未始無之……惟中國之號為大資本家者,則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彼其國人,一為官吏,則蓄產漸豐,而退隱之后,以富豪而兼紳貴,隱然操縱其政界之行動,而為鄉民之所畏忌……次之者為紳商,此中固亦有相當之官階,或至為官為商,竟不能顯為區別,常表面供職于官府,而里面則經營商務也。”
有人統計過,在1872年到1913年之間,近代企業的創辦人中地主占55.9%,商人占18.3%,買辦占24.8%,而且“投資與近代企業的地主,大都有某種官僚的身份,很多是二、三流洋務派或洋務派的幕僚,絕少是土地主”。那么如果把這些官僚地主與買辦剔除出去,民族資本還會剩下多少呢?況且剩下的那18.3%的商人中,認真追究起來,也不那么干凈。例如,周延弼是在籍三品銜候補道,葉澄衷也因道員銜而稱“觀察”,等等。顯然,這是一筆不太容易算清的帳。確實,中國資產階級又存在著不同的階層,但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是他們所占的生產資料在數量上有多有少。因此,把列寧的意思貫徹到底,可以恰如其分地分別稱之為: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引自陳旭麓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