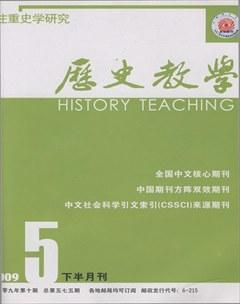東方國家對外開放的歷史反思
主持者手記:為了推進東方外交史研究,總結歷史上東方國家對外開放的經驗與教訓,我們邀請了澳門大學黃枝連教授、魏楚雄教授、外交學院熊志勇教授、印度尼赫魯大學譚中教授、淮北煤炭師范學院謝豐齋教授進行了一次筆談。五位教授從廣闊的時空背景探討了東方歷史上文明交流、融合與沖突的復雜過程,讓我們看到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是一個異常曲折復雜的歷史,同時我們也看到正是這些交流才促進了東方歷史的整體發展。探討東西方文明交流與融合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可能帶來的沖擊,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是一項不可不做的基礎工作。現將五位教授的筆談整理摘要發表,以饗讀者。
[關鍵詞]東西方文明交流,鴉片戰爭,五四運動,費正清學派
[中圖分類號]K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57-6241(2009)10-0078-06
陳奉林(外交學院外交學系副教授):自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東來時代起,包括基督教教義在內的西學即開始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沖突,直到近代西方文明大規模涌入后更是如此,其勢洶洶。黃先生,您如何看待西學在中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呢?
黃枝連(澳門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教授):我不贊同“西學”在近現代的中國沒有什么大發展之說。其實,它是大有發展的。2008年5月,在陳奉林博士召集的北京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合”研討會上,我提出所謂“中華文明的3+2+1論”:關于基督教文明及其美式文明進入新中華文明的事實,可見之于港澳特別行政區的兩部《基本法》及其“一國兩制”。因此,怎么能說西方文明及其“西學”沒有在中國大展宏圖并落地生根呢?我也認為,冷戰時代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個世界之爭”,其實是西方文明以兩種不同的形式在世界范圍內的一場斗爭,我們不過是被卷進去罷了。
在發展范式上不再糾纏姓“社”、姓“資”,是意味著中國人在現代化進程的開展上對西方近現代發展范式的重新認識和重新應用。在一個意義上,三十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在于中國人認識到西方近現代的發展范式有其可取之處。因此,試圖根據中國的實際尋求一個嶄新的發展范式。加入WTO和剛剛閉幕的被世人普遍叫好的奧運會,不也顯示西方文明的威力嗎?總的來說,自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的東西對中國產生了深遠重大的影響。因此,19和20世紀以來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代表的西方近現代文明進入中國,是使中國脫離其單一化和趨同化的例證。幸而有此注入,所以進入21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才出現另一次的飛躍。
陳奉林:改革開放后,以健全的心態走向世界,一切民族的優長的東西都要學很重要,但不容易做到。近代以來存在的夏夷之爭、中西學之爭、“五四”前后東西方文化本位問題的論戰以及走什么道路之爭等等,都是國人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譚先生,您怎么看待這些問題呢?
譚中(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這個問題牽涉太廣,很難簡短回答。我看過一些所謂的“夏夷之爭”的辯論,覺得關于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多源的問題必須要有整體觀念,要把中國文字歷史傳統和地質學理論、考古發掘資料相結合來科學地研究。我傾向于地球陸地板塊遷移理論,認為印度大陸板塊從“Gondwana/岡瓦納古陸”分裂出來,向“Laurasia/勞亞古陸”中的中國大陸板塊移動、兩者擁抱,越抱越緊而擠出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來,在這兒周圍形成一個茂盛的生態區域,并向北、向南流出四條文明之河,向南的印度河與恒河孕育出印度文明,向北的黃河與長江孕育出中國文明。人類祖先臘瑪古猿發源于這一地帶(云南發現臘瑪古猿化石最多),生存于200萬年前的“巫山猿人”和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是我們現在所知的中華民族最早祖先。大禹是“巫山猿人”后裔,羌族在最早中國民族中起過重要作用等等。這些都必須超越“夏夷之爭”,重新認識,深入研究。所謂“中學”“西學”都不是以整體觀念、從人類進化的范式來探討問題的。東方注重“精神文明”與西方注重“物質文明”只是相對而言,不必搞成“二元對立”。
普林斯頓大學英裔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于1998年為巴黎OECD出版的《中國長期經濟成就》(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勾畫出自從秦始皇大一統以后所建立的容納了人類1/6到1/3的經濟最發達的中國。我把這樣一個政治實體比喻為經歷過兩千多年的狂風暴雨、地震山崩而沒有倒塌的全球獨一無二的“su-perdome/穹頂”建筑。這樣的文明智慧必須很好總結。比方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襯托出的是中國農業文明注重“生”,讓萬物化育;“天人合一”道出了中國經濟發展不破壞生態環境;《天工開物》說明中國是能工巧匠的社會,擅長于創造精美物品等。還有“大同”“小康”的理想境界,都可以發揚光大,幫助中國在21世紀走出符合國情、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反之,如果一心一意要把中國發展成第二個美國,用百分之五人口消費百分之25地球資源的比率生存于世,那就必然為別國所不容而引起沖突與世界災難。在這基本的兩大范式之間是沒有選擇的,那形形色色的“道路之爭”都于事無補。
陳奉林:自近代以來,西方科學與技術引進中國已有百年了。在這百年當中,科技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顯,但在我國并沒有太多的獨創。黃先生,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
黃枝連:如果以過去500年,即公元1500年至1999年作為世界近現代史,則它是以基督教文明為主體的西方文明成為優勢文明的時代。西方的興起顯然是在其內部發生制度變革、科技與觀念進步的情況下取得的,其大意可以概括為對境內外一國內外的差異性因素尋求多元化的處理。這是產業結構多元化及政治結構多元化及文化教育多元化的內在動力。過去500年的歷史,充滿了同西方人有關的大小戰爭,包括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美蘇的冷戰。
相較之下,明清兩代政治經濟結構的特點便是趨同化,即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所謂儒道釋組成的中華大傳統,到明末清初形成以理學道學為主體的學問或道統。清朝前期幾個皇帝,所謂康乾盛世,其實也是建立在這種以儒學—儒術一理學為主體的單一思想體系之上的。我所謂的“天朝禮治體系”對東亞地區的區域秩序雖然曾經有一定的穩定性作用,但在遭遇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挑戰時,卻無絲毫防衛作用。
鴉片戰爭帶來的便是中華帝國這種日益萎縮的“單一體系”的無能為力及全面崩潰。所謂“同治中興”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士大夫并未認識到中國本身的問題和發展需要用多元化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體系來處理。康梁的“百日維新”,可以說是往“差異性因素做多元化處理方向”靠攏;而“五四”運動中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則是進一步向西方文明靠攏。但對中華傳統的大勢否定,則對西方文
明發生趨同化和單一性的傾斜。
因此,自19世紀末年到20世紀中葉,中國人沒有在科學技術上取得重大的原創性成就,遠一點的根源是明清兩代以來中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單一化與保守化,故步自封,把統治精英和社會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很古老和狹小的典范里。當然,這同西方支配世界500年相應的中國持續五百年“大停滯”有關系,也同國破家亡,遭遇內憂外患有關系,即大家都忙于避亂和打仗,也就談不上什么學術研究、發明與制造了。所以,迄20世紀末年中國人在現代科學技術上沒有什么突破性的發展,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的科學沒有完成向近代科學的轉變,創造出新的科學技術。
陳奉林:進入近代以來,東方幾乎所有國家中國、印度、奧斯曼帝國等都受到了歐美文化\文明的沖擊,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從封閉狹窄的國內轉向異彩紛呈的外部世界,力圖采借西學,富國圖強。魏先生,您怎么評斷這段歷史呢?
魏楚雄(澳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首先,從歷史長河來看,這種沖擊從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東方對西方沖擊的結果,并非完全是單向的。例如,奧斯曼帝國曾在蘇萊曼大帝統領下于16世紀擴張為跨越亞、非、歐三大洲的帝國,控制了西方經西亞通往東方的貿易之路,對西方造成沖擊,結果促使西方借鑒了穆斯林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某些因素,推動了西方文明的發展,并另辟了通往東方貿易和殖民的新航路。隨后,日益強盛的歐洲反過來利用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對土耳其多次進逼,使其逐漸成為“歐洲病夫”。
其次,沖擊或挑戰也意味著機遇和變革。東方各國是在不同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應對來自西方的不同沖擊與挑戰。奧斯曼帝國在一戰后的瓦解及其民族危機為凱末爾在土耳其進行劇烈改革提供了良機。雖然凱末爾巧妙地采取了階段性改革的措施,于較短的時間內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創立起新共和國,但凱末爾主義的實質是現代化和西方化。凱末爾在土耳其不僅發動了經濟改革,而且也開展了政治革命、宗教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相比來說,英國的殖民主義模式也為印度的現代化和西方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英國在印度引進的西方教育模式、文官制度和法律體系,無疑為圣雄甘地非暴力主義和獨立運動的成功創造了前提。然而,與凱末爾不同的是,甘地巧妙地把西方的法治觀念與印度的傳統文明結合起來,使得古老的印度民族和宗教獲得了巨大的現代活力,并讓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獲得了世界性的和歷史性的意義。
中國和日本也都在被迫打開閉鎖大門之后試圖走西方化的道路,但兩者的歷史條件與選擇不同,而且,日本素有樂于學習外國文化和先進經驗的傳統,號稱“好學之民族”。所以,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改革領袖能夠采取“走出去、拿進來”的態度,把幾乎一半的政府領導人帶到西方去轉了約兩年,全面詳盡地考察和學習了歐美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行政措施及文化教育設施等,為日本成功實現現代化找到了借鑒。在鴉片戰爭的刺激下,雖然中國上上下下有不少改革志士力圖“西學為用”、富國強兵,但在改革之前沒有在中央政府樹立改革權力的政治變革,中國的改革領袖無法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樣有效大膽地推行改革政策,直至中國最后不得不通過一場革命來摧毀封建勢力和傳統體制,然后再重新開始其現代化的進程。
陳奉林:“沖擊—反應”模式是費正清等西方漢學家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來的解釋東方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的一種分析模式,認為東方歷史是在近代西方的沖擊下逐漸走向近代的。譚先生,您是怎樣評斷這個分析模式的?
譚中:“Challenge and response/挑戰/沖擊—反應”論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用整體觀念聯系世界事物的杰出分析,已故當代美國中國研究泰斗費正清等人更具體地把它運用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從黑格爾到費正清以及他的門徒都有一種東方文明落后,是西方文明使東方社會現代化的根深蒂固的成見(費正清還說過,新中國所有好的事物都是西方影響造成,所有壞的事物都是中國落后傳統所致)。正是因為這種成見使費正清認為在十八九世紀阻礙中國和西方正常往來的是他所謂的中國“朝貢體制”(tribute sys-tem),又說西方國家采用了所謂的“條約體制”(treaty system)來取代“朝貢體制”而使中國和現代世界聯通,從而使中國歷史有了從“偉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到“現代改造”(modem transformation)的大轉變。這一理論對世界學術界分析中國近現代發展的影響極大,特別是其中滋生的“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當前全世界的“中國威脅論”差不多都是以此為理論依據,說中國至今仍然有一種“middle kingdom/中國”心態——把中國當作世界中心,把外國當作“蠻夷”。
我于1960及1970年代在印度研究并教授中國近代史時,曾經猛烈批判“費正清學派”(指他和《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系列》叢書的作者)用時髦的西方理論來粉飾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我在印度出版的兩本英文書:《中國和勇敢新世界》(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以及《海神與龍》(Triton and Dragon: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and Imperial-ism)已經變成印度大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使印度學者能看到替代“費正清學派”的、從中國發展本身來看“挑戰與反應”的論點。我曾經到哈佛大學去見過費正清教授,也在學術文章中不斷向他挑戰卻得不到反響。但我高興地看到,他晚期的著作中,把“條約體制”(treaty system)改成了“不平等條約體制”(unequal treaty system)。我認為不論是中國發展的實踐也好、還是學術研究中國歷史也好,都要注意切莫“東施效顰”,可以參考西方的權威理論,但應該按照“科學發展觀”走出中國自己的路子來。在西方學術界,費正清已經不像幾十年前那樣權威了。
陳奉林:魏先生,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向您請教,就是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講的“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問題。作為歷史學者,您能否給我們稍微展開談談這個問題?
魏楚雄:早在2000年,王家范教授就在“解讀歷史的沉重——弗蘭克《白銀資本》讀后”(《史林》,2000年第3期)一文中,對弗蘭克一書提出了犀利精辟的批評。我比較贊同王家范教授的觀點。無論東方的衰落跟西方的興起是同步還是先一步或后一步,無論東方的衰落同西方的興起有多大關系,這兩者之間絕非簡單的此伏彼起或此起彼伏。東方的衰落有其深刻復雜的諸多內外部因素,其深層原因同西方興起的原因一樣,實在跟許許多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因素有關,遠非白銀
的跨國度流動所能簡單地以一言以蔽之。雖然弗蘭克一書旨在抨擊曾被薩義德大師討伐過的“西方中心”觀即“東方主義”,但實際上弗蘭克理論可謂是一種“新東方主義”,因為從喜歡利用“神秘之東方”來標新立異、開拓學術生涯這一點來說,弗蘭克跟“東方主義”者沒有本質的區別。從沖擊傳統思維、構建“整體主義”理念和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說,弗蘭克的貢獻確實不小。其書大膽地挑戰了許多影響廣泛的西方經典理論,把西方與美國的“歐洲中心論”和“歐洲特殊論”從天上摔到地下。然而,弗蘭克試圖以“東方中心論”來取代“西方中心論”的作法,兩者實際是如出一轍。我反對任何“中心論”的提法。在世界歷史上,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歷來有強弱、高低之分,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互相影響,興衰不定。這正應合了中國的那句老話,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陳奉林:我想請熊先生從中國外交史的角度,分析一下近代西方對東方國家的沖擊和影響。
熊志勇(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19世紀的中國的確是在西方的沖擊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歐洲從十六七世紀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這期間中國并不缺少同歐洲的聯系,但這種聯系并未促使中國產生自我改造的動力。相反,面對歐洲殖民者的挑戰和威脅,清政府采取了閉關自守的政策。若不是19世紀中期以侵略戰爭形式所表現出來的西方沖擊,中國的近代化可能要走上幾百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自然發展那只是一種無法證明的假設。19世紀后半期的歷史對中國是痛苦的。在這種沖擊下,中國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像非洲那樣淪為西方的殖民地;二是簡單地進行反抗,中國人作過嘗試,但無法達到驅趕外國人的目標;倒是第三條道路給中國帶來了復興的希望。這就是主動地向西方學習,恢復獨立的道路。如果說,19世紀時中國的變化是西方沖擊的結果,那20世紀中國的變化則是自己主動爭取來的。實際上,這種主動向別人學習、逐步改造自己的過程,從19世紀后半期的洋務運動就開始了。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人從新的戰略思維出發,打開了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門,在開放的過程中從疑惑到逐步理解,并根據自己的條件加以吸納。
陳奉林:謝先生,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表明,近代以來隨著歐洲地理大發現的開啟,不僅有歐洲經濟圈的擴張,還同時存在著東亞經濟圈。過去我們只知道近代以來歐洲人開辟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世界經濟圈開始形成。你能夠對世界經濟圈和東亞經濟圈的存在做些解釋嗎?
謝豐齋(淮北煤炭師范學院歷史學系教授):地理大發現是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大約1500年前后,歐洲人開始從歐洲的一角走向世界各地。1494年,由羅馬教廷主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締結了雙方在全球范圍內劃分勢力范圍的托爾特西拉斯條約,葡萄牙占了東半球,西班牙占了西半球。此后,葡萄牙主要繞航非洲好望角,向中國、印度和印尼等東方國家航行;西班牙主要跨越大西洋向美洲航行。他們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許多殖民地、商館和商站,他們的商船在美洲、歐洲和亞洲之間進行大三角貿易,這就是世界市場的初步奠立。此后不久,英國、荷蘭、法國等國也加入進來,掀起了16~18世紀的歐洲國家之間的商業戰爭。
東亞經濟圈的存在一直被忽視,沒有引起學者認真的研究。實際上,在近代以前東亞是存在面積廣闊、歷史悠久的經濟圈的。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自西漢以來、甚至更早就已經存在,唐宋時期曾達到鼎盛,當時中國開放的口港包括泉州、福州和廣州等地,管理外貿的機構稱“市舶司”。元代,中國的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因為元朝的統治者已經將中亞、西亞和東亞各地在血緣上聯為一體,海上交往甚為便利。明初時期鄭和下西洋,已經將馬六甲、印尼群島的許多地方納入中國的附屬國,他們不時地對中國進行朝貢貿易。近代以來,歐洲人進入東方貿易圈以后,并沒有很快取得優勢,而只是作為一個貿易伙伴加入進來,而且在中國沿海受到很大限制,他們不能與中國官方直接交往,只能與“十三行”的行商進行貿易。
陳奉林:熊先生,您是研究美國問題的專家。我很想聽聽您怎樣看待美國戰后以來一直保持科技與經濟強國大國地位的。
熊志勇: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充分顯示了自己。戰后至今,美國依然保持著世界領先的地位。對于美國能在~個世紀的時間里長久不衰,在我看來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特點。一是美國自身條件好,如國土遼闊,資源豐富,人口適中保證了較大的消費市場,周邊沒有挑戰者等等。二是美國不斷地采取各種改革來緩和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使肌體各個部分能正常運轉,如給予黑人以平等地位,采取項目計劃的方式做預算等等。三是美國實施了激勵創新的政策并建立了相應的機制。它不僅在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方面保持著世界領先的地位,而且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方面也掌握著話語權。四是美國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條件,推行以市場化為基礎的全球化,倡導建立了處理政治和安全事務的聯合國、處理經濟事務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五是美國避免同大國發生戰爭,而是通過局部戰爭、冷戰或演變等方式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陳奉林:“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覺得可以用它來觀察今天東亞地區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魏先生,您同意嗎?
魏楚雄:所謂“天下大勢”,既可指一國的天下,也可指全球的天下;既可指一個國家內部的大勢,也可指一個地區和世界的大勢。所以,“天下”在《三國演義》里是指中國,但在今天是有空間前提的,可指一個國家或更大的范圍。縱觀世界各國,很少有一個現代國家再會分分合合的。同樣,雖然世界各國和地區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戰爭與沖突、彼此間分分合合,但當世界進入了全球化進程以后,這種趨勢就開始向合的方向遞增、而向分的方向遞減。因為全球化會把各國家各地區的經濟文化密切融合在一起,使彼此的利益無法輕易切割分裂。
從當今世界看,沖突和戰爭頻繁發生的地方,往往是全球化程度比較低的地方。東亞地區在歷史上總是分分合合,僅20世紀前半段里就發生了兩次重大沖突:太平洋戰爭和朝鮮戰爭。可是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很快把東亞的不少國家和區域納入了全球化的經貿文化網絡。雖然現時東亞各國在各種問題上仍時有糾紛與沖突,但它們明顯都在努力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東亞各國只要在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方面卷入得越深,它們相互之間的依賴程度就越大,而彼此之間出現破壞性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小。東亞地區的全球化和經濟合作發展勢不可擋,而且這種發展會是單向性的、不可逆的。
陳奉林:謝先生,根據您多年對中西方經濟史的比較研究,您認為這兩大經濟圈之間是否存在著密切交往呢?
謝豐齋:這種交往承接中世紀的貿易格局,關系一直十分密切。1989年,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世界體系》一書中,曾將“黑死病”以前的非亞歐世界體系劃分為三個緊密聯系的亞體系:即歐洲亞體系、中東亞體系和東亞亞體系。
16世紀初,歐洲人初到東方也記述了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對外貿易情況。1517年8月,第一批葡萄牙船隊抵達廣州珠江口。葡萄牙使節皮萊士根據他的見聞完成了《東方概要》一書。他聲稱中國有一千多艘帆船(junco)活躍在海外市場,他們運出的中國物產十分豐富,既有各式各樣的錦緞,也有不計其數的瓷器。與皮萊士同時的杜亞特·巴布薩(Duarte Barbosa)在《東方紀事》一書中提到,中國海外有很多富商,有很多裝備4根桅桿的中式帆船。中國人用這些船活躍在馬六甲、蘇門答臘、馬拉巴和坎貝之間,運銷的貨物計有鐵器、硝石、絲綢、胡椒、藥材、香料、珊瑚、棉布和各種小件貨物。16世紀中葉,歐洲出現了兩部關于中國的專書,即葡萄牙多明我會修士克盧士的《中國志》和奧斯丁會修士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克盧士曾提到,清朝政府的禁海令頒行以后,一些華人到海外經商,不再返回,南洋各地都有這類華人。他們常在葡萄牙人庇護下乘自己的船返國,而請葡萄牙人代繳稅款。
皮萊士曾提到,許多中國人出海時帶著妻子兒女,始終在船上生活,在陸地上沒有房子和住所。不過,我們看到費爾南多·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曾提到16世紀有一個中國商人在印尼生活時,娶了一個當地的妻子。1571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明都洛外海營救了一艘中國沉船,這些人回福建漳州,宣稱西班牙人正在菲律賓營建馬尼拉城,并急于招商,引起1572年中國商人將大批絲綢、瓷器和許多值錢的商品運到馬尼拉。于是西班牙人就地打造兩艘大帆船滿載這些中國貨,在1573年駛抵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1576年,漳州月港與馬尼拉之間的帆船貿易完全固定下來,從此,漳州、馬尼拉帆船太平洋貿易年年進行。直到1815年墨西哥戰爭爆發后,才宣告這條太平洋絲綢之路的終結。
陳奉林:謝謝五位教授應邀參加我們的筆談。
責任編輯:侯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