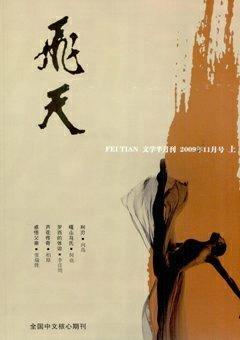行筆之前的思索
作家大多不能也不愿回避這樣一個問題:習作者為文究竟應該寫什么?被夏志清譽為“中國當代最重要的小說家”的張愛玲女士對此有獨特的思考:在1940年,張的三篇名作《自己的文章》《寫什么》《論寫作》分別從不同方面闡述了她的看法。《寫什么》一篇更是開明道義地以這個問題作為題目,對于“寫什么”進行多層次的探討。
文章起始,張愛玲在講述了自己一段經歷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作家從主觀上究竟該怎樣去選擇而為文?朋友詢問張是否可以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在那樣一個創作時代,“無產階級的故事”正是一個較為新奇的題材,可是,對張來說,“阿媽”這樣的人就是“無產階級”了,也只有這樣的“無產階級”,她方“稍微知道一點”——她對“無產階級”的事情根本是一無所知。因而,張愛玲沒有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去寫“無產階級”。在故事結尾,張愛玲不僅為自己可以堅持自己的創作路線而沒有“改變作風”而慶幸。更為重要的是,她說明了文學創作中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作家應該怎樣“面對新奇的誘惑”。“無產階級”在張愛玲看來,也只能是阿媽那樣的人物,根本上她是不了解的,這種情況下,張是不會動筆去書寫“無產階級”的。對于張來說,一個作家必須堅守住自己的創作立場,而不能受外界的引誘而背叛自己的創作。盲目地追求新奇,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很大的誘惑和傷害——作家不能夠從自己創作以外的地方去干涉作品的選材與創作。
對作家主觀層面進行探討后,《寫什么》闡述了另一個重要問題:“作為作家的本身,對于文學題材(以及更為廣闊的寫作路徑)究竟有多大的選擇余地?”張愛玲認為:“文人討論今后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選擇的余地似的……我認為文人該是園里的一棵樹,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在張看來,作家對于題材(及寫作路徑)是有限選擇的。作家的寫作是以自己的生活的底子為基礎的,一個習作者的寫作路徑“是不能有想象的自由”的,“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后,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而對于讀者或者評論者來說,作家“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如果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他(她)要做出的努力只能“向上”,即如何更好地去表現她所能駕馭的題材,或者說和他(她)內心產生“應和”,這樣才能產生出好的作品。
這一理論是獨到和科學的。賀拉斯的《詩藝》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明晰的闡釋:“從事寫作的人,在選材的時候,務必選你們能勝任的題材,多多斟酌一下是否掮得起來,哪些是掮不起來的……要有所取舍。”而不是仿佛絕對自由地去選擇題材進行書寫。何謂“能勝任的題材”?正是指張愛玲所指的那棵“根深蒂固的樹”,指作家從小就開始積累的生活經驗。每個人的大腦都不相同,而這種不同是源自于“兒童時代的經驗”,一個人即使觀察最簡單的事物也都通過一個能動的過程:我們能動地觀察世界,能動地建構現實。這一能動的過程是受個人風格或身份控制的。更近一層,所有文學反映都由包括人體身份、文化身份和使我們成為我們現在這個樣子的獨一無二的個人歷史的那種身份所控制。作家與作家之間由于家庭背景、社會歷史、還有自身的歷史的原因,他們作品中所表現的題材其實有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并不是由作家可選擇的。作品是由作家所在的“人”“文化”“歷史”共同影響的結果——“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作為題材的源頭的世界本身不是對象,必須這種對象同作者的自身發生某種關系,這樣才可能成為作家的題材。這樣,在分析一個作家的作品題材的時候,必須要分清題材和生活題材兩者的差別。可惜,很多理論家和作家對這一點認識并不很清晰。如唐文標先生在1970年曾厚非張愛玲既然是個地道的“上海人”,卻“筆下看不見農人、城市工人、公務員、商店職員、知識分子或教職員”。今天看來,唐的錯誤正是將客觀世界(素材)和與主觀發生感應的世界(即題材)混為一談;將現實中的“上海”與作家所能感知的“上海”混為一談。張愛玲所生活的“上海”是與張愛玲的內心發生感應的“上海”,是租界的“上海”,封建大庭院最后掙扎的場所,同時又是十里洋場的聚集地。而并不是“向中國散播新思想文化的中心”。對于上海這個客觀存在來說,在茅盾眼里它是民族資本家發展謀生的土地,對于巴金來說,是人心里凄凄的“寒夜”,而對于張愛玲來說,“上海”只是“一個純黑暗的大屋”,是“與國民革命后的中國不通往來,只屬于前清遺老遺少對新制度的逃避,也許茍延了一些時間”的場所。只有這個“上海”才是屬于張愛玲的“上海”,才是張愛玲可以支配的“上海”。“當她發現她的‘上海已經不復存在時,她感到迷茫與無助……于是她在無奈之下最終選擇了離開”。
由此可見,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并不是可以處在旁邊冷眼看客觀世界發生的,作家“不僅作為一個文學家來觀察生活,同樣也作為一個被日常生活安排其中的、處在復雜多變的情勢中的人物來觀察生活”。只有當這個作家自己(自覺或者不自覺)“走進書中,進行干預,對他筆下的人物的行動進行干預解釋,自己出頭描寫人物的思想感情”,這樣的作品才“變得更加真實,更富于內在的現實性”。而這種感情的介入首先建立在作品的題材必須是作者非常有“感覺”(我覺得在此用“熟悉”不如“感覺”一詞準確)情況之下,換句話說,作品對于題材的選擇和主題的追求是建立在題材本身對于作者所帶來的感悟上。失去了這種“外”與“內”的感悟,“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地也能夠寫出濫調來”。
既然作家在創作中“不能想象的自由”,那么作為一個作家,如何讓他的創作生涯“永葆青春”呢?這是《寫什么》中接下來張愛玲所論述的問題。
張愛玲先就為什么作家“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進行了探討:“因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復。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樣的題材既然辦不到,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用于不同的題材上。”題材的有限,讓作者的寫作生命經受考驗,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寫作者進行了題材拓展的嘗試,他們試圖寫不同的題材,妄圖通過題材的不同而達到一種手法雷同的糾正。張對于這種嘗試是提出中肯的批評的:“然而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經驗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幾個人能夠像高爾基、像石揮那樣到處流浪,哪一行都混過?”張認為,作家對于任何一種題材的運用,都是建立在作家自身對于題材本身的熟悉和感悟的基礎之上的。作家不可能為了所謂的“突破”而拋棄自己所熟知的題材。如果這樣做了,那這樣出來的作品也是失敗的。那么,作家該如何突破呢?“只有當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遍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個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張愛玲認為:一個作家對于題材的選擇如果要避免雷同的毛病,不要只是妄圖去嘗試自己不了解的層面,而是從深度去出發。不停地挖掘,這樣才會不斷突破自己,超越手法上的雷同。就如張愛玲前面所說的:“文人該是園里的一棵樹,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這種將發展向度從原先的廣度轉向到深度,無疑對后來的寫作者創作有很好的借鑒意義。也是對于那種“題材局限”質問的一種反駁。
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曾說過:“《傳奇》一書里的各篇人物和故事,大多‘各有其體……她的小說人物,可說是俯拾即來,和現實距離只有半步之遙。在她周邊生活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說就知道她寫的是哪一家的哪一個人。”可見,張愛玲對于小說的真實性是很看重的,她的上海是她心中的上海,而不是徒有想象的城市。張愛玲的傳奇是有真實作為底子的傳奇。“自我感情的真實”也許這就是張愛玲的世界里最看重的創作守則,也正是《寫什么》一文中,張愛玲所反復強調的。
(作者簡介:高佳嘉,四川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