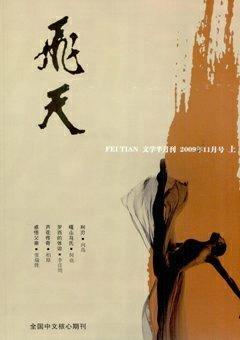《紅線》與《聶隱娘傳》比較研究
《紅線》與《聶隱娘傳》都是唐傳奇名篇,講述的都是神奇女俠的傳奇故事。《紅線》講的是潞州節度使薛嵩的侍女紅線,明音律,善阮咸,通經史。當薛嵩為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吞并潞州的野心憂悶不堪時,紅線主動請纓為薛嵩解憂。她當天夜初裝束前去魏州,半夜而返,盜回田承嗣金盒。又叫薛嵩派人快馬送回魏州,并附書信一封,以示恐嚇。田承嗣一見,果然驚慌失措,立即送禮求情示弱。不久,紅線辭別薛嵩,歸隱山林,不知所蹤。《聶隱娘傳》也是晚唐作家的作品,作者是裴■,講述的是魏博大將之女聶隱娘十歲為一尼姑看中竊去,教給她劍術,專取惡人首級。五年后還家,自擇夫婿嫁之。元和年間,魏博節度使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睦,讓她暗殺劉,隱娘因佩服劉公神明,棄暗投明,反為劉昌裔擊斃了魏博派來的刺客精精兒,接著又用計避開了魏博刺客妙手空空兒的搏擊。后亦不知所蹤。
這兩篇故事發生的背景是這樣的:為迅速平定安史之亂,唐王朝出于穩定局勢的需要分封安史舊部,張忠志為成德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這就是河北三鎮。另一降將薛嵩為相衛節度使。三鎮中田承嗣勢力最大,也最為跋扈,是唐代藩鎮中第一個表現出半獨立野心的人。
然而,薛嵩對朝廷的態度,與田承嗣有天壤之別。降唐后,“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內粗理。”他所鎮守的相、衛,正隔在河北三鎮與朝廷所控制的宣武鎮之間,起著屏障汴州和東都的作用。而田承嗣要擴充實力,第一個目標就是相衛鎮。《聶隱娘傳》中和劉昌裔發生矛盾糾葛的是田承嗣之子田季安,史稱田季安極為殘暴,惡名遠播。田氏盤踞魏博四十九年不入朝廷,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而據韓愈《唐故檢校尚書左仆射右龍武將軍劉公墓志銘》記載,劉昌裔在召還京師的途中發病,左右勸其休息,他說:“吾恐不得生謝天子。”對朝廷相當恭敬和忠心。在一些生活小節上,劉昌裔也相當的謹慎和節制。韓愈《劉公墓志銘》云:“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思念計畫”;“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于諸帥中獨然。”
明白了以上事實,就可以知道當時薛嵩和田承嗣、劉昌裔和田季安之間的矛盾斗爭就不僅僅是藩鎮之間的爭權奪利,而是維護國家一統與分裂割據之間的斗爭。因此,對雙方當事人的態度就有了是非之分,就有了區別人格高下的標準。
《紅線》和《聶隱娘傳》就是把人物置于這樣的背景下展開敘述的。這就框定了一個非是即非的故事發展走向,結果自然是故事的主人公紅線和聶隱娘都是站在正義的方面來和魏博節度使斗爭,并最終取得斗爭的勝利。這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態度,也表達了當時人民的愿望。這是兩篇傳奇一致的地方。
但僅僅具有同一的故事框架并不表示敘事線索的一致。紅線是薛嵩的家生婢,和薛嵩是主奴關系,奴才對主子的忠心是當時社會的道德標準,違此即屬不義。紅線幫助薛嵩制服田承嗣,首先是奴報主的行為。紅線的出發點是減主憂,這是符合封建社會主憂臣辱,主危臣死的倫理道德的,是義的體現。但這種義行只有在其主子的行為是正當的時候才具有超越的意義。
聶隱娘與紅線不同。聶隱娘是魏博大將的女兒。魏帥又常賜以金帛,并讓她做隨從左右的軍吏,可謂寵任有加。但她由于“服劉公之神明”,轉而投奔劉公。這似乎有違于“不既信,不倍(背)言”的俠義道精神。其實并非如此,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聶隱娘既不與魏帥同是非,自也不會與他相與信。這就是所謂的“立氣齊”。就這一點來說,聶隱娘的“背叛”和紅線的“報恩”具有同等的光輝。
《紅線》的作者給故事的敘述設置了一個正義的空間,紅線在其中只要不違背這個設定,她的一切行為就具有天然的正義性;而聶隱娘的作者給她設定的是一個非正義的空間,這就決定作者的故事敘述過程就是聶隱娘不斷突破既定設置空間的過程:作者讓聶隱娘出生在魏博大將聶鋒的家中,如果按這個設定去發展,就可能是和紅線完全相反的命運。所以作者先敘述了她的第一次突破:在她十歲的時候,一個尼姑把她偷走帶到山中,教她各種神奇的武功;然后把她帶到都市,向她指出一些人的惡行,讓她刺殺這些人。有一次,聶隱娘在刺殺一個罪惡深重的大官時,由于這個大官正和他的兒子在一起嬉鬧,聶隱娘不忍下手,所以回來較遲,遭到了尼姑的叱責:“已后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后決之。”
在這次突破中,聶隱娘懂得了是非善惡的標準和判斷,也明白了面對罪惡目標時應該怎么做, “斷其所愛”的真實含義不僅僅是殺掉目標所愛,更重要的是要學會不能以小仁而寬大惡。
聶隱娘藝成后歸家,得到魏帥的喜愛重用,這是聶隱娘向既定設置的回歸。表面看這是倒退,實際上卻是作者敘事技巧的高度藝術化。一般讀者往往忽略這個情節,于是就看不到前后事件的緊密關系。聶隱娘離家時年僅十歲,不會懂得人間的是非曲直和處置應對。學藝五年,尼姑不僅教會了她高超的武功,更教會了她為人為俠的準則。作者有意安排她在魏帥身邊,是讓她近距離的看清魏帥的真實面目,不露聲色的為她對既定設置的最后突破安排好關榫。
《紅線》的作者沒有把這個女俠的高超武功哪里來的做任何交代。據紅線自述,她的前生本是男子,游學江湖間,學神龍藥書,只因用錯了藥,死了三人,陰功得誅,才被降為女子。似乎她的絕世神奇是前生帶來的。由于沒有制定人物性格轉變的敘事策略,人物性格就顯得缺少發展。
小說中對武功的描寫讓人印象深刻,但很注意根據故事的情節而采取不同的敘述視角。同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在《紅線》中,由于盜取田承嗣金盒是紅線獨自一人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完成的,所以作者采取了讓紅線親口敘述的方式,給人以親臨其境之感;《聶隱娘傳》使用的是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因為隱娘和刺客的搏斗是在劉昌裔的眼前完成的,有他人的參與。全知和限知視角的不同,不僅切合兩人當時的情況,而且更重要的,是對于小說意境的創造。
《紅線》的作者追求的是詩的意境,他努力使小說充滿詩的優美,空靈,具有詩性特征。本來是危險叢生,讓人魂魄俱驚的盜盒行動,在作者的筆下卻是詩意盎然的探險旅行,在帶給讀者多姿的審美想象和空闊的審美空間的同時,會產生強烈的審美共鳴。
對武技劍術和格斗場面的描寫,極富傳奇性,這已突破了《紅線》等作品的重在寫意,而具有了極強的寫實效果。這標志著唐人豪俠小說漸趨成熟。
人們往往把中唐的社會現實和小說的創作背景聯系起來,游國恩說:“當時藩鎮割據,互相斗爭,往往蓄養刺客以牽制和威懾對方,而神仙方術之盛,又賦予了這些劍俠以超現實的神秘主義色彩。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找不到出路的人民,也希望有這樣一些人來仗義除奸。”但卻非本文討論的內容了。
【參考文獻】
[1]李劍國.唐宋傳奇品讀辭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3]游國恩.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5.
(作者簡介:王森林,黃淮學院中文系講師,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