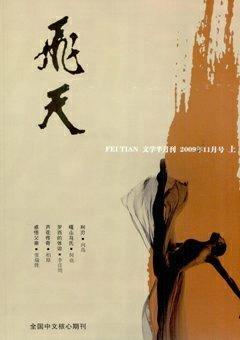克里斯蒂娜.羅塞蒂作品中自我中心的主體意識
張 纓
何自然先生在談到“感情意義”時這樣寫到[1]:“說話人由于個人情感的驅使,在表現言語行為時,對聽話人或他們所談論的事物表現出某種克制、夸大,或加以譏諷、強調等,從而使話語多少帶有感情色彩,顯得更具感染力,并使聽話人獲得更深刻的印象。帶感情意義的言語行為也往往同會話含義結合在一起。”范戴克認為,文學作品的作者實施一系列的言語行為是為了對讀者產生一定的言后之果。文學語言是高度隱含性的,它不僅僅陳述或表達其字面的意義,還希望影響到讀者的態度[2]。哈里斯認為,小說中敘述者的語句,應該歸屬于在自然語言中的相應的言外行為類別。筆者認為,同樣的情形也適用于詩歌。現實中的詩歌也有多種類別,在某些情況下,詩歌中也包含著眾多真實的敘事成分。筆者從言語行為理論的角度看詩歌中表達方式,主要是想從表明個體行為的“言語”特征入手,探究作者對讀者的影響。
在研究語言自我中心性的問題上,需要考慮語言的動態系統特征:言語行為主體所選擇的語言形式反映了該主體的“語言個性”特征[3]。自我中心的主體意識在本文中主要從具有強調意義的詞匯成分、重復結構、感嘆詞等方面來看。
首先,強調詞匯以及結構的重復性。在錢冠連先生看來[4],語用學家關心的東西和文學評論家關心的東西顯然有不同之處:后者所關心的是:形象如何產生了主題思想以及主題思想是否深刻,前者所關心的是一個大的語篇本身明白說出的話語之外還給了什么樣的隱含之意。筆者認為,文學語篇與其它語篇實質的不同,并不在于表現的內容,而在于表現的方式,在于文學語篇為了提供隱含之意而采用的特別手段。這些主要從表明作者情感態度和心理狀態的述謂成分、重復結構等許多方面表現出來。
在羅塞蒂的“歌”這首詩的第一段,詩人就用了幾個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詞:Sing no sad songs for me,/Plant thou no roses at my head,/Nor shady cypress tree,/Be the green grass above me…一連三個否定詞匯,將詩人面對死亡的超然氣質活化在我們眼前。接著,詩人又用了兩個重復的句型And if thou wilt,remember,/And if thou wilt, forget。作為此段的結尾,又用了三個重復的句型作為下一段的開頭:I shall not see the shadows,/ I shall not feel the rain/I shall not hear the nightingale,這樣強勢情感的詩句,雖然在形式上是重復的,但其所起的作用卻是對詩歌出人意料的平靜結尾提供了很好的烘托與陪襯:“Haply I may remember/And haply may forget.”這樣一個看似不經意的結尾,好似一襲薄沙,無法攏住感情強烈又明媚的月光,反而帶給讀者更深的情感體會。一揚一抑的結果并不是感情的止息,相反,卻是欲言又止卻又難止的文學效果。
“SONG”一詩筆調輕盈,雖談論的是死亡問題,卻無沉重之感。在這首詩中,詩人象在對愛人述說,又象是自言自語,其間,滲透著對生者的關懷,也流露出作者淡泊的心態和對人生的徹悟。這首詩以恬淡的憂傷和美麗的寧靜撥動著讀者的心弦。詩人的超然伴隨著對人心的撫慰,在超然之外又多了一分對親情的依戀。懷念與忘記,想起與遺忘都籠罩在濃厚的愛之氛圍中。
其次,感嘆詞以及思維的跳躍性。從語用學的角度出發,文學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不是作者直接出面用話語來表達的,其間所涉及到的“虛”與“實”兩個概念,實,是人物形象,虛,是某個思想、意念或精神。但虛是比實更重要的東西。
在《漢語文化語用學》這本書中,錢冠連先生談到,語用學在文學上的體現,就是其范疇(如語境干涉、附著符號束和智力干涉等等)與規律(如語用原則和策略等等)在具體的文學作品---小說、散文、戲劇、詩歌---中的體現。錢先生特別談到“附著符號束”的概念,他認為附著于人的符號,包括伴隨物、面相身勢與聲氣息,它們參與談話時,會對話語有深刻的影響。伴隨物不是語境中的自然物體,是說話人正在運用中的或者自覺地準備著參與談話的東西。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同樣有必要關注這些附著符號,因為是它們幫助作品產生了意義。
再次,多重假設及主體意識的凸顯。一般來說,在實施具有命題內容的任何施事行為中,說話人對命題內容都會表示某種態度[5]。施事行為的特性也跟預定條件相關。在羅塞蒂的詩中,有些假設的條件是顯形的,有些則是隱形的。在詩歌“Winter: My Secret”中[6],詩人對于吐露秘密,先是斷然拒絕,而后又含混其辭,說也許有一天,但不是今天。緊接著,詩人又一次否定,說秘密是自己的,不會告訴任何人。僅在第一段,詩人的態度就接連三次發生變化。在第二節,詩人似乎無意繼續以上的話題,而開始談論一些似乎與主題不相干的東西,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詩人不愿吐露自己的秘密,是基于心理上的許多假設:寒風會啄我的鼻子,吐露秘密會受到傷害,因此,要戴上口罩。這樣的詩句,雖然是隱喻,我們也不難從中看出詩人的自我防護心理。通讀全詩,我們不難感受到詩人活潑可愛調皮多變的性格,詩人的“不情愿”,以及不合情理的推委態度,這一切都表現出詩人的個人心態:既想同人溝通,又想隱匿自我,喜歡順其自然的個性。而這一切,在這首詩中,都是通過心理上對假設的建立和取消完成的。這樣,正反映了作者矛盾的心情,產生了讓讀者更加關注詩人心靈狀態的言后之果。
這就是克里斯蒂娜·羅塞蒂。她擁有一種驚人的才能,能把這些令人悸動難平的激情,提煉成一種純凈平和的情愫,融入輕婉柔美的韻律和節奏之中。一連串的否定詞告訴讀者詩人的堅定與執拗,重復的結構揭示著詩人情感的持久與強烈,不斷的假設暗示了詩人的謹慎與自守,這一切言語行為的成功實施,向我們展現了一位多彩的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羅塞蒂,恰恰是這一點使我們看到一個特別的她,達到了眾多詩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參考文獻]
[1]何自然.語用學概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6).
[2]Van Dj jk,T.A. Pragmatic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6.
[3]趙華英語“自我中心”語句的語用分析[J].外語學刊,2004,(5).
[4]錢冠連.漢語文化語用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2).
[5]索振羽.語用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7).
[6]董素華.英語名詩賞析[M].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9,(10).
(作者簡介:張纓,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外語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