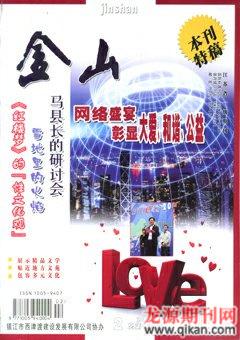一痕山水淡如無
于文清
今年是孫煒兄的不惑之年,趁著過四十歲,熱鬧一下,想要辦個畫展,同時再準備出個小冊子,命我寫幾句話。我本不想應命,因為我實在說不出關于美術評論的一些行話,而這些寫在畫展或畫冊前面的話,還是應該由他的早先業師范揚先生與現研究生導師宋玉麟先生、劉赦先生說幾句才更合適。然而孫煒兄卻以為多年的老友無論怎樣說都行,多承他的美意,我也就只好放筆寫去了。
孫煒兄這四十年生涯,畫畫卻是占去了大半的。四十歲是個不咸不淡的年齡,裝嫩已是不行,充老更是不可,然而四十歲卻是一個不可不對人生進行初步總結的年紀,這個年紀我想應該作一個梳理,回頭望望走過的路,再朝前看看今后的路該如何地走,這樣的回顧與展望我想是必須的。都說畫畫是一條寂寞之道,然而怎樣將這條寂寞之道走出空谷足音來,那是須大智慧、大力量的。
孫煒兄是科班出身,有名師指授,畫藝一路精進,這自不待言。在與之交往的二十余載中,對他我似乎也只總結出兩個詞:淡定與堅守。淡定是一種境界,是與身所俱還是潛心修得,這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境界是從事繪畫創作的人所必須具備的,否則你就跟著浮躁的畫壇瞎轉悠吧,到頭來,等你轉暈了,你就該吃藥了。
如果說淡定是一種內省的話,那堅守則是一種外修。不去湊熱鬧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該如何堅守我們的審美理想?怎樣表現我們心中的筆情墨趣?這一點孫煒兄心里明白的很,他就那樣松松地畫著山,淡淡地畫著水,這符合他自身的性情,也符合中國畫的精神。書畫創作,少年看生動,中年看氣象,老年看趣味。孫煒兄已屆不惑,漸漸地將步入中年,他的畫也漸漸地呈現出清明的氣象,這是多年修持的結果,應當好生護持,假以時日,相信在這種清明的氣象中會開出純凈的花來。曾經有人問過我:學哪一種碑或寫哪一本帖最好?我說最適合你性情表達的那一種最好,只有與你性情合與不合之分,并沒有碑帖好壞之別,選一兩種適合你性情的碑帖寫吧,時間長了,融進去了,化進去了,你就是在書寫自己性情了。書如此,畫亦然。
拉雜了這許多閑話,可能都沒有搔著癢處,孫煒兄見諒了,四十歲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