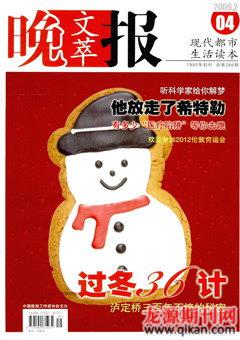能力不敵態度
2009-03-24 05:30:16濟寬
晚報文萃·開心版 2009年4期
濟 寬
初去日本京都女子大學做外教,很是興奮。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我提議引進一個多媒體教學系統,為此我必須向校方提供一份報告。
在國內,寫報告是形式,用不著仔細推敲。可在日本,我卻栽了跟頭:我根據國內的工作習慣,連夜趕出一份報告書。領導很快找到我,說報告內容空洞,毫無說服性,讓日本同事橫山君協助我重做一份。之后,教研室開了多次會,動輒長達六七個小時。報告由最初的三頁變成長達數十頁的“長篇巨制”。最初的報告里介紹了這個系統的內容、特點、價格和用戶反饋。教研室的老先生們看了提出問題:這個系統以哪些學生為對象?要達到什么教學目標?有哪些院校已經采用了這個系統?教學的效果如何?
過了一個月,橫山君的第二稿里有了一個表,上面是日本200多所大學使用這套系統的調查數據。該系統的價值得到初步認可。又過了一個月,橫山君的第三稿拿出來了,明確了將在哪些班級試用這套系統,由哪些教員實施,隨后是第四稿、第五稿……報告人手一份,逐字逐句推敲,有問題就要求橫山君詳細說明。質疑時措辭尖銳,不滿時直言不諱,有爭論,有批評,不但對事,而且對人,簡直就是“審判”!
“認真是日本人的生命線。你不在乎就不行!”橫山君說。在他的幫助下,這套投資兩千多萬日元的系統最終獲得了批準。
和日本人在一起的時間長了,我漸漸明白:相對于“能力”而言,認真的態度更體現一個人的價值。在日本,態度不認真的員工,命運只會是:或者道歉,或者辭職,或者自殺。
猜你喜歡
發明與創新(2022年30期)2022-10-03 08:40:56
人大建設(2018年6期)2018-08-16 07:23:10
文理導航·科普童話(2017年5期)2018-02-10 19:42:14
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32期)2017-10-28 22:48:36
南風窗(2016年26期)2016-12-24 21:48:09
文學教育(2016年18期)2016-02-28 02:34:38
小星星·閱讀100分(低年級)(2015年10期)2015-10-22 08:30:04
南風窗(2015年22期)2015-09-10 07:22:44
南風窗(2015年7期)2015-04-03 01:21:48
中學語文(2015年21期)2015-03-01 03: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