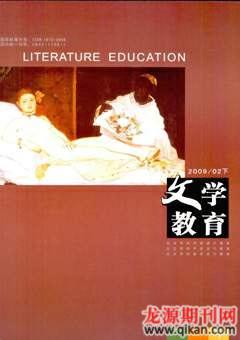從語文教材管窺古代士人的人格境界
在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必修五《報任安書》中,司馬遷說:“《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時至唐代韓愈也有“不平則鳴”說。
文學作品是士人這個古代社會特殊的階層宣泄內心復雜情緒的重要載體,是士人思想情感的形式化。士人的內在情緒借助文學作品外化出來,或哀怨,或憂愁,或激憤,或惆悵……不一而足。士人是文學創作的主體。隨著對蘇教版教材中古代文學作品接觸逐漸增多,理解加深,我覺得這些文學作品除了表現了各個作者——士人個體——的獨特的思想情感外,似乎更有一種彼此共通的心理狀態、價值追求,一種基本的人格境界逐漸凸顯出來。它深深打動并極大感染了我,特別是有些詩歌散文的藝術之境和人格之境達到高度的融合,具有精神的高度,帶給人強烈的美感。如《始得西山宴游記》柳宗元寄情山水,融情自然,他寫道:“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這不就是柳宗元對自我心靈的不自覺發現和欣然肯定嗎?高峻峭拔的西山不就是柳宗元傲世獨立情懷的鮮明寫照嗎?難怪柳宗元物我兩忘,“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陶醉其中,“不知日之入”,“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
士人階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于主體地位。他們是文化的主要承擔者,既繼承既往文化,又不斷地構建和發展當代文化,由此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和文化境況。士人在上古時期一般是指那些未做官的讀書人,屬于士、農、工、商“四民”之一,但他們擁有豐富的文化知識,大多懷有躋身為官的愿望,而且憑借他們的知識才能在現實中具有出仕為官的可能性。所以士人階層除平民知識分子外,也應包括士出身的官吏——士大夫。
士人通常在社會中扮演三個角色:民、官、文化承擔者。民一般是士人原本充當的社會角色,是個體的起點,同時也是被超越的對象。出仕為官是士人們普遍的期望,退則為民,進則為官,介于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文化承擔者是士人的基本角色,特別是其中不少人隱而不仕,或辭官歸隱,或身在官位卻全力構建精神樓閣,如陶淵明、王維等。作為文化的主要承擔者,士人接續古今,馳騁天地,具有超越意識,這個階層具有特定的價值觀和理想追求,由此也具有批判精神。
這三種角色彼此相通,有時在士人個體身上交錯重疊。常見的是士人為民時具有為官的影子,當然為官時也具有為民的印跡。在必修四《論語》的《季氏將伐顓臾》,特別是《孟子》的《寡人之于國也》中,閃耀著“重民”的民本思想。作為民孔子、孟子常寄望君主,以自己的價值觀和理想要求國君,希望統治者能夠“仁者愛人”,施行“仁政”,關愛百姓,這是從民的角度對統治者寄以希望,不僅如此,他們還提出相應的富民、惠民、養民、教民的具體措施。從為官的角度看,孔孟則提出“齊之以禮”,“為政以德”,希望教化百姓,“修文德”,“申之以孝悌之義”,規范社會倫理道德,建立一種禮樂秩序,約束人們的行為,順從朝廷,從而穩定和發展社會,最終達成“王道”,達到國君“譬如北辰”,眾民如“眾星共之”的理想社會。
先秦時期,諸子開宗立派,著書立說,指斥時弊,盡管到了漢朝以后這樣的自由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但士人們的社會關懷卻一成不變。“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士人們無論是得志還是失意,總認為自己對天下負有責任,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相應也具有匡世救民、建功立業的使命感。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對周公瑾的仰慕,王勃在《滕王閣序》之所以抑郁寡歡等中無不體現這一點。這一切形成了中國古代士人階層社會關懷的重要特征,進而滲透到民族心理層面,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一個極為突出亮點。
士人作為文化承擔者,有著自己的獨立的精神、鮮明的價值觀和強烈的理想追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士人并非都是利祿之徒,他們有著對“名”的渴求,爭作“名士”,這不僅是一種身份的追求,更是一種精神的渴求,甚至有人將名傳后世的榮耀視同生命。士人追求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主要與“名”有關。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闡述自己甘于自沉縲紲之辱,“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卻不引決自裁的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士人對宇宙、生命具有極為敏感的覺察和體驗。《論語·子罕》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這恐怕是這方面最早的記載了。必修一《赤壁賦》中,蘇子與客的對話毋寧說是蘇軾內心的一次交鋒,蘇軾自感生命渺小卑微,“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因而有著對永恒宇宙的無限的羨慕和向往,“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必修五教材上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感嘆道“曾不知老之將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士人對人生易老、世事滄桑、生命苦短的感慨,對死的恐懼、對生的眷戀溢于言表。在有的詩文中士人甚至在悠悠天地中感到深深的孤獨和悲愴。士人企望建功立業,追求名譽,常因生命易老而倍感急迫因而嘆惋,蘇軾、杜甫的詩文時常表現出這一點。另外,即便士人功成名就,也會被心靈深處的憂慮所糾纏,產生莫名的閑愁,晏殊可謂是一個典型。這種閑愁不是無所事事而產生的百無聊賴之感,而是一種不知所以然的淡淡的惆悵失意和哀傷。賀鑄也是如此,《青玉案》云:“試問閑愁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這些是心靈深處焦慮的呈現。此種焦慮長期郁積在心靈深處,當有外物刺激時,閑愁心緒則會悄悄流出。
渴望建功立業,追求顯赫名聲,希望延續生命,這種種不滿足折磨著士人敏感的心靈。處于這種心靈困境中的士人常常努力去尋求自我超越、自我解脫的心靈自救之術,從而使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內蘊豐富,也使中國文化具有鮮明的特色。
道家認為萬物本體是“道”,強調自然無為。對士人個體而言,個體應拒斥一切社會文化規范與價值觀念,消解心靈的一切憂慮,達到沖虛清靜、自然無為的人格境界。必修五《逍遙游》中,莊子深化了老子哲學中的自我超越的方式,借助于超凡的想象力,使自己的精神自我無限膨脹起來,從而超越時空、超越憂樂,融入一種不累于物、俯仰自得、無私無欲的心靈凈地,達到自由自適、神妙高遠、飄逸逍遙的理想精神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個體在想象中駐足于此自然與逍遙的境界中,人世間一切生死痛苦、進退榮辱便瞬間渙然冰釋了。
佛家擺脫放棄對通行世俗觀念作價值判斷,直至擺脫放棄常人思維方式,從而悟而見性,進入一種清凈澄明、寂然不動的全新精神境界。《唐詩宋詞選讀》中《山居秋暝》寫道:“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營造如此清新自然、空靈灑脫的境界,詩畫俱佳的王維,不只長于描摹,更在于王維的藝術追求和精神指向一致,其精神指向大概是決定因素。此類詩有的還具有悟而見性的釋家意趣、理致。
儒家以經世救國為要義,社會理想高遠,以自我心靈修養構建為主要手段,達到剛健有為、公忠為國、誠心為民、堅守氣節、以義制利的人格境界。如文天祥的《〈指南錄〉后序》便是典型代表,如此人格境界至今可以激勵人們產生發憤圖強、報效祖國的責任感,培養節制物欲、追求高尚的情操,鍛煉民族個體自尊自強人格。
在這以上種種的人格境界中,個體精神是獨立自由、自覺自適的,因而這樣的人格境界是審美的、詩意的,藝術之境與人格之境相通相融。例如唐代三位最有影響的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就分別代表了以上三種藝術之境與人格之境相通相融的類型。李白被稱為詩仙,作品自然清新、飄逸放達,是老莊人格境界的顯現;杜甫被稱為詩圣,作品沉郁頓挫、穩健典雅,是儒家人格境界的展現;王維被稱為詩佛,作品空靈清寂,是佛釋人格境界的體現。
儒、道、佛之間有相通之處,特別是在超越人生境界的追求,現實尷尬處境的解決,內在深重焦慮的緩解方面,使士人達到新的精神高度,為士人心靈提供棲息安居之所,也使中國古代文學園地多姿多彩。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整體特征是“政治化了宗教,倫理化了政治,文學藝術化了倫理,人生化了文學藝術”。
“骨正風高自精神。”在課堂教學中,我們應注重文學體驗的豐富構成,注重學生的信念形成、心靈成長和人格塑造,從典籍的藝術境界、士人人格境界中汲取養分,讓文學的社會使命得到充分的恢復和完整的展現。
徐曉華,教師,現居江蘇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