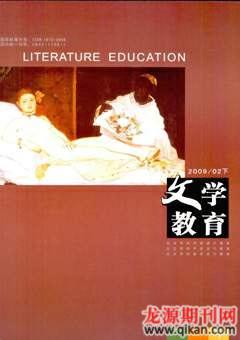耶里內克初期創作的倫理啟示
200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艾爾弗雷德·耶里內克,被文壇譽為“女性法西斯主義”,其基本思想的形成在她創作之初的三部小說《我們是誘鳥,寶貝》、《逐愛的女人》和《米夏埃爾》中已大體具備雛形,對性、暴力、虐戀等欲望主題及其裸語直陳的表現形式都有所嘗試,后來經《鋼琴教師》、《情欲》等作品將這些方面的表現漸趨專注、成熟并推向極端。就現有研究資料對耶利內克的傾向性態度來看,其創作顯然屬于學術正統少有染指的“性文學”(指著力于對性欲、性愛、性行為和性心理進行藝術審美并深度表現的文學作品)范疇。
當我們面對20世紀末的中國文壇,“無性不成書”已成為作家取悅讀者的重要手段,并構筑了一道誘人的文學風情園,先前跟著西方學舌的國內文學終于追上了時代的步伐,與同時期的西方性文學相映生輝。在80年代勞倫斯、杜拉斯、昆德拉、納博科夫等“涉性文學熱”之余,奧地利女作家耶里內克在不斷的詆毀與贊譽中后來居上。她的小說面對一個物欲橫流的、金錢至上的社會,抓住了人們的消費心理,她的初期作品體現的權欲、情欲、占有欲、強奸欲、破壞欲等,沖破了傳統倫理所能接納的文學禁區,并以此開啟了她文學創作道路的與眾不同。更讓文壇和讀者倍感意外的是瑞典文學院對她作品的認同,除爭議與質疑之外,又何嘗不意味深長?本文僅借助于耶里內克初期創作的幾部作品,探視那些剝離了“愛”的“性”究竟意味著什么?
一
商業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滿足了人們需求的同時也放縱著欲望,使固有的道德與禁忌隨著一代代世風日下的墮落而松動。生活中的性享樂追求和小說里的“色情描寫”,使兩性情愛關系中的身體因素凸現出來。20世紀性自由的試驗在文學領域全面展開,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道德固守后,60年代最終從法律上解禁的西方世界,各種性學思潮轟轟烈烈登上了大雅之堂。此時闖入文壇的耶里內克及性主題小說有了難得的天時地利人和,她的寫作思考自然就從這解禁后的性問題開始了。
在《逐愛的女人》中寶拉為了養家糊口,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去做娼妓,而從陌生男人那里拿到錢來討好自己的男人,可結果是什么也沒得到還被埃里西無情地拋棄。面對同樣的生活,我們的文化卻對男性拈花弄草寬容得多,比如海因茨與布麗吉特發生關系時還纏著漂亮的蘇茜。當事人顯然認同這種性權力的不對等,女性似乎被排斥在性的話語和享受之外,其間兩性關系的不公正性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在女權運動和性解放之后的泛性年代。早在《我們是誘鳥,寶貝》中,透過作品對性器描寫與性行為的刻意渲染,粗俗而悲苦的女性的命運,如同一個人人都可受用的工具一樣任意拿放,作品的描繪中到處充滿了血腥,到處滋生著暴力。像埃里卡殺死父親,奧托殺死朋友,女性淪為男性陰謀的幫兇。作者把人類最隱私的東西直露地擺在了我們面前,以展示性的生物稟賦和自然狀態。但這種來自性的“生命狂歡”給予我們的警示,一如埃利斯《性心理學》所言:“性是一種充盈于生命中,并提高生命質量的強大的力量,但是,人們對性保持著恐懼的心理。”耶里內克試圖用強刺激的矯枉過正讓人們習以為常。《米夏埃爾》中寫英格·邁澤的八處“我性欲強極了”的自我言說,每次基本重復的描寫,把一個女人對性的要求寫得如此赤裸,已經開創了先河。接著描寫比爾叔叔這個男人的性渴望一段更是一種非常態的發泄。盡管像弗洛伊德認為的那樣,性是人類饑餓本能,如同吃飯睡覺一樣。然而,自然主義式的直白并沒有讓讀者覺著美味可口,正是這種反向效果的追求傳達出“性生態”(自然兩性關系與人類精神世界的沖突與和諧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失衡與扭曲的隱喻。
可見,在耶里內克編制的兩性關系中,性的生命力展示主體是男人,而動力源卻在女人那里。有一點是我們應該明確的,只要你是女人,就有先天的“誘惑基因”,你就對男人有一種罪性的吸引。只是這種吸引的結果卻產生了力量的倒置,最終反而傷害了女人自己。
二
我們知道,在東西方共同的兩性觀念里,“愛情——婚姻——性”是三位一體的,但在現代社會中,這種一向經典的理論已經變得糾纏不清。錯位了的“性”更多的是一種享樂和繁衍的寄托,而非表達愛情的方式。耶里內克在《逐愛的女人》中描寫的兩樁婚姻就能很好的說明這一點:“這些女人通常以嫁人或者其他的某種方式毀滅。”在她們中,一個是有心計卻很現實的女人,處心積慮地討好為了得到能給她帶來財產和身份的男人;一個是懷著純潔愛情幻想的女人卻悲慘地被生活所愚弄和拋棄。她們希望在愛的追求中去找到自己的幸福,結果是他們卻變成了“性”的奴隸,處境是被無情地占有、屈辱地生存。城里的女工布麗吉特視“兩性生活”為一種手段,因為她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上認識了一個能以后給他生活保障的男人——海因茨,從此她就挖空心思去討好海因茨和他的家人,甚至奉獻她的肉體盡量去滿足男人的欲望,通過懷上海因茨的孩子成了他的妻子。但這種性的生命連接卻淹沒了愛情,也鑄成了一樁無愛的婚姻。布麗吉特身上已沒有了愛,海因茨呢——不喜歡布麗吉特,但他還是受不了她的誘惑。埃利斯還曾說過:“婚姻和愛情都以性生活為基礎,性和諧是婚姻和諧的保證。”對于這一點,我們從布麗吉特的身上沒有看到,在寶拉的身上也沒有看到。《逐愛的女人》這樣描述寶拉的追求:“學完裁縫以后,享受一下生活,去意大利,花自己掙的錢去看電影……然后結婚跟他生孩子,生活在一起并相愛。”開端是美好的,但她愛上了一個不值得她去愛的人,并且更不應該懷孕,陰差陽錯筑成千古之恨,她的夢破滅了。
事實告訴我們,愛在現代生活中早已經不起考驗。從理論上講生活是一個大的百科全書,生老病死,喜怒哀樂,飲食起居等無所不包,當然也包括愛情。而作品呈現給讀者的冰冷的現實是:生活遠遠比愛情殘酷。不要被愛情沖昏頭腦呈現出女人的軟弱,女人決不要在消亡的愛情中把自己交付于男人,成為男人“性”發泄的工具。布麗吉特的身體就是女人和不愛她的男人之間的交易資本,這樣的兩性關系意味著:性成了消費品,只是為了人們提供某種身體上的需要,與婚姻和愛情沒有必然關系。在男女的情感世界里,費爾斯通認為,女人在性生活中總是處于不利的地位,男人可以割斷他們性需要與情感需要之間的聯系,而女人則做不到。擁有了浪漫、性和男人,她們才是最幸福的人。寶拉的結局就說明了這點,她們的靈魂被生活壓力無情地粉碎后又被肉體吞食,導致愛情在物化災難中成了瀕臨滅絕的珍稀物種,是那樣的脆弱而不堪一擊。
在性泛濫的欲望化時代,愛情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遙遠,情與愛作為文學主題表現力生成源也越微薄渺茫,性在這個時代成了藝術本身,就如同一個漂亮女人成為大家觀摩的對象一樣沒有一點遮攔。耶利內克通過作品里肆意地性描寫,直擊人性深層那原始、野蠻而殘酷的欲望中心,這不簡單地表現為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身體的征服,而是時代性意識混亂與兩性關系不和諧的表征,從中體現的是文學中欲望敘事的本真意義。在這樣一種性解放之后,“性”突然之間變成了一種游戲被直接暴露于公眾的面前,讓人們以肉體的渴望填充精神的空虛。愛情的價值消亡后,剩下的就是與權、錢等值的赤裸裸的交換了。
耶里內克的小說從始至終展現出這個時代性的生命力及存在狀態,自然還有相隨的愛情漸次消亡的過程。耶里內克也想通過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來喚起女性的清醒,以應和福柯對文明的忠告:從性中解放出來!走出人類對性的病態憎恨和偏執迷戀的誤區。但文學如何適當地去觸動性問題——這一敏感的社會神經?在耶里內克的小說里我們沒有找到答案,然而,我們卻得到了啟示:性愛分離的兩性關系作為性解放和技術文明的產物,盡管背離了伊甸園的理想圖式,可已經是既成的現實。對此,無論是道德的壓抑,還是行為的放縱,都不是自然的表現,更成熟的態度應該是寬容而不過多的關注,當然,炒作是最拙劣的“藝術”方式。而對于評論界來說,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的描述極具借鑒價值:“現在,傳統道德受到了動搖,而人們還沒有提出新的道德觀來取代它。舊時的責任已經失去了它們的威力,而我們尚無法清楚而肯定地看到我們新的責任是什么。不同的思想觀念擁有相對的看法,我們正在經歷一段危機時期。因此,我們不像過去那樣感受到道德規則的壓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陳淼霞,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