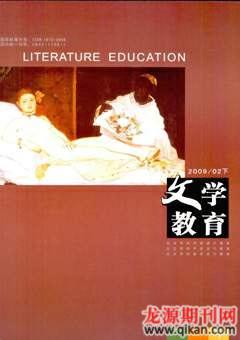《琵琶行》與《李憑箜篌引》里的音樂描寫
趙 冬
音樂,能給人帶來聽覺的享受,心靈的撫慰,而一篇描寫音樂的優美篇章,更能愉悅身心,陶冶情操,讓人浮想聯翩,心馳神往。人教版第三冊中的《琵琶行》和《李憑箜篌引》都是描寫音樂的杰作,現將這兩篇詩歌中的音樂描寫作一比較。
一、從思想內容方面比較
兩篇都細膩再現了音樂飄忽多變的過程,借以展現樂曲的美妙動人、技藝的精湛高超。《琵琶行》中,嘈嘈的大弦給人粗重之感,而切切的小弦又帶來竊竊私語般的輕細,這兩種旋律交錯出現時,樂聲清脆婉轉,如同珍珠灑落玉盤,黃鶯啼叫花底,很快低沉冷澀就像泉水在冰下艱難流淌時發出的嗚咽聲,接著,“弦凝絕”、“聲暫歇”,悄無聲息,經過這一跌宕起伏之后,樂聲猶如“銀瓶乍破”“鐵騎突出”,竄向高潮,激越高亢,隨 即又在“四弦一聲”中戛然而止。整個過程可以顯示為:清脆婉轉——低沉冷澀——悄無聲息——激越高亢——戛然而止。再看《李憑箜篌引》。樂聲時而如山崩玉碎,激越高亢;時而似鳳凰鳴叫,悠揚婉轉;時而低沉憂傷,讓芙蓉悲泣;時而清麗歡快,使香蘭歡笑。
曲折有致的描寫中,兩篇都把音樂動人的旋律清晰的譜寫下來,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神奇瑰麗的世界。然而,《琵琶行》中寫音樂,意不在寫音樂而在寫人,那千變萬化的音樂,就是琵琶女滿腹心事的吐露,就是琵琶女坎
坷人生際遇的寫照。而《李憑箜篌引》只是在音樂的倏忽萬變中極力展現李憑演奏箜篌的卓越技藝,別無弦外之
意。
二、從藝術特色方面比較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兩位詩人構思精巧,都利用先聲奪人的方式,為主人公的出場作了濃重的渲染,也為讀者留下懸念,激發起大家想一聽為快的強烈欲望。《琵琶行》中,主客潯陽江頭“慘將別”,“忽聞水上琵琶聲”,頓時,“主人忘歸客不發”,都沉浸在美妙的音樂之中,千呼萬喚后,琵琶女終于“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出場了。開篇先寫琴聲,雖寥寥數語,卻恰似精彩演奏會的前奏,已經給人美好印象了。《李憑箜篌引》先在制作精良的箜篌和悠揚動聽的樂聲中拉開序幕,接著再讓演奏者閃亮登場。那樂聲何等美妙,能讓空曠山野中的浮云駐足傾聽,能讓善瑟的湘夫人和素女傷心落淚,也能讓我們對那位神奇的演奏者充滿無限遐想,最后,詩人才挑明“李憑中國彈箜篌”。
音樂是無形的,而兩位詩人都能夠借助豐富的想象將抽象的音樂轉化為具體可視的物象,讓我們如聞其聲,如臨其境。兩人的想象卻又各具特色。聽到琵琶女的琴聲,白居易把優美的聽覺形象轉化為優美的視覺形象,“急雨”、“私語”、“大珠小珠”、“間關鶯語”、冰下的泉流,所有的視覺形象都從作者的生活實際出發,貼近現實,因而,白居易的想象具有現實主義特點。而李賀的想象大膽奇特,不拘對象,不限時空,縱橫馳騁,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江娥素女女媧在側耳傾聽,浮云老魚瘦鮫也沉醉其中,昔日的妃子與當今的皇帝,人間的萬物與天上的神靈似乎都在參加李憑的音樂盛會,沒有時空的界限,沒有人與物的差別,整個詩篇洋溢浪漫主義色彩。
同是寫音樂,白居易更喜歡正面描寫。借助語言的音韻摹寫樂聲,如“嘈嘈”、“切切”、“間關”、“幽咽”這些詞語摹寫出樂聲的各種變化,不僅如此,詩人還在一連串生動比喻中加強樂聲的形象性。
李賀卻更喜歡側面描寫,借助聽眾的一系列反應側面襯托出音樂的巨大魔力。悅耳的箜篌聲一經傳出,補天的女媧聽得乳了迷,竟忘了自己的職守,結果“石破天驚逗秋雨”;老魚瘦鮫不顧身體的羸弱無力,伴隨著音樂翩翩起舞;伐樹的吳剛,倚靠桂樹,忘記了勞作的疲倦,聽得如癡如醉,就連蹲伏一旁的玉兔,任憑深夜的露水浸濕身上,也不肯離去。在音響效果的描寫中,含蓄表達著詩人自己對樂曲的感受和評價。
當然,白居易筆下也沒忘側面描寫。“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以無聲襯有聲,達到一種余音裊裊、余意無窮的藝術境界。李賀詩中也有正面描寫,“昆山玉碎鳳凰叫”比喻中點出樂聲特點,“芙蓉泣露香蘭笑”擬人中以形寫聲,以情傳聲。
樂聲雖然變化無窮,但兩位詩人都能用他們獨特的體驗、生花的妙筆為我們捕捉到那精彩的瞬間,奉獻給我們音樂連同文學上的精神享受,也給我們留下寫作上的諸多啟迪。
趙冬,教師,現居湖北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