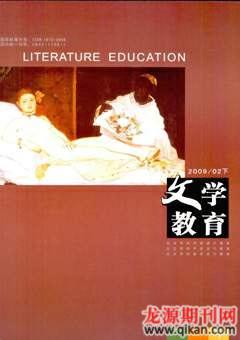《嬰寧》不應(yīng)做刪節(jié)處理
《嬰寧》是魯教版《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一篇文章,執(zhí)教時我注意到編者把它選入教材時,刪去了一節(jié)內(nèi)容:
庭后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之,輒呵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墻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于心,大號而踣。細(xì)視非女,則一枯木臥墻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之,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燃火獨窺,見中有巨蝎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fù)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訐發(fā)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諗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誣訟,將杖責(zé)之。生為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shè)鶻突官宰,必逮婦女至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fù)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需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fù)笑,雖故逗之,亦終不笑。
刪除的原因,我估計編者認(rèn)為里面?zhèn)€別詞句有不潔之嫌,易引發(fā)不健康的聯(lián)想,不適合學(xué)生閱讀。另外,在閱讀過程中,我注意到一些先生對此段文字也有否定評價,譬如聶紺弩老先生寫到:“《嬰寧》篇,是一篇藝術(shù)性很高的作品,嬰寧是一極美的天真少女形象。這篇作品,如果只寫到結(jié)婚而止,真是題無剩意,態(tài)有余妍。不幸后面有這么一段(與以上內(nèi)容同),試問《嬰寧》一篇,何須有些節(jié)外生枝,特別是那些污穢字句,真是‘刻畫無鹽,唐突西子。”趙儷生先生也認(rèn)為:“在全部《聊齋》的言情小說中,《嬰寧》一篇應(yīng)當(dāng)被公公道道推為壓卷之作,故事好、文筆好、語言對話好、寫景也好……自然《嬰寧》篇中也不是沒有糟粕的,如用枯木巨蝎謔虐西鄰浮浪子致死的一段情節(jié),為不必有耳。”不知這類評價是否也影響了編者。
然而從蒲松齡的生命歷程及《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主旨看,我認(rèn)為這段文字不應(yīng)刪。
首先,從蒲松齡先生本人的生平及創(chuàng)作歷程看。
蒲松齡生于1640年,于1715年逝世,一生飽受生活貧寒之困和科舉失意之苦,可算是封建時代一位標(biāo)準(zhǔn)的懷才不遇的窮書生。他從二十歲左右開始寫作《聊齋志異》,至四十歲才初具規(guī)模,以后逐步增補(bǔ)、修改,直到晚年才告完稿,此書可謂是耗盡他畢生心血的杰作。眾所周知,一切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總是洋溢著作者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氣息,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現(xiàn)實。蒲松齡先生的創(chuàng)作也不例外。馮鎮(zhèn)巒先生說:“此書(指《聊齋志異》)多敘山左右及淄川縣事,紀(jì)見聞也。時亦及于他省。時代則詳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外作文,鏡花水月,雖不必泥于實事,然時代人物,不盡鑿空。”(讀《聊齋雜說》)易宗夔先生也說:蒲松齡“目擊清初亂離時世,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書孤憤而諗識者”。(《新世說》)這些評論都在說明《聊齋志異》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清醒落寞的窮書生用自己的冷眼熱腸審視處身其中的社會,表達(dá)了對一個沒落時代的不滿。蒲松齡曾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比擬為韓非的發(fā)憤著書,用他在《聊齋自志》中的話說,就是“集腋成裘,妄續(xù)幽靈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所以《聊齋志異》一書的創(chuàng)作,雖是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氣息,但最深層、最為根本的目的在于表現(xiàn)作者的現(xiàn)實感受、經(jīng)驗或精神上的向往、追求。蒲松齡筆下的神仙、狐、鬼、花妖,都是出自他個人心靈的創(chuàng)造,凝聚著他大半生的苦樂,表現(xiàn)了他對社會人生的思考和批判。
其次,從《聊齋志異》在文學(xué)史上的價值及地位看。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短篇小說中,用文言作成,以敘寫怪異故事為基本特征的所謂志怪傳奇小說,歷史最為悠久,它始于漢,興于魏晉六朝,復(fù)盛于唐,宋元明也有此類作品,只是已呈式微之勢。但出生于清初的蒲松齡,在此類小說已如日薄西山之際,卻憑一部《聊齋志異》,傾倒了天下文士,連一些名位甚高、視小說為小道的詩人、學(xué)者也為之刮目,成為這一領(lǐng)域當(dāng)之無愧的霸主,原因何在?就在于先前的此類作品重在構(gòu)想之幻、情節(jié)之奇,目的是供讀者“游心娛目”,不甚考慮有所寓意。而《聊齋志異》有了巨大飛躍,“假幻設(shè)以寓意”成了作者創(chuàng)作意識中的主導(dǎo)原則,“假幻設(shè)”有對文學(xué)藝術(shù)魅力的追求,更有不得已之處,因為蒲松齡所處的時代是動亂和黑暗的;但最深層、最為根本的目的在于寄寓現(xiàn)實意蘊。所以《聊齋志異》中的神怪狐鬼,不論其如何奇幻,讀者往往會覺得親切,有現(xiàn)實味兒。這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明末志怪群書,大抵簡略,又多荒怪,誕而不情。《聊齋志異》獨于詳盡之處,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fù)非人。”(《中國小說史略》)實際上,蒲松齡無意讓讀者對自己虛構(gòu)的鬼狐花妖完全信以為真,他結(jié)撰這類奇異的故事,是作為文學(xué)事業(yè),以寄托情懷的。他期望于讀者的,也只是能領(lǐng)會其中的意蘊,理解他用幻想的方式把狐精、花妖、女鬼等置于現(xiàn)實生活中,是委婉而又辛辣的揭露當(dāng)時的社會現(xiàn)實,同時又借她們超現(xiàn)實的力量表達(dá)自己反抗和改造當(dāng)時社會的理想和愿望。可以說正是因為這深層的意蘊,使《聊齋志異》徹底擺脫了前人志怪小說的窠臼,并且避開了這一類小說容易陷入的怪異、荒誕、不知所謂的泥潭,開創(chuàng)了一個嶄新的創(chuàng)作境界。孫犁先生說:“《聊齋志異》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的大書……其中很多篇寫了狐鬼,是現(xiàn)實主義的力量使這些怪異成了美人的面紗,銅像的遮布,偉大戲劇的前幕,無損于藝術(shù)本身。”
綜上兩點,現(xiàn)實主義是《聊齋志異》最基本的精神底色,是其根本價值所在。所以作為讀者,只有讀懂這深層的意蘊,我們才是真正理解了蒲松齡;也只有感知到那現(xiàn)實的憂憤,我們才是真正走進(jìn)了非但不荒誕、反而合情合理充滿斗爭精神的千古佳作——《聊齋志異》。
回到《嬰寧》的刪節(jié)問題上,如果把嬰寧進(jìn)入現(xiàn)實生活、進(jìn)而導(dǎo)致性格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刪掉,讓“笑已成生命特征”的嬰寧突然“對生零涕”,單從情節(jié)發(fā)展上就難以理解。更為重要的是,刪掉這一段,是對作品現(xiàn)實底色的極大破壞,是對蒲松齡先生創(chuàng)作精神和主旨的閹割。因為刪掉這一段,讀者無法感知丑陋的現(xiàn)實力量對美好性情的摧殘,難以體會僵化的禮教對一個鮮活生命的“吞噬”,充其量只留下一個“美”的印象——美麗的故事,美麗的狐女,而這種“美”又只是桃花源式的,虛無縹緲、遙不可及。如果文章真如此結(jié)構(gòu),意義何在?而且這樣的“美麗”豈不讓蒲松齡有粉飾太平之嫌?劉烈茂先生曾談到:“蒲松齡憎恨黑暗的現(xiàn)實,自然也憧憬美好的理想。不過,他表達(dá)理想的方式,主要不是靠虛構(gòu)桃花源式的理想境界,而是在批判黑暗王國的同時,寄托了解決社會問題的理想傾向。”所以蒲松齡的“虛幻”絕非荒誕不稽或虛無縹緲的空想,他的“旨意”不是把人們引向茫茫太空,而是啟發(fā)人們深化對現(xiàn)實的認(rèn)識。寫嬰寧進(jìn)入現(xiàn)實生活進(jìn)而性格被迫轉(zhuǎn)變的這一段,正是對這一“旨意”的表達(dá),對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文章至關(guān)重要。只有還原這段文字,我們才能看到蒲松齡先生的本來面目——一個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將嬰寧處理為狐女,由一個所謂“鬼母”培養(yǎng)成人,又將她安排在野鳥格磔、遠(yuǎn)離塵寰的環(huán)境中,因為他深知嬰寧反璞歸真的性格只能在他的理想中存在,在現(xiàn)實生活中無法成長生存。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婦女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生活的重?fù)?dān)、禮教的韁索,使千千萬萬的女子猶如巨石之下的小草,枯黃柔弱,早已失去了生命的色澤,無拘無束、無所顧忌的放聲大笑對她們而言是“天理難容”,她們只需奴顏婢膝、恪守“笑不露齒”的古訓(xùn)。這黑暗不公的現(xiàn)實始終壓在清醒的蒲松齡心上,而且鋪就了他文章的底色。讀者只有觸摸到這層底色,才更加感覺到嗜花愛笑、天真無邪,像山花一樣爛漫、像山泉一樣純凈的嬰寧是多么可貴!她清新動人的笑容真如一道燦爛的陽光破空而來,照徹這個沉重污濁世界的每一處角落。被刪除文字不但是這現(xiàn)實底色的凸顯,而且充分說明了丑陋的現(xiàn)實生活對天真爛漫的理想性格的殘酷扼殺。雖然這樣的結(jié)局可能會使讀者惋惜,但符合嚴(yán)酷的生活規(guī)律。也只有寫出這種結(jié)局,才表現(xiàn)出作者對現(xiàn)實認(rèn)識的深刻精微,反映出他深廣的憂憤。這才是完整而真實的蒲松齡,這樣的文章才符合《聊齋志異》的本色。
所以,課文中被刪文字在《嬰寧》一文中并非可有可無,它是全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全面深刻理解作者及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刪去這段文字,會造成對文章的狹隘淺薄理解甚至誤解。至于詞句不潔問題,我覺得也并非像想象的那么嚴(yán)重。它比之一些文學(xué)名著包括《紅樓夢》,比之當(dāng)下流行的影視作品,性色描寫的分量可謂輕之又輕。而且現(xiàn)在已非談“性”色變的年代,隨著時代的進(jìn)步,性教育在某些地方早已成為學(xué)生的必修課程,從當(dāng)今學(xué)生的接受心理和年齡看,這點內(nèi)容的出現(xiàn)不會引發(fā)多么不健康的后果。
鑒于此,建議編者對課本修訂時,將這段文字補(bǔ)上。也希望編者在編輯教材時,對原文尤其是公認(rèn)的名篇佳作的刪節(jié)處理一定要慎重。
沈云杰,女,山東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語文教育碩士,山東濟(jì)南中學(xué)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