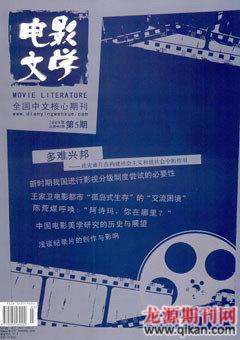當代中國電影“弒父者”人物形象構建
王玉坤
摘要家庭中的父子關系出現疏離、分歧或矛盾,象征性轉喻了父輩與子輩間文化上的沖突、意識形態上的隔閡。“弒父”大都發生在社會即將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父輩的意識形態已不適應社會的發展,遭到子輩的質疑和抗拒,逐漸成長的子輩試圖擺脫父輩話語權的桎梏,奪取話語表達權,重新構建社會秩序。在此種背景下,影片對子輩“弒父者”的言說采取了共性化的人物建構策略,突出了家庭倫理矛盾背后激烈的新舊文化沖突。
關鍵詞弒父;弒父者,人物形象構建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電影,在經歷種種社會變革、文化沖突時,影像世界中子輩的成長與掙扎總是著力表現逃離原有父權體系,掙脫現有話語權的束縛,“弒父”現象成為不同時期對于文化變革的強烈呼應。在“弒父”的文化代際過程中,影片在子輩“弒父者”人物塑造方面,對作為“弒父者”的子輩分別從其所處的壓迫性環境、所屬的邊緣化身份進行雙維度的建構,形成“弒父者”受壓迫、受排擠的人物特征。還將個體主人公納入人物組群,將個體的叛逆經驗拓展為社會的群體性叛離,從個體對父親的反抗衍生出子輩對父系權威的挑戰。
一、“鐵屋”中的年輕靈魂
渴望擺脫權威、自主選擇生活的主人公,卻往往出現在父權高高聳立的地方。象征封閉和傳統的古老庭院、陳舊弄堂、偏僻山村,甚至是象征政治強權的軍區大院,都成為敘事的空間。這樣的敘事空間,形成了新鮮與陳舊、圍困與叛逃的二元對立意象。魯迅先生曾經將封建中國比作。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表現“弒父”母題的電影也樂此不疲地建造著一間又一間壓抑的“鐵屋子”,被囚禁著的年輕子一代,要么無聲無息地窒息死去,要么就要打破父權的牢籠,沖出去獲得新生。
這間“鐵屋”可以是皇宮、軍區大院,由一個亦父亦君的中央集權掌控著每條秩序、每個人的命運,強調對子輩的絕對控制。可以不問是非,為所欲為。這間鐵屋也可以是庭院、老宅,代表著家長權力半是壓迫半是挽留地牽絆著子輩“弒父”的腳步。這間“鐵屋”還可以是偏遠的鄉村、小鎮,象征著封閉、落后、愚昧的傳統價值觀對人性的制約與壓抑。
影片中的子輩都是年輕的主人公,他們處在一個青春期將過而未過的時期。他們厭煩權威榜樣的教誨,反感禁錮思想、情感的僵硬法則。子輩在壓抑下體驗著青春的萌動:夢想、愛情、痛苦、死亡,脫離父輩掌握的人生經驗陌生而新奇,充滿著不可名狀的快感。處于狹小、壓抑、封閉空間的子輩向往著一個更為寬廣的天地。
《植物學家的女兒》里這間“鐵屋”是一個在小島上由父親管理的植物園。子一代生于斯,長于斯,她們如同父親栽種、澆灌的植物,被父親賜予生命。父親為她們制訂嚴格的法則,生活上嚴格的作息時間,飲食上的偏好,無一不是以父親為主體的。她們被忽略、漠視,小心翼翼地忍耐和生存。但在循規蹈矩的表象下,她們也像植物一樣生長茂盛,年輕的生命同樣充滿青春的騷動,在黑色的牢籠中蠢蠢欲動。她們雖然處于嚴密的監視和管制下,但卻還是忍不住偷嘗自由和反叛的禁果。積蓄年輕的力量。如同顧城在《一代人》中的宣誓:“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子一代鮮活的生命注定要與陳舊的“鐵屋”抗爭,擺脫父權的控制。
二、游離的邊緣族群
子輩往往并不是處于社會上層和中心的大人物,而是脫離家庭生活軌道、脫離正常社會秩序的邊緣人物。被流放的太子、卑微的轎夫、騙子、小偷、同性戀者、妓女、吸毒者、藝術青年等。他們在生活中處于劣勢,在精神上卻有超越常人的思考。他們逃離家庭不再受父親的控制,他們的生存困境是來源于社會上各種力量的控制與壓迫。影片試圖給這些反叛的角色以話語權,矛頭則直指無所不在的一元權力中心。
《北京雜種》中茫然的藝術青年、作家以及混混,在喧囂城市里無所事事地游蕩,散落的、碎片化的個體生命經驗浮現出焦慮、躁動、憤懣、抑郁、迷失。“我們都是一樣的……由著性子胡來,想怎么著就怎么著……是社會的異己分子”,試圖用逃離、蔑視社會常規來反抗主流意識形態,卻不知道應該去向何方。
電影中常以音樂的邊緣化來表現人物的邊緣化身份。邊緣化的音樂對情感的表達是非主流的,坦蕩、赤裸、不加掩飾,呈現出一種情感的碎片化形態,可以觸動心靈卻沒有終極目標的精神夢想。《黃土地》中顧青到陜北的目的是搜集民歌信天游,它象征著傳統文化的深層內涵,新文化也要向其中尋找力量的根源。而信天游的民歌又是在那個惡劣的生存環境下當地人民對命運無力地吶喊,唱“酸曲”是為人所看不起的。影片開始的喜宴上,唱“酸曲”的漢子只能以類似乞討的表演混口飯吃。所以翠巧的“酸曲”唱得越好,她就越向傳統文化的邊緣游走。《夜宴》中流放吳越之地的太子無鸞所帶來的越人歌,舞者們蒼白的衣服和面具,怪異扭動的肢體,清亮的歌聲婉轉幽怨,透著徹骨的寂寞,相對于代表宮廷莊嚴的黃鐘大呂、輕歌曼舞,它只是山水間的一縷幽情。現代電影中,多以搖滾樂作為子輩邊緣身份的標志化象征。搖滾樂以破裂的音節、夸張的肢體語言釋放、強化著意識中最原始的渴望掙脫、獲取自由的情感。《北京雜種》《昨天》《長大成人》中都出現了相同的角色,他們留著長發,穿著破牛仔褲,聲嘶力竭地向陳舊的條條框框宣戰,揭露工業社會華麗外衣下的滿目瘡痍。他們越是離經叛道,就越被社會所排擠,現實生活的庸俗、骯臟,與理想的純粹形成強烈的反差,讓他們的生活更加極端,吸毒、暴力、濫交成為暫時逃離壓力的麻醉品。
三、叛逃后的人物組合
逃離父權中心的主人公往往融合進社會中的某個性格群體中,其中存在形形色色的人。以群體式的生存模式,來加強個體的信心和力量,營造歸屬感。在這種群體中,人物性格一般分為以下三種類型:沖突型、對比型、映襯型。在作為精神豐碑的父親形象失去光彩之后,子輩以脫離父輩控制管束的形式,進入了社會。這些弱小的單體,自然而然地結合成小群體,依賴群體意志來增強自信。
沖突型人物與主人公觀念不同,實際行動發生碰撞和沖突,成為在社會中碰到的阻礙力量,常作為某種社會權力出現,對主人公的生活構成緊逼和壓迫,成為一種社會化的父權。《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劉憶苦是小團體中的權力中心,他可以決定這個團體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并對馬小軍的青春性幻想構成阻礙。《小武》《任逍遙》中都出現了這樣的形象,暴富的人用金錢和暴力壓迫這些邊緣青年,使得他們的生活更加不幸。《小武》中以一個意味深長的鏡頭來描述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寬寬的街道上,一面是林立的嶄新樓房,另一面是低矮破舊的平房。一部分人的富裕生活是建立在對這些底層青年的壓榨和盤剝上,卻以掠奪來的財富侮辱、排擠他們。
對比型人物與主人公觀念不同,實際行動卻不相沖突,平行發展。與主人公的生活軌跡形成叛逃與回歸的鮮明對比。《麻將》中的紅魚與倫倫就形成了這樣的對比,紅魚拋棄良心和道德瘋狂斂財,最后憤而弒父,成了殺人犯-倫倫則艱難地固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即使被社會譏笑,被小團體拋棄也在所不惜,最后他收獲了愛情。對“原鄉”文化的態度導致同一團體中兩人的分歧,走上不同的道路,演繹不同的命運。這種強有力的對比,讓紅魚結尾對于“原鄉”文化的呼喚顯得真實可信,富有感染力。
映襯型人物與主人公觀念相同,作為群體相互映襯,通過類似人物聚合成群體性形象,將個體的“弒父”行為拓展為一代人集體的“弒父”行為。將個體生命體驗置換成群體生命體驗,形成一代人的社會遭遇,他們有共同的渴望、沿著逃脫家庭的路走向共同的命運。在這其中存在著一個意味深重的符號性映襯者,《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騎著棍子的傻子,他是一個不存在自我意識的個體,他所呈現的完全是社會的父權意志留下的時代烙印,他的成長與馬小軍們的成長保持著一致的步調。在神化政治父權的時代,小軍們與傻子的交流是革命話語的暗號:“古倫木”和“歐巴”。當精神偶像幻滅后,長大成人的孩子們共聚一堂再試圖以革命話語與傻子交流時。這種交流中斷了,遭到了傻子的拒絕,傻子換了一句時髦的京罵,主流意志的改變導致社會話語體系的改變,傻子和他們一樣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