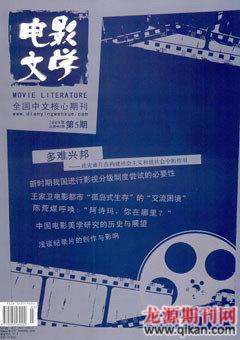一杯濃郁的文化佳釀
姜玉梅
電影《梅蘭芳》,無論劇情還是人物,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本文試從故事情節(jié)和梅蘭芳等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談?wù)勎业挠^感。
《梅蘭芳》的片頭字幕顯現(xiàn)的那一刻,落寞的鑼鼓聲在字后鳴響,一代京劇藝術(shù)大師的藝術(shù)人生就以藝術(shù)的方式徐徐展開,霎時(shí)間令人感覺昨日重現(xiàn)。
劇情截取了梅蘭芳生活中三個(gè)主要的橫截面,比較典型而豐富,這是電影《梅蘭芳》選材的優(yōu)勝之處。三個(gè)情節(jié)核心分別是:京劇藝術(shù)上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個(gè)人感情生活、蓄須明志對(duì)日拒演。三個(gè)情節(jié)既互相獨(dú)立又互相聯(lián)系,從不同側(cè)面塑造了一位立體的豐滿的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梅蘭芳。
梅蘭芳之所以為梅蘭芳,首先是他藝術(shù)上的不俗追求和成就。他的成就不在于它能將京劇承繼,而是他的大膽創(chuàng)新和變革,從而使得他自成一格,出神入化,美輪美奐,創(chuàng)立梅派,從而成為四大名旦之一。劇情伊始,就再現(xiàn)了他和京劇大腕十三燕——他的“爺爺”(一個(gè)文戲武戲都能演,造詣?lì)H深的梅蘭芳的長輩)之間新舊觀念之間的沖突與較量。首先在邱如白的點(diǎn)化下,梅蘭芳決意在舞臺(tái)動(dòng)作表演上改動(dòng)一些細(xì)節(jié)。因?yàn)閭鹘y(tǒng)的京劇有些拘謹(jǐn)、僵化、不自然,有很多表演細(xì)節(jié)已成定勢,不足以表現(xiàn)人物的真性情。但藝術(shù)上尚不成熟的青年梅蘭芳要改革,首先最大的阻力就是當(dāng)紅名角十三燕,梅雖開誠布公,與之切磋溝通,終遭拒絕。最后迫不得已,毅然決定與十三燕唱對(duì)臺(tái)戲,打擂臺(tái)以定輸贏。最具創(chuàng)新眼光的邱如白向梅蘭芳預(yù)言“你的時(shí)代到來了”。就這樣,青年梅蘭芳戰(zhàn)勝內(nèi)心的掙扎與矛盾,頂住可能慘遭失敗的巨大壓力,一老一少,一舊一新,展開殘酷的競爭。這一過程,再現(xiàn)了梅蘭芳對(duì)待藝術(shù)的真誠果敢和創(chuàng)新追求,柔中帶剛,雖無咄咄逼人之氣卻也銳不可當(dāng)。當(dāng)然,以前是合作者,現(xiàn)在要登臺(tái)打擂,事關(guān)個(gè)人名氣毀譽(yù)事業(yè)成敗,兩人內(nèi)心的矛盾和掙扎,表演得淋漓盡致。最終,代表傳統(tǒng)的十三燕在新銳前敗北,劇場空無一人,但這位久經(jīng)世事滄桑,對(duì)京劇對(duì)藝術(shù)愛恨交加的老藝術(shù)家,依然固執(zhí)而忘我地帶隊(duì)表演,直至曲終。此場戲尤為顯得蒼涼悲壯,其雖敗猶榮,震撼人心,讓觀眾既為之惋惜又不得不嘆服欽佩。此時(shí)的梅蘭芳雖取得大滿貫,但未卸裝就跑過去探望十三燕,一老一少,終于前嫌盡釋,進(jìn)行了感人至深推心置腹的交流,凸現(xiàn)了青年梅蘭芳柔美善良的人性光輝。
黎明扮演的梅蘭芳,氣質(zhì)儒雅風(fēng)流倜儻柔中帶剛,其扮相舉止,所演繹的京戲人物的喜怒哀樂,都顯得不溫不火恰到好處,既不呆板僵化沉悶,又不扭捏過火裝腔作勢,自然舒服,頗具梅蘭芳的神韻,應(yīng)該說是比較神似的。
在藝術(shù)上的追求造詣和貢獻(xiàn),雖是梅先生一生的主要亮點(diǎn),但劇情僅止于此,便不足以表現(xiàn)豐滿的有血性真性情的梅蘭芳。劇情的第二節(jié),表現(xiàn)的是梅先生的感情生活。
首先,是他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妻子福芝芳。但福與眾不同,結(jié)婚時(shí)就聲明“我是管你來了”,果不其然,他成了梅先生的賢內(nèi)助,操持家務(wù),打理演藝事業(yè)上的瑣事,處理人情往來,通情達(dá)理,賢惠能干,又深明大義。在梅蘭芳是否去美國演出這件事上,雖也有猶豫,但能以梅事業(yè)發(fā)展為重,不惜拿房子作抵押,很有長遠(yuǎn)眼光和非凡氣度。對(duì)待梅的紅顏知己,雖也有普通女人的無奈傷懷,但卻能以理性戰(zhàn)勝情感和妒忌,到孟小冬寓所開誠布公,坦陳利害,她懇求孟離開梅蘭芳時(shí),一番說辭尤為感人:“梅蘭芳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他是座兒的。”見解獨(dú)到非凡,超越了個(gè)人感情的恩怨得失,在她心目中,梅蘭芳甚至不僅僅屬于她,而是屬于京劇藝術(shù),屬于熱愛他的大眾,為了梅蘭芳,為了他的清譽(yù),為了他的清靜和孤單(邱如白在這一點(diǎn)上,見解更為深邃深刻),她懇請(qǐng)情敵離開梅蘭芳,凸現(xiàn)她的無私和博大。夫妻感情有過波折,但最終復(fù)歸于平靜,尤其日寇入侵,生活動(dòng)蕩不安時(shí),夫妻二人的感情更顯篤定。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溫馨幸福,融會(huì)在生活的細(xì)水長流中。
但不可回避的是,梅蘭芳曾與孟小冬的精神戀愛。梅孟一見如故,正如邱如白對(duì)孟所言:“梅蘭芳在這之前,一直是孤單的,直到遇見你。”一個(gè)是旦角之王,一個(gè)是坤角之后,臺(tái)上游龍戲鳳,臺(tái)下你情我意,志趣相投,是典型的知己之交。一個(gè)熱情奔放,敢愛敢恨,一個(gè)文雅含蓄,一往情深。雖相愛已深,但也僅限于一些不能公開的交往:雨中孟為梅撐傘,梅借還傘想多接觸對(duì)方,梅送紙飛機(jī)給孟為禮物,兩人各自許愿,梅的愿望也只是想和孟小冬看一場電影。劇本截取這些溫婉多情而不做作的生活細(xì)節(jié),溫婉地再現(xiàn)了兩人的激情難抑卻含蓄節(jié)制的愛情,讓人又憐又惜,也只能生發(fā)無限感慨和無奈了。最終,孟小冬在福芝芳和邱如白一再的勸說下,忍痛離開了梅蘭芳。這一節(jié)快結(jié)束時(shí),梅在自己家中,惆悵無語地喝著福芝芳每天為他熬制的保護(hù)嗓子的潤喉湯,一勺一勺地喝著,眼淚就大顆大顆地落下來。福芝芳在一旁不忍看下去,過來溫語相勸,“你別哭呀”,結(jié)果,勸人的人自己就不能自己地嘩嘩眼淚沖瀉而出,這一幕情景,演員演得真切到位,觀眾也看得眼淚滂沱。孟小冬與梅蘭芳的婚外情,愈發(fā)彰顯了一個(gè)有血有肉至情真性的梅蘭芳。因?yàn)椋水吘故歉星榈膭?dòng)物。而藝術(shù)家尤其是感情的動(dòng)物,自古以來,概莫能外。這一筆,增強(qiáng)了電影的觀賞性,也豐富了梅的藝術(shù)形象,尤為真實(shí)感人,給觀眾留下深刻的余味。
最后一節(jié),表現(xiàn)的是梅蘭芳的民族氣節(jié)。1937年,日軍侵入中國。在北平的梅避住上海租界,并立志不再登臺(tái)演出。但日軍想借梅蘭芳的聲望造勢,“欲征服支那人,首先得征服梅蘭芳”,逼迫他登臺(tái)演出,結(jié)果遭到嚴(yán)詞拒絕。后來又誤導(dǎo)民眾,在報(bào)上假說梅蘭芳的復(fù)出和日軍侵華戰(zhàn)爭的日期有某種聯(lián)系,偽造事實(shí),結(jié)果輿論一片嘩然,梅蘭芳一時(shí)百口莫辯。日方逼迫梅參加日方主辦的記者招待會(huì)。為了消極抵抗,梅請(qǐng)醫(yī)生為他注射了傷寒針,寧愿讓自己發(fā)燒甚至可能冒著生命危險(xiǎn),也不能讓日本人的陰謀得逞。他滿面憔悴出席招待會(huì),并現(xiàn)場含蓄表明自己的立場。蓄須明志成為梅先生愛國的標(biāo)志,這一幕,再現(xiàn)了梅性格中深明民族大義堅(jiān)貞不屈的民族氣節(jié)。一代京劇名旦,終因戰(zhàn)亂謝幕多年,告別心愛的舞臺(tái),是何等的無奈、何等的壓抑,但為了民族氣節(jié),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又是何等的仁義剛烈,何等的錚錚鐵骨。戲臺(tái)上的文弱和性格中的剛烈形成鮮明對(duì)比,將一個(gè)愛國的梅蘭芳呈現(xiàn)出來。劇情至此,才完成了對(duì)梅蘭芳這位藝術(shù)大師的完整形象和性格的塑造。
與對(duì)日不合作拒演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電影的結(jié)尾,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沉寂多年的梅蘭芳復(fù)出,劇場人山人海,梅被觀眾擁戴追捧。但此時(shí)的梅蘭芳并不過度興奮,有一種歷經(jīng)藝海沉浮滄桑巨變的淡定平和,好像他早預(yù)料到會(huì)有這么一天,好像他為觀眾演出是天經(jīng)地義再自然不過的事,他神態(tài)莊嚴(yán)態(tài)度優(yōu)雅和婉、氣定神閑地對(duì)圍堵的記者和觀眾說:“你們別跟著我了,我這就要扮戲了。”淡淡的一句話一出,又回蕩起悠揚(yáng)高亢的京劇唱腔,整部劇情戛然而止,留給觀眾無限的回味無盡的感慨——梅蘭芳。是為藝術(shù)而生的,是屬于祖國和觀眾的,而惟有藝術(shù)才能使梅蘭芳煥發(fā)生命的真正活力。
除了主要人物梅蘭芳之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演員王學(xué)圻扮演的十三燕,孫紅雷扮演的邱如白,陳紅扮演的福芝芳。這三位人物被塑造得個(gè)性鮮明、跳脫生動(dòng)、血肉豐滿。
《梅蘭芳》拍的是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大半生,也再現(xiàn)了那個(gè)風(fēng)云亂世里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無論從劇情的編排,還是演員的表演,都可稱得上是一部充滿了藝術(shù)靈感的創(chuàng)作,整部電影端莊典雅、厚重感人,意蘊(yùn)綿長。
略顯不足的地方是,三個(gè)故事片段所占時(shí)間比較均勻。精彩之處大多集中在前半段,后半段則略顯乏力。它只講述了一代大師前半生的故事,結(jié)局在1945年戛然而止,亦讓人意猶未盡。筆者認(rèn)為,主角梅蘭芳藝術(shù)追求之路的艱辛坎坷,其堅(jiān)持民族大義、罷歌罷演后的苦悶和遭遇,這兩處也許可以做更多開掘。
電影反映的時(shí)代的跨度和深度,遠(yuǎn)遠(yuǎn)不及《霸王別姬》,這一點(diǎn)是陳凱歌自己也承認(rèn)的。但作為傳記片,是在生活真實(shí)基礎(chǔ)上的“藝術(shù)真實(shí)”,即便大動(dòng)筆墨,也注定不會(huì)有超越事實(shí)本原的過于激烈的戲劇沖突和天馬行空的悲情,否則,會(huì)給觀眾虛構(gòu)虛幻感,反而會(huì)削減它真實(shí)感人的藝術(sh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