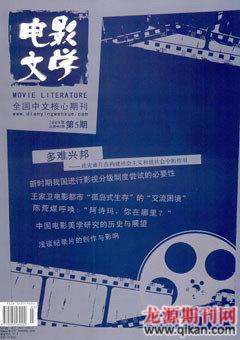女性生命本體欲望的消解與反消解
王 鵬
摘要《白鹿原》無疑是陳忠實在20世紀90年代給中國當代文學界注入的一針強心劑,作為一部民族心靈秘史,他在《白鹿原》中以厚重的筆墨著力刻畫了三類風格各異、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白嘉軒之母是男權主義與宗法制度“幫兇”的代表,田小娥則是白鹿原上盛開的一朵“惡之花”,以她為核心的性放縱,極富人性色彩與女性覺醒意識;鹿兆鵬之妻則是宗法制度與封建社會合謀造成的另一種犧牲品,長久的性壓抑造成了她最后的瘋魔。
關鍵詞男權主義,宗法制度,性放縱,性壓抑,審父
陳忠實是陜西第二代作家群體中的領軍人物,《白鹿原》作為他惟一一部長篇小說,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長篇創作的重要收獲之一,是能夠反映那一時期小說藝術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的重要作品之一。《白鹿原》從1988年4月搭筆到1989年元月寫完,隨后又經過一次長達3年的修改,最終發表在《當代》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上。陳忠實以其深厚的生活和藝術功底建構了一個蘊涵豐富、容量巨大、藝術震撼力強勁的獨特世界,出版之后,好評如潮,并于1997年以修訂版的形式獲得了第四屆茅盾文學獎,成為繼路遙之后,第二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陜西作家。作為一部民族秘史,陳忠實的創作具有極深的歷史意識與文學深度,作為一部極具文化意識與文化品格的巨著,陳忠實無疑做出了巨大的探索。在《白鹿原》長達近50萬字的文本寫作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女性形象的書寫與塑造,白嘉軒之母、田小娥、鹿兆鵬之妻等等豐富而立體的女性形象刻畫,無疑為中國當代文學畫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男權主義與宗法制度的“幫兇”——白嘉軒之母
白嘉軒之母是自家無法替代的精神領袖,她的作用更多地是為了敦促白嘉軒,不要忘記傳宗接代、為白家延續香火的重要使命。而白嘉軒作為一個傳奇,他的滿口仁義道德卻阻擋不住他男權主義思維的急速發展,全書開篇的第一句話:“白嘉軒后來引以為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就預示著男權社會對女性的一種強烈的征服欲。白嘉軒富有傳奇的一生也從這里開始,在小說的第一章,作者極盡能事地用白描手法,寫出了白嘉軒與前六個女人由生到死的結合。白嘉軒一次次的征服欲的釋放只是為了傳宗接代,只是為了維護一個家族的血脈傳承,“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在他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在一次次的無果的短暫婚姻后,他的一次又一次地續娶,更多的只是為了擺脫別人對自己“有毒鉤”的無稽猜測所做出的努力。白嘉軒的第五房女人——木匠衛老三家的三姑娘是一位不幸的男權主義的犧牲品,父權制度下的她被父親不顧死活地賣給了白嘉軒填房,在夫權制度的淫威下,在白嘉軒欲望得不到應有滿足與靈魂自尊受到極度傷害后,在近乎癲狂的性沖動下,最終在不到半年的歲月中,瘋癲般地溺死于澇池中,草草地結束了自己苦難的一生,父權的淫威逼迫著她無法選擇自己一生的婚姻,夫權的淫威迫使她早早因為膨脹的性欲而早早丟掉了性命,男權社會對于女性的壓迫與毒害成為赤裸裸的暴力行為制造著一場場不幸,制造著一個個無法形容的血腥的事實。然而,面對女性如此巨大的不幸,男權社會的男人們尚且表現出了一絲的憐憫與不安,而同樣作為從壓迫與剝削中走來的婦女來說,卻甘愿充當男權社會的幫兇,白嘉軒之母就是典型代表,她的一席話更是體現出男權主義對于女性生命的無盡忽視。她說:“甭擺出那個陰陽喪氣的架勢!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死了五個我準備給你再娶五個。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占去心甘。”在這里,女人的生命僅僅是充當生殖的一種工具,是被男權完全禁錮的工具而無自身存在的價值,如同草芥的生命在男權主義的壓迫下,女性本能欲望遭到了殘酷的剝奪,這就是白嘉軒所標榜的“仁義”。
二、白鹿原上盛開的“惡之花”——田小娥
田小娥,作為白鹿原上的一朵“悶暗環境中綻放的人性花朵”,成為《白鹿原》中最富人性魅力,最富女性獨立意識,最具反抗精神的“白鹿原上最淫蕩的一個女人”,同時,也是白鹿原上最為不幸,命運最為悲慘的女性形象。
《白鹿原》中的性描寫主要也是圍繞著她來敘述與書寫的。在“田小娥身上,宗法封建體制之下以男權為中心的性奴役、性剝奪、性歧視,都發展到非常野蠻、非常殘忍的程度。”
田小娥的命運是悲慘而讓人同情的。作為郭舉人的二姨太,田小娥不僅要受到大女人日夜的監督,而且還是郭舉人發泄性欲的工具,郭舉人在田小娥下體里泡棗的事實,完全將一個受侮辱、受壓迫的婦女形象無疑地表露了出來。但是,田小娥之所以是白鹿原上盛開的“惡之花”,還在于她強烈的反抗精神,她將每天泡在下體的三顆棗,扔入尿桶中,用尿這一“排泄物”來反抗郭舉人對自己身體與心靈上的奴役。田小娥與黑娃的結合,是長久得不到性滿足的花季女子對性可求的結果,同時也是田小娥走向對宗法制度下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有力抗爭,田小娥與黑娃的結合是愛欲的本能流動,無比的幸福與滿足成為田小娥與黑娃愛情的見證加以詮釋。然而,田小娥與黑娃的愛情是短暫的,不被白鹿村族權所肯定的“非法”婚姻注定是不能被傳統道德所許可的,艱難的生活與命運的執著,使得田小娥逐步淪為了鹿子霖釋放性欲的工具,鹿予霖乘人之危的發泄暴露了他本來可憎的面目,簡單的性出軌揭示了他本人無法彌合的缺陷,生理的滿足帶來的是心靈上的缺失,一個與白嘉軒相對立的角色在遮掩的道德外衣下被揭批得體無完膚。不僅如此,田小娥還成為鹿子霖與白嘉軒權力斗爭的犧牲品,以身體的誘惑加速了白孝文的淪落。然而,田小娥的本性是善良的,她為自己對白孝文的一舉一動感到難以平靜,面對白孝文的性困惑,面對白孝文的淪落,在一次次與白孝文的性交合中,她的內心是極度內疚的,是有負罪感的,是無法平靜的。她為了喚起白孝文的性欲望,在一次次地交媾中終于完成了對白孝文性欲的恢復。而尿在鹿子霖頭上成為田小娥不愿淪為他的工具與玩物的反抗。田小娥用性的放縱與自己身體式的反叛,反叛著宗法制度的不公,最終的慘死鹿三梭鏢鋼刀之下與死后變成惡鬼所引發的一場瘟疫。都成為命運被捉弄婦女對男權社會、對族權制度、對宗法制度、對封建禮教發起的一場總攻。然而,田小娥一個弱女子的反抗畢竟是有限的,在朱先生與白嘉軒的共同合謀中,田小娥的尸骨被從窯里挖出,架起硬柴燒了三天三夜,燒成灰末兒后被裝在瓷缸里封嚴封死,埋在窯里并在上面建塔,永世不得翻身。如此的合謀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與鄉約族權的偽善,“萬惡淫為首”的傳統觀念與“女人是禍水”的傳統女性觀是衛道士們壓制女性的罪惡根源。但是,田小娥身上原始的生命沖動與勃勃生機,對性愛追求與滿足的渴望,所散發出的野性、瘋狂與魔性則代表著男權社會巫女和魔鬼的典型,她們的妖冶、魅惑、風流與性感誘發了男性征服的欲望,以便在她們身上發泄其被壓抑的精神和性的苦悶,而她們行為中那種不計后果的沖動與
瘋狂又對男權社會的秩序與倫理構成了一種破壞性的力量,身體的叛逆成為女性覺醒的武器,將直接的和赤裸裸的身體自由地呈現在現實生活中,排除一切理性和語言的干預和支配,排除一切由理性和語言所制定的社會道德文化規范,無盡的肉體狂歡打破著宗法制度的一切禁忌。還原人作為社會主體的本來面目。
仁義,保守,墨守成規,宗族倫理成為陜西關中地區人的普遍文化心態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關中人。關中倫理觀念的核心是“仁義”,在關中農村的鄉約族規家法民俗之中,仁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重義輕利為核心的為人處世準則,二是以注重孝悌為核心的家庭道德,三是以貞潔婦道為核心的女性觀念。正是因為如此,在《白鹿原》中,白嘉軒固守著“仁義”二字,在父慈子孝的觀念和宗旨下,對一切忽視“仁義”與“孝悌”的子孫無情地進行了鞭撻,而對婦女貞節的重視,造成了對婦女本身人性意識上的戕害與摧殘,以“仁義”的觀念扼殺著女性欲望本身的覺醒,田小娥的性放縱,既是白嘉軒所要扼殺的也是白嘉軒們害怕看到的。
三、帶著精神鐐銬的狂舞者——鹿兆鵬之妻
鹿兆鵬,是一個敢于沖破封建傳統的包辦婚姻制度的革命先行者,他與白靈之間靈與肉的完美結合,雖然不甚完美但也極具現代意識。鹿兆鵬是白靈幸福的給予者,在與弟弟鹿兆海的情感博弈中,他以自己堅定的革命立場與現代的愛情觀念,在革命任務的掩護下,成就了這樣一段與白靈的生死相戀。同時,他也是另一個女性瘋魔的罪惡根源。冷先生的女兒,在包辦婚姻的不自主中走進了鹿兆鵬的家,“她不知道鹿兆鵝和她完婚是阿公三記耳光抽扇的結果”,“他和她新婚之夜僅有的一回那種事,并沒有留下歡樂,也沒有留下痛苦,他剛進入她的身體就發瘧疾似的顫抖起來,嚇了她一跳,以為他有羊癲風,甚至覺得很好笑。”婚后一直獨守空房的她,長期忍受著生理與精神折磨的痛苦,性愛的白日夢與婚內的絕欲,一步步地將一個年輕的女性,逼入了瘋魔的深淵。她的精神枷鎖是深重的,無法滿足的生命欲求越是壓抑卻愈是強烈,婚內的絕欲除了生理上的擾亂與不適感外,在心理方面,對性沖動既不能不驅遣,而又驅遣不去。結果是一個不斷往復的掙扎與焦慮,而越是驅遣不成,神經上性的意象越是紛然雜陳,那種不健全的性感過敏狀態越是來得發展。鹿兆鵬之妻的失眠、顫抖、焦灼的渴望與意念中的亂倫,成為她瘋魔前的表征。女性在男權社會沒有掙到做人的資格,常常是愈做奴隸而不得,奴隸的命運讓長久壓抑的性欲得不到必要的滿足,鹿兆鵬之妻的死就是對這個在宗法制度的理念包圍下的社會對人本性摧殘的最好寫照。
宗法制度、族權、鄉約的合謀,制造著白鹿原上一個個悲劇,一個個血腥的事實,對性欲的干預與人生命意志的戕害,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封建傳統道德觀念的虛偽性與卑下性,對宗法制度的殘忍性表露無遺。
四、結語
男權社會中的男人們在制造了一整套貞潔婦道的女性觀念禁錮扭曲女性的同時,也禁錮扭曲著他們自己。鹿三對于田小娥的刺殺行為實際上就是被禁錮扭曲的男性向女性肉體施暴的一種變異形式。而鎮壓田小娥的靈魂,則是在道統武裝下虛弱無力的男性向充滿張力的女性靈魂所作的一次徒勞無益的掙扎,在德里達“陽具邏輯中心主義”的論述中,曾經指出:女性身體永遠都是男性身體,特別是男性生殖器(即陽具,原文phallus)的客體和性欲發泄對象。在文本中,白嘉軒三子白孝義的不育,卻造就了男權主義婦女貞節觀念上的又一場重大“突破”,不論是渴求在棒槌神會日讓孝義之妻借種,還是最終借兔娃之種以達到生殖與傳宗接代的目的。這樣的一次“借種”,作為一次男權主義賦予女性的合法的失貞行為,更多的體現為一種“無奈”,一種無法抗爭的“無奈”。以貞潔婦道為核心的女性傳統觀念中的實用功利性與虛偽性,以貞潔婦道為核心的性觀念在《白鹿原》中的解說,也從更深的層面,說明了它殺人和虛偽的另一面本質。
而田小娥與白嘉軒、鹿三之間的巨大沖突,同時也是一種廣義上的父子對立,其間隱含著陳忠實“自我”與“超越”的兩種文化人格心理,這種沖突顯然表現出陳忠實對現實和歷史清醒的獨立理性批判精神,它是創作主體的獨立自我人格和現代自由意志的藝術傳達。“審父”,作為田小娥的抗爭,從道德倫理中的巨大反叛中也表現出對父權的公然挑戰與蔑視,鹿兆鵬之妻瘋魔前的對鹿子霖道貌岸然的“公然”對抗,正是“審父”主題的巨大推衍,一個對父權制度的顛覆性舉動成全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對于陳忠實而言,“審父”是人性的另一種審判,他的“超我”和“自我”的人格擁有著強大的心理能量,換言之,由于他的傳統道德意識和現代啟蒙意識使得他的“本我”人格能夠借助其道德人格和啟蒙人格的心理對抗而獲得一種“合理”又“合情”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