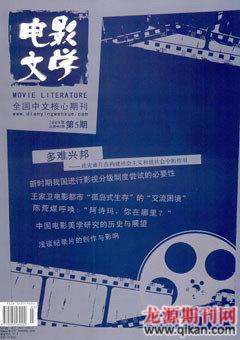《色戒》緣起
陳 宇
摘要電影《色戒》的出現,使得張愛玲的小說重回大眾視野。小說吸引了大批學者的探討,不乏有誤讀和曲解之處。文章從文學即是入學的角度,切入分析張胡之戀、作家的童年體驗對張愛玲創作的影響,從而探索張愛玲的生命歷程與《色戒》緣起之關系。這將有助于理解張愛玲豐富的情感世界以及紙上的灰色人物,也有助于重新品讀作品《色戒》的內涵。
關鍵詞《色戒》,張愛玲,創作,張胡之戀,缺式性童年體驗
一、張胡之戀對張愛玲創作的影響
李安對《色戒》的翻拍,使得張愛玲的小說再度進入大眾的視野。小說創作于張愛玲的晚年,篇幅短小結構卻異常精致。精致中又處處埋藏著殺機與溫情的糾葛。更令人稱嘆的是張愛玲對情愛世界的解讀,對個人命運的理解。
《色戒》取材于20世紀30年代的真實事件即1939年的“丁默郵遇刺案”。愛國女學生設美人局暗殺日偽漢奸,結果卻為情所困愛上了漢奸反被殺。一些學者懷疑此文的政治立場是否有偏差。臺灣作家張系國批評張愛玲“歌頌漢奸的文學—即使是非常曖昧的歌頌——是絕對不值得寫的”。張愛玲寫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作為回應,指出其“穿鑿附會,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牽強的曲解”。張愛玲是甚少為自己辯護的人,可見其對此文的重視,對個人名譽的珍惜。
文學即是人學,作家在創作中往往融入自我的人生體驗和情感。張愛玲撰寫《色戒》更多的是對自身身世的悲嘆,也是張胡之戀的反思之作。1943年,張愛玲初出文壇,胡蘭成仰其才多次登門拜訪。對于剛出校門的張來說,他能讀懂她的心靈,是她生活中從未遇到過的知音,于是給胡回信“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并捧出自己真摯之心。而此時的胡蘭成已經有過兩次婚姻,且久經官場,他盼得到的未必是她的心,因而所予的也并非真心。正如他自己所言“她這送照片,好像吳季扎贈劍,依我自己的例來推測,那徐君亦不過是愛悅,卻未必有要的意思。張愛玲是知道我喜愛,你既喜愛,我說就給了你,我把相片給你,我亦是歡喜的。而我亦只端然地接受,沒有神魂顛倒。”兩人婚后不久汪偽政權垮臺,日本投降,胡開始逃亡生涯,委情于多名女子。這段婚姻維持三年終以離婚收場。她是個獨立的女子,所想要的只是愛。但是生活并沒有因為她的真純善待她。她曾經質問過胡:“你與我結婚時,婚帖上寫現世安穩,你不給我安穩?”張愛玲對于這段感情是耿耿于懷的。
《色戒》中王佳芝也是青年學生,沒有什么戀愛經驗,這與初識胡蘭成時的張愛玲相仿。王佳芝很天真,毫無人生經驗的學生卻要完成鋤奸大事,結果錯把情欲當愛情,因善良而送命。文中她將漢奸易先生引進珠寶店,在佯挑鉆戒時,她望著他,發現他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她被這神氣所打動,突然覺得真心愛他,一瞬間,她心里轟地一下,理性的樊籬被愛情沖破,低聲叫他“快走”,救了他的命。但是易先生同張愛玲筆下的其他男子一樣,懦弱陰柔到冷酷。脫險以后絲毫未憐惜王佳芝這個他愛過的人“馬上一個電話打去,把那一帶都封鎖起來,一網打盡,不到晚上十點鐘統統槍斃了”。易先生處理得冷靜干脆!小說結局,張愛玲對易先生的諷刺與鞭撻是相當有力的。
胡蘭成政治上的不忠必然致感情上的不實。他對張愛玲的背叛不僅是對她生命力的扼殺,也間接導致了其創作的凋敝。1946年張愛玲遭遇了情變也遭受“文化漢奸”之攻擊。至此在文壇沉默了俾。1950年恢復創作,但文章已不如從前之輕靈、灑脫、飛揚。正如與此情決裂時,她對胡蘭成說的話“我將只是萎謝了”。《色戒》全文一萬多字,卻寫了30年,可見蘊蓄其中情感的復雜。親情、友情、愛情在張愛玲看來是近乎無情的,又要在這些無情底下尋找一抹溫情,這種掙扎與抗爭讓人動容。
二、缺失性童年經驗對張愛玲創作的影響
《色戒》中的易先生長著花尖鼻顯得有點鼠相,人影映在大人國的鳳尾草窗簾上顯得極矮小,外貌之不偉已顯示其性情之卑瑣。《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佟振保、《年青的時候》的潘汝良,他們在作者筆下也是些陰柔怯弱的凡人。為什么陳列在張愛玲的創作畫廊里的都是些灰色的沒有生命活力的人物?這與作者的童年經歷有關。
沿著《色戒》我們也可以摸索到童年對張愛玲創作的影響。如果說《色戒》中陰冷的易先生是胡蘭成的投射,那么張愛玲早期作品大都是對童年往事的追憶以及大家族衰落的書寫。《琉璃瓦》中把子女當搖錢樹的姚先生,《花凋》里舍不得為女兒花錢治病的鄭先生,都折射出張愛玲父親的影子。
張愛玲出生于顯赫的家族。祖母李菊耦是晚清名臣李鴻章的親生女兒。祖父張佩綸是晚清“清流黨”的代表人物。張佩綸宦途坎坷,晚年抑居南京,抑郁終老。死而不歸祖塋,凄涼的身世為這個顯赫的家族抹下了蒼涼的底色。其母系一族也是晚清大族。張家的后人很難走出祖輩的巨大光環。在張愛玲出生的1920年,滿清王朝已經滅亡10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滌蕩全國。而新的思想并沒有影響這個名門世家,其內部儼然還是個小封建帝國。他們是被新時代拋棄的遺老遺少,坐擁著已不再的時光。《花凋》里的遺少鄭先生,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是個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尸。《茉莉香片》里的父親和繼母,一個汗衫外面罩著一件油漬斑斑的軟緞小背心,一個蓬著頭,一身黑,面對面地躺在煙鋪上抽鴉片。滿屋子煙氣騰騰的。這些都是作家對沒落家族的摹寫。
8歲的時候父母離婚,童年因而碎裂。父親張廷重是典型的遣少,吃喝嫖賭,抽鴉片,娶姨太太。對家庭子女也毫無責任心,張愛玲在《花凋》中諷刺過“等爹有錢……非得有很多錢,多得滿了出來才肯花在女兒的學費上——女兒的大學文憑原是最最狂妄的奢侈品”。在張父看來女兒的出路是嫁人而不是獲得自己的幸福,《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多少恨》中的虞老頭便是其父的折射。受姨太太的挑唆,張廷重甚至打罵囚禁張愛玲,“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這座房屋忽然變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現出青白的粉墻,片面的,癲狂的。”屋外是滬戰,屋內是冷漠的親情。張愛玲17歲時逃離父親的家。從此再無往來,有關父親的記憶便停留在青少年時代。
母親黃逸梵在張愛玲4歲時便遠避海外,4年后與張父離婚。母親是情感的庇護與慰藉之處,但是張愛玲的眼淚卻只能留給自己看。在《傾城之戀》中,白流蘇在家中遭排擠,向母親求助:“‘媽,媽,你老人家給我做主!她母親呆著臉,笑嘻嘻的不做聲。”這種感覺好似“在傾盆大雨中和家里人擠散了。她獨自站在人行道上,瞪著眼看人,人也瞪著眼看她,隔著雨淋淋的車窗,隔著一層層無形的玻璃軒罩無數的陌生人”。孤立無援之感源于童年時期母愛的缺失。母親的缺席對她來說是一生的遺憾。
張愛玲的童年是缺失的。童慶炳界定缺失性童年經驗為“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質匱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殘、壓抑、生活極端抑郁、沉重。”他認為豐富性童年經驗和缺失性童年經驗雖然都已成為創作動力的“動力源”,但后者比前者在激發創作動機的內在心理驅動力上更為強烈。
《色戒》中王佳芝的個人身世,作家交代不明,但李安在翻拍中還原了人物來源。電影中,王佳芝父母離異,父親再婚,母親遠在海外,這為王佳芝陷入不倫的情網之中作了很好的鋪墊。而李安的還原正來源于張愛玲的個人經歷。
戰爭,家族沒落,家的崩潰。年少時期便經歷人情的冷暖,十六七歲便感到“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1942年,由于經濟的窘迫,張愛玲輟學圣約翰大學。寫作成了靈魂的出口,也成為謀生的方式。在她身后的文字世界,除了《私語》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有關個人遭遇的敘述。因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天才女子,和多數中國人一樣“喜歡喧嘩吵鬧”,喜歡制造“傳奇”。如今,我們看到的張愛玲,熱鬧只是其表象,身世之坎坷令人哀嘆同情,而承擔不幸、反抗命運、追求幸福的勇氣又令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