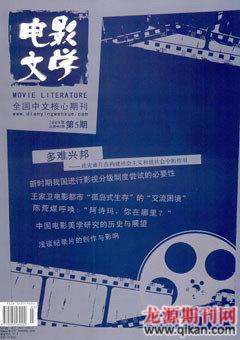當繆斯女神遭遇“人類紀”
張守海
摘要在金錢與科技構筑的強大現實面前,繆斯女神像失去了往日的風采和神韻,等待著消費者的垂青和眷顧。許多中外文藝理論家也宣揚起文藝終結的論調。“人類紀”是當代學者基于科學與人文的視闞融合提出的一個全新的地質年代命題,“人類紀”的人類正面臨著自然生態惡化和精神疾患蔓延的嚴峻挑戰,文學藝術應該發揮與自然和生命密切關聯的優勢,以悲憫情懷和詩性智慧為“人類紀”的良性發展提供精神支撐。
關鍵詞“人類紀”,生態危機,精神疾患,大悲憫,大智慧
古希臘神話傳說中有九位掌管文藝的繆斯女神,雖然無法確知是否真的有這樣的神靈,但是東西方的文藝理論確實都很重視文藝創作中的迷狂、靈感、神思、妙悟等問題,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文學藝術的敬畏之情。文藝伴隨著人類從荒蠻走向了文明,傳承著人類的詩性精神,促進著人類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它值得人類珍惜。但是隨著三百年前人類吹響了工業革命的號角,科技擁抱著資本走上了歷史舞臺的中心。在金錢與科技構筑的強大現實面前,繆斯女神像一只躲在角落里的丑小鴨,失去了往日的風采和神韻,等待著消費者的垂青和眷顧。與此同時,許多中外文藝理論家也開始宣揚起文藝終結的論調。繆斯的使命真的到此結束了嗎?今天,當我們把這一問題放在“人類紀”這個全新的理論背景下來探討時,我們發現未來的文學藝術既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
一、自然與人文的視閾融合——“人類紀”的提出
最早做出地球發展進入“人類紀”時期這一判斷的是兩位國外的科學家:一位是諾貝爾獎得主鮑爾·克魯岑,另一位是地圈與生物圈研究國際計劃(IGBP)領導人兼國際壘球變化中的人類因素計劃(IHDP)執行主任威爾-史蒂芬。他們在2004年提出“人類紀”這一概念,立即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注。在他們看來,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于自然環境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大自然本身的活動力量,人類單憑著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快速改變這個星球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特征。所以“人類紀”就不只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和寒武紀、侏羅紀一樣的地質學術語,它已經涵蓋了地球上不同國家、不同種族共同面對的經濟、政治、安全、教育、文化、信仰的全部問題。我國著名地質學家、環境學家中科院院士劉東生近年也在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上發表演講認為,“環境問題是全球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環境問題研究其本身就是環境演化的研究,而環境演化在研究未來的時候,更需要認識現在和過去。”在地球科學方面,“把現在或者說最近這一個時代也可以看作為環境問題的時代,作為一個單獨的有其特殊含義和內容的地質時代來研究,那就是人類世,它是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新的視角,也是從地球環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尋求自然科學走向和實踐的新的途徑。”
中外科學家從自然與人文相融合的視角提出人類紀(人類世)這一新的概念,其意義即在于展現一幅關于全球變化的最新理論圖景,讓我們從根本上重新審視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處境與責任,從而能夠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運,創造美好未來。如果我們清楚了當前“人類紀”里人類的處境怎樣,最需要做的是什么,我們就不難理解地球步入“人類紀”這一重大轉折對于有“人學”之稱的文藝而言意味著什么。“人類紀”是以人類命名的地球紀元,但是當前人類在“人類紀”的處境并不妙。由人類一手造成的生態危機正在地球生態系統的各個層面上不斷加重,外在的自然環境危機和內在的精神危機都給人類社會亮起了紅燈,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面臨著巨大的考驗。
二、生態危機與精神疾患——人類在“人類紀”的境遇
任何對人類的命運有責任感的人都不能不正視“人類紀”里我們所面臨的極其嚴峻的生態危機。從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態環境來看,不可再生資源的迅速枯竭、荒漠化和水資源的極度匱乏、全面的和難以凈化的環境污染,是我們所面臨的三重最為緊迫的危機。從全球角度來看,當前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最主要的有溫室氣體排放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平流層臭氧耗損,森林銳減與生物物種滅絕,土地荒漠化以及淡水資源短缺等五大問題。其中任何一項都對人類的前途有著致命的影響。有未來學家預言,從資源和環境角度看,今后50-75年之間,人類社會有以下幾種可能:一是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繼續人類在地球上的文明,二是高度發達的技術社會,以技術的重大進展為支撐,更有力地控制自然,三是未來的狩獵一采集社會,地球生態崩潰,幸存的人類回頭再作“自然中的人”。我們知道,人類歷史上由于不適當地作用于生態系統,造成環境破壞進而導致文明驟然衰落的慘痛教訓有很多。如兩河流域環境退化與蘇美爾文明的衰落,中北美洲低地叢林環境退化與瑪雅文明的消亡以及古絲綢之路沿線文明的消失等等。在古代,一個地方環境破壞了人們還可能遷居到另一處;而今天,人類已經遍布地球的各個角落,如果再繼續破壞地球的生態環境,那么人類將面臨的是全球性的生態崩潰和人類文明的徹底覆滅,許多好萊塢災難片中的可怕場景將成為現實!
與自然的生態危機同樣嚴重的是人類精神領域的危機。無論從中國還是從全世界來看。科技的進步和財富的增加都沒有給人類的心理帶來更多的幸福。相反,我們都不幸地處在一個精神疾患日益增多的時代。精神疾患不僅是一個重要的醫學問題,更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是社會發展誤入歧途的精神表征。社會迅速轉型、競爭壓力增加、社會正義缺失、環境污染加劇等,都會產生精神衛生問題。精神疾患對我國人民健康的危害已經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重,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最新流行病學統計顯示:中國“精神疾患時代”已悄然來臨。自80年代以來,我國重癥精神障礙患病率呈明顯上升趨勢,目前全國各種精神病人約1700萬人。兒童行為問題、酒精濫用、海洛因成癮、網絡成癮、自殺發生率均明顯上升;大、中學生以及老年人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持續攀升。精神疾病的救治難度非常大,精神疾患給家庭和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醫療負擔,更嚴重的是精神疾病患者中有十分之一已經危害社會,許多惡性案件的背后都有精神異常的影子。我國抑郁癥的患病率約為10%~15%,已與發達國家類似,預計今后還會逐年遞增。從疾病發展史來看,人類已經從“傳染病時代”、“軀體疾病時代”步入“精神疾病時代”。
尼采曾說:地球患了一種嚴重的皮膚病,病的名字就叫做人。今天站在“人類紀”的立場上,面對人類自身病弱的精神和由人類一手造成的嚴重生態危機,尼采的話更加讓人感慨和憂慮。但人類不會就這樣毀滅,哲學家、科學家、倫理學家、政治家及宗教界人士都在關注著人類所面臨的這一空前危機,探尋著擺脫困境的出路,文學藝術家當然也不甘心無所作為。
三、大悲憫與大智慧——文學藝術在“人類紀”的擔當
人類為了眼前的利益瘋狂地破壞自然、自毀家園、斷子孫路,沒有比這更愚蠢、更短視、更無情、更殘忍的
了。這樣下去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必然加劇,人的精神異化也必然越來越嚴重。要走出這個惡性循環,需要人類具有大悲憫的情懷與大智慧的境界,只有這樣才能承擔起拯救地球與人類未來的大責任,從根本上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困境。人類的文化觀念是造成生態問題的關鍵,而精神疾患本身既是精神領域里的問題。所以魯樞元認為:“解救地球的生態困境,就必須首先從人類自身的救治開始。于是修補精神圈的空洞和裂隙,矯正精神圈的偏執和扭曲,進而從根本上改善地球上的自然生態與精神生態,就成了人類紀的人們面臨的一項重大歷史使命。”須發揮文藝的作用,修補甚至是重構人類的精神世界,以此再造和諧健康的地球生態系統。面對生態惡化,文藝當然可以揭露生態惡化的事實,控訴污染者,宣傳環保知識等等,但筆者認為文藝最重要的作用還表現在它所蘊含的悲憫情懷和詩性智慧對人類主體精神的塑造上。
作家曹文軒認為,文學對人類的根本擔當就是“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而悲憫精神即是良好的人性基礎之一,“文學正是因為它具有悲憫精神,并把這一精神作為它一個基本的屬性之一,它才被我們稱之為文學的。也才能夠成為一種必要的,人類幾乎不能離開的意識形態。那么對于文學來講,這不是一個其他的什么問題,它就是一個藝術問題,悲憫情懷就是一個藝術問題”。文學藝術的悲憫情懷不應該只限定在人類內部,還必須擴展到天地間的一切生命。因為如果人類對其他生命始終是殘酷壓迫與殘害,那么最終也會把這種統治與壓迫的邏輯運用于人類社會內部,人類社會便永遠不可能獲得解放。具體到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上,悲憫情懷主要體現為一種生態良心和生態倫理。愛因斯坦就曾說過:“人類本是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卻是自己脫離了宇宙的一部分。我們今后的任務就在于擴大悲憫情懷,去擁抱自然萬物。”許多優秀的生態文藝作品和寓言故事都批判了人類對其他動物的殘暴貪婪和不仁不義,也揭示了人類如果繼續不負責任地荼毒生靈,必將自取滅亡的道理。對生命的關愛不但適于動物,也適于植物。徐剛在《伐木者,醒來!》中講過一個感人的故事:一個老人給砍樹的人60元錢買下一棵樹,抱著已經被砍傷的樹失聲痛哭。對生命的敬畏與悲憫并不是簡單的人類施恩于自然,因為悲天與憫人是一體的。當河流污染、草木凋零、鳥獸消亡、垃圾圍城、空氣污濁之時,人的家園也就不復存在了,人的尊嚴、人的高貴又到哪里去找呢?
文學藝術除了能以悲憫的情懷感化人心溫暖人心,更能以詩性智慧啟迪人心鼓舞人心。詩性智慧從根本上來講也是一種生態智慧,它是源于自然天性的智慧,是人與自然、肉體與靈魂,感性與理性和諧的智慧。現代科技教給人們的是功利的知識技能,以“造福”人類的名義去操縱控制自然,結果卻在欲望的驅使下利令智昏,制造災禍。湯因比感嘆人類已經“進入了精神王國”,是大地母親的最強有力和最不可思議的孩子,同時他也意味深長地指出:“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欲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何去何從,這就是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斯芬克斯之謎。”技術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結盟導致人們狂妄自大、貪得無厭,忘記生命的常識,忘記人是自然之子。我們需要的是回歸質樸的生活,放棄對自然的征服和掠奪,只有這樣才能揭開人類面臨的這個斯芬克斯之謎。這也正是生態文藝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日本導演黑澤明的影片《夢》就傳達了只有順應自然、返璞歸真才是人類正道的深刻哲理。
四、結語
我們認為文學藝術作品應該具備大智慧與大悲憫的境界,也讓人學會愛與悲憫,懂得責任與擔當。好的藝術一定會教導人們更好地與自然相處,而藝術創造與欣賞活動本身就是一種“低物質消耗、高精神層次”的綠色生活方式,它可以救治現代人過分功利化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我們呼喚文學藝術能夠超越這個時代的功利主義精神背景,給人類提供大悲憫與大智慧的精神滋養。有了愛的能力、有了責任擔當的心靈一定是強大的心靈、健康的心靈。削減物欲的同時也就保護了自然,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對抗也就減少了,人的心靈也會因此得到滋養,“精神疾患時代”的陰影將漸漸淡去,人類將迎來陽光明媚的未來,這才是人類所期盼的“人類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