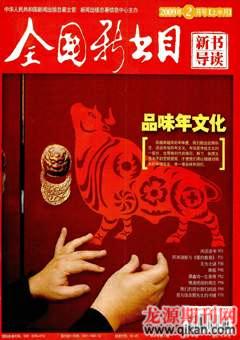歷史的背影
徐世平
研究民國史的人,一般都會去讀一本書,馮自由的《革命逸史》。
馮自由,1882年生,1958年5月6日在臺北因中風去世,其原名馮懋隆,字建華,祖籍廣東南海人。他是中國人,卻出生于日本,其父叫馮鏡如,英文譯名金塞爾,生于香港,入英國籍,早年因受太平軍的影響,隨父東逃日本,在橫濱山下町開設(shè)文經(jīng)商店(又名文經(jīng)活版所),專營外國文具及印刷事業(yè)。馮鏡如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痛恨清政府腐敗而剪去發(fā)辮。1895年,馮鏡如在日本橫濱,熱情接待了逃亡日本的孫中山和陳少白等人,并在孫的影響之下,在其文經(jīng)商店二樓成立了興中會支部,自任會長(中華書局版說明則稱長崎支部,不知何故)。幼年的馮自由,也因此結(jié)識孫中山先生,并加入興中會,后成為中國同盟會會員,時年14歲。

馮自由曾在他的《革命逸史》中,自述其加盟革命的經(jīng)過。 “當橫濱興中會成立時,余年甫十四耳。興中會成立后約一星期,某日中山(孫文)、少白(陳少白)、士良(鄭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詢余好讀何書。余曰:‘好讀小說。中山先生曰:‘好讀哪部小說?余曰:‘《三國演義》。中山先生曰:‘《三國演義》人物汝最喜歡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歡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順道之理。我等之興中會便是漢朝之劉備、諸葛亮。今之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等之起兵驅(qū)逐滿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謂余父曰:‘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令其入會?余父遂命余填寫誓約。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黨之原因也。”這段記述是生動的。其一,他加入興中會,是孫中山的意思;其二,原委是他喜歡諸葛亮;其三,當時入興中會,也是要填表和宣誓的。不過,中山先生舉“孔明之六出祁山”來形容民主革命,似乎不妥帖,也寓示著其革命的艱難程度。其時,少年的馮自由,年輕氣盛,其曾因《民約論》(今譯《社會契約論》)影響,以及反對康有為而將名字改為馮自由。17歲時曾自題詩一首,氣度不凡:
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
由此可見,馮自由與孫中山關(guān)系是相當親密的。據(jù)說,辛亥革命后,馮自由曾任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深得信賴。因此,他對孫中山先生的逸事,相當熟悉。比如,《革命逸史》之中,有關(guān)孫中山先生的記述相當多。其中,說中山先生喜歡下象棋卻棋藝不精,但牌就打得很好的記述,很有趣。
馮自由寫到:“中山畢生不嗜煙酒,讀書之余,間與人下象棋,然習之不精,好取攻勢而懈于防守,故易為敵所乘,余與胡漢民何香凝等皆嘗勝之。外國紙牌尤非其所好,然頗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廣東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橫濱時,每與陳四姑(名香菱)、張能之夫婦玩之。”哈哈,其中所提之陳四姑,乃孫中山的前任妻子陳粹芬,其原籍福建廈門同安,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稱 “陳四姑 ”。據(jù)說,福建同安人愛國華僑陳嘉庚是她的侄輩。陳粹芬身材適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勞,頗具賢德。
《革命逸史》中,涉及民國精英的此類記載,相當多。比如,說到過孫中山與黃興的旗幟之爭,以至兩人的關(guān)系,曾長期不和,也提及過孫中山先生關(guān)于 “革命黨 ”一詞的認知,甚至梁啟超的家庭愛情。他曾記述 “梁任公之情史 ”,認定梁啟超的婚姻并不美滿:“李女貌陋而嗜嚼檳榔。啟超翩翩少年,風流自賞,對之頗懷缺憾,然恃婦兄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晚清至民國之要人,幾乎全在他的筆下,生動形象。由此看來,馮自由的文學才能,可能是遠遠高于其政治才能的。
自民主革命始,馮自由先生一直是報人角色,曾任《中國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也當過《大漢日報》、《大同日報》主筆等職。畢其一生,似乎都是用筆在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山先生去世之后,馮自由于 1925年底在北京大學發(fā)起成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 ”,公開進行分裂活動,因此被國民黨 “左派 ”控制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開除出黨。不過,其做派孫中山先生不滿意,蔣介石卻是欣賞的,1935年,馮自由被蔣介石恢復國民黨黨籍,其時,馮自由一面經(jīng)商,一面寫《革命逸史》、《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等著作,有相當影響; 1943年,當選國民政府委員;1948年12月移居香港;1951年,蔣介石還特意電召其偕妻赴臺;1953年,馮自由任臺灣當局的 “國策顧問 ”,一直到死。
中國的文人,大抵說來,都有自視清高與固執(zhí)己見的通病。不過,這種通病,往往是被政治家們所利用的。馮自由的一生,你或許說不出,他到底有什么明確的政治見解,但是,他一旦認定的東西,卻會莫名地堅持而不會改變。
當然,我們也應該感謝馮自由,他畢竟留下了一部《革命逸史》,親歷之述,林林總總,讓我們可追尋歷史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