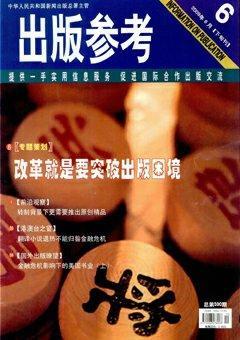改革就是要突破出版困境
劉偉見
出版改革已經進入到實質性的攻堅階段,改不改已經不需要討論了,怎么改也有了大的方針與政策,其最終目的是要通過改革重塑出版的市場主體。目前的突出問題是怎樣落實和完善各項改革措施,同時在推進改革時又要做好當下的發展工作。如果國際、國內市場是我們需要搶占的陣地的話,改革是在運動中調整作戰而不是停下來修整備戰。由此所引發的改革的復雜性與艱巨性就成為無論是改革的推動者還是被改革的對象都需要審慎面對的問題。
作為一家中央部委所屬出版社的負責人,筆者最近參加了多輪的出版改革培訓,深切感受到出版改革不僅是實踐問題,還是思想認識問題,一方面,我們對于出版改革所賦予和期待的實效是積極而又迫切的;另一方面,改革對于廣大出版社來說,雖然已經意識到很多發展問題亟需解決,但能否通過改革造就一個更為健康、發達的出版業,有的人還心存疑慮。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既是一場產業格局的調整戰,又是一場思想解放的心理戰。我們對于改革的迫切性還有著這樣與那樣的不同的認識,對于改革的方式還有著這樣和那樣的存疑。這是因為,出版有著與其他產業相比的獨特屬性,在過去的30年里,人們已經形成和習慣了所謂的事業化性質和企業化管理的體制思維。要在思想上與實踐上真正走向市場主體,需要我們在改革的視角下從國家文化戰略層面、產業主體建立層面、出版人的文化角色轉換這三個層面重新定位和拓展我們的認識。
處境的局促與視野的拓展
在文化的責任上,我們要拓寬出版視野,形成世界和中國并重的眼光。
文化競爭力已經日益成為世界各國競爭力的核心組成部分。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綜合國力已經大為增強,但文化的影響力卻遠遠遜于經濟的成就。表現出來的幾個值得關注的出版上的困境是:其一,在國際上,有關中國的出版物很少,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的出版經營比重很低,無論是文化藝術還是思想學術,我們都缺乏有影響力的作品和有代表性的作者。其二,頗為局促的是,我們在國際上沒有發聲的渠道。如果有那么三兩家影響力大的國際性傳媒集團,可能效果就會大不一樣。我們未必要強人為信,但至少可以發表出一些能說明問題的事實。其三,國內出版的市場競爭缺乏創造性,雄踞在暢銷榜上的圖書多數是引進類的圖書。除了生活實用類的圖書外,大量內容拼湊的圖書充斥市場。引進版的圖書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文化滋養,但我們自身培養精神內涵,提高人文底蘊的原創性作品更為重要。這雖然與整個社會的功利化趨向密切相關,但也與作為內容生產者的出版者缺乏長遠的戰略很有關系。
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也許在于:行政干預和保護下的畸形市場競爭,事業身份的保護和行業資源的分割使很多出版社沒有開拓的沖勁。小富即安的日子使我們很多出版人忘記了作為文化人的精神追求。相當一部分出版機構缺乏文化理想,這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是值得憂慮的。因為,文化的浸潤將使一個國家處于文化的劣勢上,從而成為別國文化的附庸。文化上一旦沒有了自己,這個民族就將衰亡。我們要從中華民族的興衰上去理解出版改革的重要性,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來考慮出版發展。目前的現狀是,在面臨國際的激烈的競爭中我們的產業格局需要調整,而我們小的出版個體的思想認識又局限于一城一池。這是出版改革需要直面和解決的首要問題,即讓我們的出版微觀組織從一種依附型思維轉向市場競爭的主體性思維。
出版界如果從國際、國內兩個視角來理解中央關于出版體制改革的精神,就會在文化的責任上形成自己應有的擔當。文化起著培本固基的作用。目前的現實是西方文化的強勢傳播使我們在潛移默化中學會了西方文化的欣賞與消費,而對本國的傳統文化表現出疏離,甚至是鄙視。問題在于,西方人不懂中國文化,中國人自己也漸漸不通中國文化,文化之衰微,其何以堪?而我們再怎么學也是有中國痕跡的西方文化,就像中國人過圣誕節是聚在一起大吃一頓一樣,這種非西非中的文化在國際上怎么會有影響力呢?所以,文化體制改革的目的就在于激活我們文化的創造力。當然,我們不能也不該夸大出版對文化發展的絕對性作用,但通過改革,出版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嘗試有所拓展:其一,大的出版集團軍中應當有那么幾支國際勁旅,他們是海外市場開拓的方面軍,能為中國出版的國際組稿、國際出版、國際營銷趟出幾條路子來。其二,我們的教育與出版實踐應當著眼于培育具有國際、國內兩種眼光的青年出版梯隊,在學校教育與工作實踐中有意于人才的專門培養。弱化出版的身份級別,培養出色的國際出版經營人才。其三,將文化與經濟做深度聯姻,共同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可以嘗試兩個戰略思路。一是借助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經濟的全球拓展成果,把文化播衍出去,中國經濟的觸角伸到哪兒,中國的文化就經營到哪兒。二是研究各國傳媒的特點,將文化與經營方式深度結合,開辟新的領域與市場。
產業主體性缺陷與轉化
從市場角度來說,需要推動出版建立獨立的文化市場主體地位。這需要我們要用市場主體的眼光重新定位我們的發展。傳統出版產業的主體性缺陷主要表現在:首先,在文化建設上功能發揮上出版產業的內容經營不足,往往為他人做嫁衣裳。從文化的產業鏈上來看,出版產業應當是文化產業的基礎產業。它是電影、電視、動漫等文化產業的內容來源。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有影響的文化作品首先是以出版形式最早出現的。但出版機構各自為戰,其小而全,散而多使出版產業一直沒有確立自己應有的文化產業的基礎地位,往往內容貢獻較大而經營不足。其二,缺乏公正、有效、誠信的市場競爭環境。在舊有的出版機制與體制下,一個明顯的現實是,出版作為一個產業,其市場化、產業化、國際化的程度非常之低。這與出版社沒有作為完整的市場主體密切相關。有的出版社想做大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持,有的出版社瀕臨倒閉而依附于政策資源,長久以來,就形成了一種不公正的發展現實,使強者不壯,弱者不死。這是一種市場的不公。有的發行企業的誠信更是聲名狼藉,而國有出版社對印刷、稿費的拖欠也是很多合作者的隱痛。其三,缺乏持續的品牌經營戰略。過去出版社作為事業單位的級別考核,使很多出版社社長亦官亦商,從領導層面上來說容易缺乏做大做強的動力。在舊有的機制下,有的老牌大社、名社開始出現空殼化。有的出版社社長不是著眼于市場而是著眼于政策資源與行業壟斷資源,忽略市場資源的積累。于是乎,很多出版社過分依賴于行業與政策資源,市場經營能力很弱,但職工的小日子卻過得還不錯。這一切都使改革充滿了復雜性與艱巨性。
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使我們積累了相當多的改革經驗,而改革的一些教訓也使我們很多出版人心懷憂慮。但國力的增強使我們具備了文化體制改革的物質基礎,改革的各項措施考慮到文化的特殊屬性相比較其他行業改革有著更多的保障,極力體現的是改革是為了更好地發展。但筆者注意到兩個較少提及的層面。一是主管者思維的轉換。如果改革只注重出版社這個主體而對主管者的思維轉換關注不夠,那么改革的效果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因為中國社會結構中的行政特性很容易導致思維慣性。出版社的主辦者無論是脫鉤與不脫鉤,最終作為帶有意識形態定位的特殊企業這個屬性仍然存在,這就需要我們的主管者轉換好改革后的管理思維。第二,政府在市場主體建立中的產業指導定位問題。目前政府在促進出版主體的確立,提升企業獲得更大的、自主的市場經營權,形成企業健康發展的市場主體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將促使出版產業在文化產業的價值鏈中脫穎而出,通過兼并重組,跨地區、跨國界形成大的出版集團旗艦,從而為文化建設貢獻更多更大的重大文化項目。同時,出版產業的壯大,也能突破目前出版社社會文化功能單一的現狀,形成多媒體發展,用更多的文化方式,發揮服務更廣大人民的積極作用。但一旦產業主體建立后,政府需要從推動產業長遠發展的角度進一步調整好自己的定位。
文化個性的缺失與凸顯
出版人作為社會文化的主體對于文化建設應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其在社會文化中也應當有著很高的文化地位,但目前我們的出版人的文化地位并不高。這需要我們通過改革凸顯出版人的文化作用,使我們的出版人具有更為高遠的文化眼光,形成更富特色的文化個性。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很多大家、名家同時也是出版家、編輯家,如王云五先生等。魯迅、茅盾等文學家在創作的同時也做著編輯的工作。建國后,有相當一批編輯家在文化界德望很高,如周振甫先生等。改革開放后,我們的出版人在“半”市場化的運作中文化地位相對降低了。具體表現在,其一,出版人的文化個性不突出。有的出版社給錢就出書,這使編輯的文化含量降低了。社會風氣對出錢出書認同后,也增加了有特色的名社堅持按傳統品位出書的困難。同時有的編輯對編輯的文化定位不準,模糊了書、報、刊的界限,出了很多時效性太強的書,失去了書籍應有的厚重,這使出版人的文化個性日益模糊。其二,出版人的社會文化地位不彰顯。不斷強化經濟效益的出版績效考核使很多編輯眼光向外,內心浮躁。編輯與作者的關系日益成為利益關系。出版人的文化地位經常被認為是“書商”,本應很具有文化權利的編輯人與出版人在文化見解上缺乏創見,造成出版人在很多文化實踐中處于“失語”狀態。第三,躋身于出版業的人才在出版的功利化考核機制下要么放棄學術品位,要么離開出版進入其他文化組織,使編輯成家的人越來越少。
出版改革能推動出版業不再依附行政、教育和行業,能使出版業本身的文化屬性日益凸顯。對出版人來說,在產業獨立與壯大的情況下更容易形成自己的文化個性。出版人這一群體將顯得更為獨立、自信。這將顯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一個發達的出版業將吸引更多的優秀的文化人來加入。這將真正提升出版的文化形象。每一個出版方向有那么幾個大文化人,那么,出版引領文化的作用就會凸顯。如果沒有出版業界的編輯大家、出版大家,那么我們期待的出版對于文化建設的作用只能是自說自話。其二,出版將更加專業化和職業化。職業出版人的出現將有利于改變有些人認為的出版有點文化就可以干的狀況,尤其是出版社的社長,未來將由從業有年,又業績突出的出版人來擔任。這樣出版的文化理想才能得到更好地實現。
(作者單位:中國書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