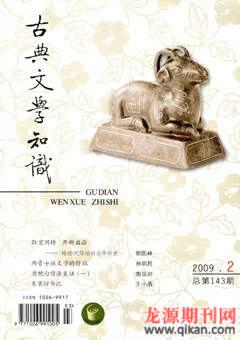取宏用精 開新啟后
郭院林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盫,江蘇儀征人。他以短暫的36年生命從學從政,留下了七十四部著作,這些著述不僅涉及經(jīng)學、小學、校讎學等傳統(tǒng)國學領(lǐng)域,而且還包括體現(xiàn)時代關(guān)懷的“預流”學問:政治、經(jīng)濟與教育,采取近代西方的學術(shù)方法與體系研究中國學術(shù)。“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認為當時50年為中國學術(shù)思想的黎明時代,而“此黎明運動中之劉君(師培)家傳樸學,奕世載德,蘊蓄既富,思力又銳”,(《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可見其對劉氏的推崇。劉師培力圖重建國學,為學界引進了西方的理論,并使其與中國國粹融為一體,對即將面對世界潮流的中國民眾,開新啟后,產(chǎn)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本文就劉師培的通達的治學特色、治學領(lǐng)域的開拓以及學術(shù)地位進行論述,以窺其博大精深。
一、 會通學術(shù)分歧的努力
作為“揚州學派”的殿軍,劉師培以“紹述先業(yè),昌揚揚州學派自任。”(尹炎武:《劉師培外傳》)劉師培繼承家學傳統(tǒng),兼有吳、皖兩派之長,既能確守漢詁,條源析流,又能辭外見義,學求致用。劉師培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不局限于儒家的經(jīng)典,對經(jīng)、史、子、集、道藏、內(nèi)典以及西學均有涉獵。劉師培論學貴“通”,他多次說到要做“通儒”,鄙斥“僅通一經(jīng),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他試圖糾合傳統(tǒng)學術(shù)的分歧,進而達到發(fā)揚國粹,建設民族特色文化,恢復國民信心的目的。他對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經(jīng)學史、文學史、文字學、倫理學等方面均有導夫先路之功。他不僅要打通經(jīng)史,平分今古文經(jīng)學,而且還要調(diào)和漢宋,溝通中西。
1. 等視經(jīng)子
與今文經(jīng)學家一味強調(diào)經(jīng)史之別不同,劉師培在經(jīng)史觀念上比較通達。他繼承龔自珍的學說,從學術(shù)起源的角度論證六經(jīng)皆史,認為 “六經(jīng)皆周公舊典”,“成周一代之史,悉范圍于六經(jīng)之中。”西周時“史官記言記動,仍仿古代圣王之制,故《易經(jīng)》掌于太卜,《書經(jīng)》、《春秋》掌于太史、外史,《詩經(jīng)》掌于太師,《禮經(jīng)》掌于宗伯,《樂經(jīng)》掌于大司樂”。“《春秋》者,本國近世史之課本也。”“若孔子六經(jīng)之學,則大抵得之史官。”“六經(jīng)本先王之舊典,特孔子另有編訂之本耳。周末諸子,雖治六經(jīng),然咸無定本,致后世之儒只見孔子編訂之六經(jīng),而周世六經(jīng)之舊本,咸失其傳。班固作《藝文志》以六經(jīng)為六藝,列于諸子之前,誠以六經(jīng)為古籍,非儒家所得私。”因此他再三申明“六經(jīng)之書,確為三代之古籍典章”(《劉申叔遺書·經(jīng)學教科書·古學出于史官論》)。
基于六經(jīng)皆史的觀念,所以他以六經(jīng)為史料,研究歷史,以之“考古代之史實,以證中國典制之起源,觀人類進化之次第”。成書于1905-1906年間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其史學代表作,該書體制上仿照西方歷史作品的章節(jié)體,縱向上按照歷史進化次序劃分階段,橫向上按社會政治、文化思想、軍事經(jīng)濟等分類敘述,加以分析,探索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于征引中國典籍外,復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界可以稍明”,進而擴大了“六經(jīng)皆史”的涵義,認為“上古時代之學術(shù),奚能越六經(jīng)之范圍哉?”
劉氏撰史期于“繁簡適當”,內(nèi)容力求簡明,在體例上仍不脫“以經(jīng)證史”的模式,參考資料仍以經(jīng)學古籍為主。而且,從其思想來看,也是從經(jīng)學中汲取民族革命的要素進行鼓吹反滿革命,終極目的在于發(fā)揚國粹以保種保國。劉師培倡導“六經(jīng)皆西周之史書”,發(fā)揮經(jīng)書中華夷之辨,目的最終在于進行民族革命。
2. 平分今古
劉師培首先從學術(shù)發(fā)展史的角度分析了經(jīng)學的產(chǎn)生,而且不承認有所謂今古文經(jīng)學的說法。他認為今古文師傳相同,都是詮釋《春秋》的,“《春秋》作于孔子,三傳先師持說實同。”“《春秋》三傳,同主詮經(jīng)。”(《劉申叔遺書·春秋左氏傳例略》)古文經(jīng)源于孔子六經(jīng)之學,三傳相通。“孔子之以六經(jīng)教授也,大抵僅錄經(jīng)文以為課本”,“弟子各記所聞,故所記互有詳略,或詳故事,或舉微言……然溯源流,咸為仲尼所口述,此《春秋》所由分為三,《詩經(jīng)》所由分為四也”。(《劉申叔遺書·漢代古文學辯誣》)他取消今古文的區(qū)別,認為“近代學者知漢代經(jīng)學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吾謂西漢學派只有兩端:一曰齊學,一曰魯學”“然魯學之中亦多前圣微言大義,而發(fā)明古訓亦勝于齊學,豈可廢哉?”(《劉申叔遺書·國學發(fā)微》)這就是說,所謂的“微言大義”并非今文學家的專利,而是今古文所共有的。
通過學術(shù)史考察,劉師培指出:“《春秋》三傳其分歧始于漢初,漢代以前同為說《春秋》之書。治《春秋》者或并治其書,以同條共貫。”今古文的區(qū)別僅在文字不同,“今文者,書之用漢代通行文字者也;古文者,書之用古代文字者也。”(《劉申叔遺書·漢代古文學辯誣》)這就證明今古文經(jīng)沒有根本區(qū)別,有的區(qū)別僅僅是外在形態(tài)而已。即使到了東漢之時,“經(jīng)生雖守家法,然雜治今古文者亦占多數(shù)。”“無識陋儒,斥為背棄家法,豈知說經(jīng)貴富乃古人立言之大公哉?”(《劉申叔遺書·國學發(fā)微》)同時又指出:“且當此之時,經(jīng)師之同治一學者,立說亦多不同。”這就是劉氏站在通儒的立場,抨擊固守家法的做法。
3. 持平漢宋
漢學與宋學是儒學中的兩大派別,漢學側(cè)重儒家經(jīng)典的訓詁考據(jù),而宋學則注重儒家經(jīng)典的“義理”,兩者各有師承,各有淵源。劉師培認為:“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是為宋學之祖;子夏、荀卿皆傳六藝之學者也,是為漢學之祖也。”(《劉申叔遺書·國學發(fā)微》)孔子均具師儒之長,所以漢學、宋學都淵源于孔子。這樣劉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歷來漢學與宋學的“道統(tǒng)”之爭,漢學、宋學都是得孔學之一端發(fā)展而成,都是孔學“道統(tǒng)”的繼承人了,幾百年來漢宋之爭原來本一家。他認為門戶之見都是可笑的,“但以合公理為主,不分漢宋之界”。
漢學與宋學的差異在于“漢人循律而治經(jīng),宋人舍律而論學,此則漢宋學術(shù)得失之大綱也”。漢宋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夫漢儒經(jīng)說,雖有師承,然膠于言詞,立說或流于執(zhí)一。宋儒著書,雖多臆說,然恒體驗于身心,或出入老釋之書,故心得之說亦間高出于漢儒,是在學者之深思自得耳。”(《劉申叔遺書·漢宋學術(shù)異同論》)
劉在《國學發(fā)微》中提出了對漢宋學術(shù)進行“以類區(qū)分,稽析異同,討論得失”的主張。他首先揭示了漢宋門戶之見遮蔽了對漢宋學術(shù)作客觀的認識,“東原諸儒于漢學之符于宋學者,絕不引援,惟據(jù)其異于宋學者,以標漢儒之幟。于宋學之本于漢學者,亦屏棄不言,惟據(jù)其異于漢儒者,以攻宋儒之瑕,是則近儒門戶之見也。然宋儒之譏漢儒者,至謂漢儒不崇義理,則又宋儒之忘本之失也”。
4. 會通中西
劉師培素有深厚的舊學根柢,但是他并不排斥西學。他試圖會通中西,或者藉西證中,從而達到樹立民族文化的信心。從1902年《江南鄉(xiāng)試墨卷》第三題《中外刑律互有異同,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應如何參酌損益,妥定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權(quán)策》來看,劉師培對于當時世界形勢頗為了解,所以才能得到考官評語“論治能識歐亞”。劉師培有關(guān)史學的著作深受當時西學新潮的影響,尤其顯著為對“進化史觀”的認定。劉師培曾作《讀天演論》二首,通過描寫景物的季節(jié)更替,“感此微物姿,亦具爭存志”,表達對《天演論》“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汰”思想的理解。劉師培對西學也十分看重,并深以自己不通外文未能及時獲得新知為撼。他有詩曰:“西藉東來跡已陳,年來窮理倍翻新。只緣未識佶盧字,絕學何由作解人。”(《甲辰年自述詩》)
劉師培運用進化理論和西方社會學、考古學、文字學知識,對上古社會作了探析。《古學出于史官論》發(fā)揮其考據(jù)學之長,以簡明而又堅實的證據(jù)論證了己之所見,語雖扼要但殊少紕漏。《周末學術(shù)史序》分學術(shù)為16類,《經(jīng)學教科書》已經(jīng)運用了經(jīng)學研究的新方法。用西方的學科分類體系界定中國古典學問并以此分類為體裁撰著學術(shù)史。以西方的學科分類體系界定中國古典學問,則完全是劉的獨創(chuàng)。(李帆《論劉師培學術(shù)史研究的地位與特色》)他所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一部公認為以進化論思想指導下的新型歷史教科書。為了使“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他認為書寫中國歷史應該注意,“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學術(shù)進退之大勢”,這些都反映了進化論思想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此書除征引中國典籍外,并參考若干西籍,目的尤在使“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
在接受西學的出發(fā)點上,劉師培是借西學佐證中學,甚至與“西學中源”有類似。劉師培的新學結(jié)構(gòu)以社會學、歷史學、哲學為骨干,談不上成體系地了解和接受西學,尚未做到圓融貫通的中西學交融,劉師培吸納西學的出發(fā)點和最終目的都在中學。劉師培在歷史、思想、學術(shù)諸方面將中國與西方進行比照,然后試圖會通。但是他自小受國學熏陶,國學始終是他立命之本,他甚至沒有象王國維等人理性上趨于西學,而情感上卻依然顧念中學的心理分裂,他不過是借西學來為中學開辟道路,所以他對中國前途充滿樂觀。要而言之,劉的“中西觀”,雖然主觀上要求“參互考驗,以觀其會通”,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往往只能做到“會”的層次,對中西學術(shù)進行簡單的附會,而不能真正做到“通”的高度,對中西學術(shù)的認識未脫晚清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窠臼。由于時代原因,劉還有保存國粹,與西學一爭高低的企圖,不免存有意氣之爭,這也影響到了劉對“中西會通”作進一步的探索。
二、 研究領(lǐng)域的開拓
1. 道藏研究
劉師培從小就博覽群籍,“內(nèi)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清末宣統(tǒng)庚戌年(1910年)孟冬,劉師培旅居白云觀,披閱《道藏》,對37種道經(jīng)加以勾玄提要,隨筆記錄,計37篇,錄成一帙,名曰《讀道藏記》(未完)(《國粹學報》第7卷,第1~5期,第七十五至七十七、七十九期。1911年),是為近現(xiàn)代最早的《道藏》提要。該《記》又被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第69冊、以及丁福保編《道藏精華錄》、胡道靜等主編《道藏要籍選刊》等書中。在后來的《讀道臧記》的序中,他敘述了這段經(jīng)歷:“迄于咸、同之際,南《藏》毀于兵,北《藏》雖存,覽者逾勘,士弗悅學,斯其征矣。予以庚戌(1910)孟冬旅居北京白云觀,乃啟閱全《藏》,日盡數(shù)十冊,每畢一書,輒錄其序跋。”法國漢學家施舟人評論道:“(中國本土)第一位比較科學的研究道教的人是劉師培(1884-1919),他是清代著名的學者劉毓松(1818-1867)的后代。1910年,他在北京白云觀讀《道藏》。”(施舟人《中國文化基因庫》)
2. 敦煌學研究
劉師培有幸親見早出的敦煌材料,并且迅速的著手進行研究,開敦煌學之濫觴。1909年9月4日,京師學者在六國飯店設宴招待伯希和,侍讀學士惲毓鼎在致詞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辦”。具體實施者,是羅振玉。羅氏又請端方襄助,敦請伯希和出售所攜和已運回國的四部要籍寫本照片,伯氏如約,陸續(xù)寄到,端方分交羅振玉和劉師培考釋。(榮新江:《北京大學與敦煌學》)1911年初,劉師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十九篇。劉師培以當時他能看到的伯希和供應的少數(shù)材料為依據(jù),撰寫《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19篇,1910年11月21日開始連載于《國粹學報》第七十五至八十二期。這是對傳統(tǒng)的“四部書”殘卷進行的最早的深入研究,以考訂寫卷年代、進行文字校勘、評定寫卷價值等為主。極為精審扼要,可稱典范之作。開創(chuàng)敦煌研究之先聲。(白化文《中國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劉師培已于1911年在《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國粹學報》辛亥第四號)中,據(jù)《新唐書·藝文志》和《太平寰宇記》,考出了《貞元十道錄》的名稱和作者,對地志類文獻進行整理和研究,并指出了該卷與傳世史志的異同。
3. 神話研究
1905年10月20日劉師培《國粹學報》上發(fā)表的《讀書隨筆》子目有《易言不滅不生之理》、《山海經(jīng)不可疑》。在《〈山海經(jīng)〉不可疑》一文,據(jù)“西人地質(zhì)學謂動植庶品遞有變遷”的新知識,再引漢武梁祠所畫證明“《山海經(jīng)》所言皆有確據(jù),即西人動物演為人類之說也”。他接受“地球之初,為草木禽獸之世界”的觀念,視“西國古書多禁人獸相交,而中國古書亦多言人禽之界”的現(xiàn)象為“古之時人類去物未遠”明證;則“山海經(jīng)》成書之時,人類及動物之爭仍未盡泯,此書中所由多記奇禽怪獸也”。既如此,此書所言自不可疑。(《劉申叔遺書》第1950頁)就史學方法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劉師培提出:后人對所不及見之事物,“謂之不知可也,謂之妄誕不可也”。這正是后來的趨新疑古派與舊派正統(tǒng)學者相近之處,兩者皆視其未見之古事物為不存在,所異者一以為“偽造”,而一以為“妄誕”也。另外劉氏對《穆天子傳》、《楚辭》、《列子》等包含豐富的神話文獻進行了研究。
4. 金石研究
劉師培的父親很重視石刻文獻的收集,自己也能靈活的運用金石材料進行研究。1909年為端方考訂金石,稱為“匋齋師”,撰有《論考古學莫備于金石》、《晏子春秋補釋》、《蜀中金石見聞錄》一頁等專文,另外零散的見于各種文章。如:“其旁訂金石文字也,于虢盤正月丁亥以三統(tǒng)術(shù)推之,定為三日。”(劉師培《先府君行略》)重視金石材料對于考古的價值(《論考古學莫備于金石》),研究范圍包括鐘鼎、宋磚、漢碑、殘硯、畫像等等,凡有益考古之金石,劉氏皆能為己所用。利用金石證明的問題也很廣泛,不局限于清儒的文字考據(jù),而擴展到社會學領(lǐng)域,如《中國古用石器考》一文證明中國社會發(fā)展經(jīng)歷了由石器-銅器-鐵器的發(fā)展,可謂新天下耳目。《唐張氏墓志銘釋》考地理,《周代吉金年月考》考歷法,涉及內(nèi)容廣泛全面。惜乎天不予年歲,系統(tǒng)難成。
三、 “二重證據(jù)”之濫觴
在近代,學術(shù)研究方法日益豐富、完善,一些大家紛紛提倡新方法,發(fā)掘新材料。劉師培也提出了獨創(chuàng)一格的見解,成為日后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的濫觴。劉氏對“考古”的概念理解比較開闊,在《古政原始論總論》中,他主張運用書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證的方法,再借以西方社會學所得出的定例檢視之,即可以考究“古代人群之情況”。他認為,考跡皇古,“厥有三端”:一曰“書籍”,五帝以前無文字記載,但“世本諸編去古未遠”,此外《列子》、《左傳》、《國語》、《淮南子》等書,其“片言單語,皆足證古物之事跡”;二曰“文字”,中國文字始于久遠,“文字之繁簡,足窺治化之深淺(中國形聲各字,觀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況……)”;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雖失傳,但刀幣鼎鐘,于考古都“珍如拱璧”。(《古政原始論·總論》)劉氏意識到外來的新知與固有的材料兩者參證對古代史的研究的進展很有意義。他所謂的書籍、文字、器物這三種材料,如依其來源和性質(zhì)區(qū)分,則可歸納為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二種。他雖未明確提出這兩種材料互相釋證的具體方法,但卻已注意到其間頗具互補性,因此主張引進西方田野考古學,發(fā)掘地下遺物。這兩點見解均體現(xiàn)于《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從中可以看到日后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的濫觴。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清華講授《古史新證》,他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故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之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楊向奎先生對此補充修正,他說:“過去,研究中國古代史講雙重證據(jù),即文獻與考古相結(jié)合。鑒于中國各民族間社會發(fā)展之不平衡,民族學的材料,更可以補文獻、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證據(jù)代替了過去得雙重證。”在這一方法體系的發(fā)展上,劉氏不能說不具有先鋒開導之功。
四、 國故整理之先行
劉師培率先清醒的意識到保存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終其一生為國學發(fā)揚不懈努力,為后來胡適的國故整理導夫先路。
1904年劉氏即發(fā)表《論孔教與中國政治無涉》、《論中國并不保存國粹》、《讀某君孔子生日演說稿書后》等文,同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展開針鋒相對的論戰(zhàn),澄清學術(shù)真相,表明他對傳統(tǒng)文化的看法。他認為“孔子者,中國之學術(shù)家也,非中國之宗教家也”。(《論孔教與中國政治無涉》)1905年劉師培又積極參與國學的保存與重建工作,劉氏擔任國學講習會正講師,該會以國學為“立國之本”,保存國粹。劉氏編有五種講義:《倫理教科書》、《經(jīng)學教科書》、《中國文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國地理教科書》。1905年創(chuàng)建的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就是以劉師培、鄧實、黃節(jié)個人藏書為基礎(chǔ),初約6萬卷,后擴充至20多萬卷。在《國粹學報》的82期中,其中80期刊有劉師培的文章(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三兩期沒有),劉師培著述在該刊中連載過的就有33種,在該刊部分發(fā)表五十余種。(鄭師渠《晚清國粹派》)1913年7月,劉師培在山西創(chuàng)辦《國故鉤沉》雜志,發(fā)表了幾篇文章。該刊僅出一期即停刊。1919年1月26日,《國故》月刊社在劉師培宅正式成立。劉師培、黃侃出任《國故》總編輯,陳漢章、馬敘倫、康寶忠、吳梅、黃節(jié)、屠孝寔、林損、陳鐘凡出任特別編輯,其中馬敘倫、吳梅、黃節(jié)三人為南社社員,張煊、薛祥綏、俞士鎮(zhèn)、許本裕等十名同學出任編輯。
整理國故這一發(fā)明權(quán)應歸于劉師培,而胡適的所作所為,只是對劉師培的回應。(朱維錚:《失落了的“文藝復興”》)劉師培在這方面的努力確實率天下先,而且與后來的整理國故相比更具特色與深刻性,它是對民族危機的獨特思考。國粹派之所以為國粹派,不僅在于他們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機;而且更主要還在于,他們看到了民族危機與文化危機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機是更本質(zhì)、更深刻的民族危機。他們提出了“保種、愛國、存學”的口號,大聲疾呼:愛國之士不僅當勇于反抗外來侵略,而且當知“愛國以學,讀書保國,匹夫之賤有責焉”的道理。(《國學保存會小集序》)劉氏決不是一個純粹埋頭于故紙堆里腐儒,而是具有滿腔愛國之情的學者。
(作者單位:新疆石河小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