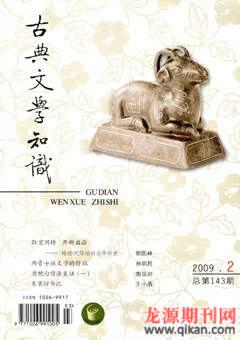《世說新語》條目發微(下)
劉 強
《規箴》第4條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不上諫曰:“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此條為今見唐寫本殘卷(僅存51條)首條,故頗引人注意。劉孝標注引環濟《吳紀》稱:“(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為此時舍書。”陳壽《吳志·孫休傳》與環濟《吳紀》文字略同,然不提群臣規諫之事。細玩此條文意,群臣雖有直諫,但敘事重心則落在孫休辯解之語上,置諸《言語》篇或許更為允當。按《世說》乃纂緝舊文之作,分門隸事時不免模棱兩可之處,王世貞作《世說補》,每每打亂舊局,以《德行》、《言語》之事屬之《品藻》、《夙慧》之科者所在多有,如以“郭林宗造袁奉高”、“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等條入《品藻》,以“徐孺子年九歲”、“孔文舉年十歲”、“鐘毓兄弟小時”、“梁國楊氏子九歲”等條入《夙慧》,皆是;而《政事》、《方正》諸篇招致的非議就更多了。此其一。
其二,孫休射雉的愛好當是受到其父孫權的影響,而納諫的雅量則相去甚遠。據《三國志·潘浚傳》注引《江表傳》:
權數射雉,浚諫權,權曰:“相與別后,時時蹔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浚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豈特為臣姑息置之。”浚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此事既狀寫規諫者潘浚神情如畫,又見出孫權的顧全大局,更合《規箴》之目。故余嘉錫先生加按語云:“今讀《世說》及《吳紀》,知權父子皆有此好。但權聞義能徙,而休飾辭拒諫,以故貽譏當世。”(《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修訂本,頁551。)這里的“貽譏當世”,應該是根據劉注引《條列吳事》“休在位蒸蒸,無有遺事,惟射雉可譏”數語。
問題是,《世說》為何不取孫權采納雅言之事,而偏愛孫休“貽譏當世”之舉呢?這就與《世說》的撰述旨趣相關。誠如魯迅所言,《世說》乃“遠實用而近娛樂”、“為賞心之所作”,故其遴選割舍,每每以“個性”、“趣味”為先,一本正經的題材反而不為所重。此條孫休答語,雖屬巧言,但婉轉關生,比之孫權的“不復射雉”,孫休的“耿介過人”一語,實屬夫子自道,更可見其真性情。《世說》之門類,雖各有定規,然“經”、“權”之間,決定取舍的杠桿,仍是一個大寫的“人”字。在這個“人”字面前,國家大勢、仁義道德、是非功過等等,反而成了可有可無的“背景”和“陪襯”。
《輕詆》第24條
庾道季(龢)詫謝公(安)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珣)《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于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又,《文學》第90條:
裴郎(啟)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珣)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兩條對照,可知王珣(字東亭)所作《經王公酒壚下賦》,才是導致“《語林》遂廢”的原因。按此條“王公”當為“黃公”,即《傷逝》2所載王戎嘆逝所經之“黃公酒壚”:
王浚沖(戎)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后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于此壚。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王戎是否有此事,后人頗有懷疑,該條劉注引戴逵《竹林七賢論》稱:“俗傳若此。穎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事,皆好事者為之也。”王珣所賦當即為王戎此事。謝安顯然贊同庾亮的說法,故庾龢(字道季)“讀畢”該賦才會出言譏諷。但謝安之所以“都不下賞裁”,除了《語林》傳寫“不實”外,當還有個人恩怨的因素在起作用。謝安與王珣素有嫌隙,王珣、王珉兄弟皆為謝家女婿,因猜疑致嫌,謝安既絕珣婚,又離珉妻,由是王、謝二家遂成陌路。上引《輕詆》第24條劉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記載此事說:“時人多好其事(指《語林》),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于謝坐敘其《黃公酒廬》,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謝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于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對謝安的“濫用權威”和時人的“個人崇拜”大加駁斥。
事實上,如此條末句所云:“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可知《語林》并未就此“遂廢”,至少至《世說》成書的劉宋時期還“健在”,只不過去掉了開罪于謝安的那兩條而已。劉孝標作注時或許也見過《語林》原書,其大量援引《語林》入注就是明證。周楞伽先生論及《太平廣記》轉引《殷蕓小說》實多出《語林》時,說:“《世說·文學篇》所記裴啟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后因記謝安語,被安詆為不實,其書遂廢,然讀者仍歡迎不衰,傳寫者乃冠以《雜語》、《雜記》、《小史》等名,究其文,無不采自《語林》,故非《廣記》從《小說》轉引,反系《小說》從此類雜題書名中傳襲《語林》之文也。”(見前揭周楞伽校注《殷蕓小說》,頁158。)

這里的《雜語》當即孫盛的《異同雜語》。既然檀道鸞就可以對謝安“挫成美于千載”的行為表示不滿,那么,孫盛暗中將“裴氏學”溷入自己的著作(如《雜語》)使其流傳后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其實,何止一個孫盛,《世說》編者大量采用《語林》入書,不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表現么?今之學者多以此條故事為口實,論證當時小說偏記亦必須“征實”,進而坐實《世說》亦全寫“真人真事”的主觀臆斷,恐怕難免失之不考。
《方正》第34、35諸條
《世說》的條目安排,看似紛繁無章,實則亂中有序。其一,一門之中,以所記人事的時間先后為順序;其二,就全書而言,一個人物的眾多故事被打散,歸入不同的敘事單元,統整起來不啻為一篇篇“人物列傳”;而就每一門類而言,記事的鏈條又每每以人物為單位,環環相扣,組成一組組藕斷絲連、相對獨立的“故事鏈”。
這樣的“故事鏈”一般有兩種情況。(一)連續的幾條故事有同一個人物作為記述的主體(主人公)。例如,《德行》第2—3條記黃叔度,4—5條記李元禮,6—8條記陳太丘父子;《言語》第3—5條記孔融及其二子;《雅量》第4—6條、《儉嗇》第2-5條記王戎;《豪爽》篇1—4條記王敦;《賢媛》第6—7記許允婦;《任誕》篇連續十余條記阮籍、劉伶;《假譎》第1—5條記曹操;諸如此類。(二)連續的幾條故事雖不共有一個“主人公”,但卻有一往來穿梭的“線索人物”,表明所記載的人物大體處在相同的時段和空間,只是“主”、“賓”的位置在不斷變換。例如,《言語》第55—61條分別記桓溫和簡文帝,二人仿佛輪流“坐莊”一般,敘事的重心也隨之變換。《雅量》第27—35諸條,所敘人物有桓溫、郗超、謝安、王坦之、孫綽、支道林、戴逵等,但起到關鍵的“樞紐”作用的卻是謝安。此外,還有一些條目,由于前后關系至為緊密,似乎是一對被拆散的“孿生兄弟”。比如,《方正》篇的兩條故事便透露了其中消息: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鐘雅獨在帝側。或謂鐘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鐘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方正》34)
庾公臨去,顧語鐘后事,深以相委。鐘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鐘曰:“想閣下不愧荀林父耳。”(《方正》35)
這是緊鄰的兩個條目,所記的主要人物是鐘雅。有意味的是,“鐘雅”之名在兩條故事中只出現了一次。后一條的“庾公臨去,顧語鐘后事,深以相委”,這里的“鐘”,顯然是承接上文語意,所指當為“侍中鐘雅”。也許,這是編者的一時疏忽,因為類似情況在《世說》中僅此一見。但它十分清楚地顯影了編者在編撰時的匠心所在。關于此點,古人亦有會心。凌濛初批點此條說:“按此‘鐘因承上文,遂不言名字;《世說》原有斷而不斷之意,不得擅改。”(前引拙著《世說新語會評》,頁192。)這里的“斷而不斷之意”,不是將《世說》編撰體例的幽微妙處一語道破了么?
有趣的是,因為“斷而不斷”,有時還會出現“合二為一”的現象,如今本《世說·賞譽》第5條: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于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于是用裴。
余嘉錫先生按此條說:“‘吏部郎以下當別為一條。”他的根據是:“‘吏部郎以下出王隱《晉書》,見《御覽》四百四十五。”細審文意,余氏所言誠非妄語。
當然,由于這樣一條“故事鏈”的存在,各個相鄰條目的故事,就未必能夠完全遵守“時序”來排列。比如《言語》篇3—5條記載孔融及其二子的故事,從孔融十歲到他被殺,時間跨度為幾十年;而緊接著6—10條記載的陳太丘父子、荀慈明、袁閬、禰衡、龐統以及劉楨等人的言行,有的還在孔融被殺的208年以前。不過,為了編織一條條相對獨立、引人入勝的“故事鏈”,任何一種對體例的“不忠”都是值得的。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