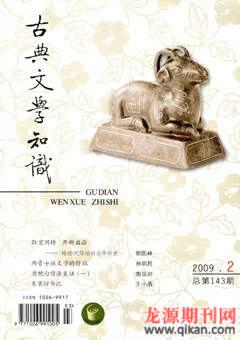話說鬼詩
熊憲光
清代著名詩人王士禛(漁洋山人)為蒲松齡《聊齋志異》題辭云:“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聊齋》一書說精道怪,言狐談鬼,難怪王漁洋有“鬼唱詩”之詠。其實,試檢古籍,不僅可聞鬼唱詩,而且可見鬼作詩。這在中國文學史上,絕對稱得上一大奇跡。也許由于這些鬼詩無非“姑妄言之”,只需“妄聽之”而已,所以向來不受重視,學者不屑一顧。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另類詩作毫無意義,不值一提。竊以為,倘能探其源流,明其特征,揭其內涵,還是可堪玩味的。
就現有資料看來,大約在春秋時期,鬼詩就產生了。《左傳》記哀公十七年(前478)秋衛侯夢于北宮,見一人登上昆吾之觀,披頭散發面朝北方喧嚷道:“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這就是有名的“渾良夫譟”。盡管此乃喧嚷之辭,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詩,但其主旨在申冤,富于激情,不乏詩的形象、節奏和音韻,故清杜文瀾輯《古謠諺》將其收入,近人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也將其收入“雜辭”類。值得注意的是,喧嚷者亦即作者是出現在衛侯夢中的渾良夫,而渾良夫是在當年春天被太子謀殺的,堪稱“新鬼”。所以不妨把《左傳》所載“渾良夫譟”視為鬼詩的濫觴。
所謂“鬼”的觀念,無疑是具有世界性的。當人類還處于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對許多自然現象都不能作出正確解釋的古代,“鬼”的概念就通過人們的幻想而產生了。越是不可捉摸的事物,越需要幻想出一個神秘莫測的概念來試圖作出合理的解釋,以一種虛幻的假象去消解蒙昧的疑惑,“鬼”的觀念大概就是這樣產生的。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
鬼:人所歸為鬼。以疊韻為訓。《釋言》曰:“鬼之為言歸也。”郭注(筆者按:指郭璞《爾雅》注。《釋言》為《釋訓》之誤。)引《尸子》:“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左傳》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禮運》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
人死則為鬼既然出自人之幻想,幻想的基點也就離不開人。因而鬼的形象雖可謂千奇百怪,卻只不過是人的形象的種種畸變;而鬼的行為看似不可思議,也大多與人的行為明暗相通。那么,既然人會作詩,為什么鬼不能呢?鬼詩的出現,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說,《左傳》所載“渾良夫譟”還不能算是真正的鬼詩;那么,到了晉代,干寶撰《搜神記》卷十六所載《紫玉歌》,便可以認為鬼詩之成熟了。紫玉為吳王夫差小女,與童子韓重相戀,吳王不許,未能成嫁,乃結氣而死,葬閶門之外。韓重游學歸來,往吊于墓前。紫玉魂從墓出,宛頸而歌曰: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怨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
《搜神記》是志怪小說,其中采集了不少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正如逯欽立所指出:“此故事或不始于晉時,然以歌飾說,當在晉時。”這就是說,這是一首晉人根據該故事情節,假托紫玉鬼魂創作的一首鬼詩。與此類似之作,還有祖臺之《志怪》所載《廬山夫人女婉撫琴歌》,《搜神后記》所載《陳阿登彈琴歌》,《樂府詩集》所載《劉妙容宛轉歌》。它們或詩或歌或騷體,或四言或五言或雜言,都是所謂死鬼亡魂之作,故被逯欽立先生一并收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之“鬼神”類。
晉代以后,鬼詩之作綿綿不絕。直至唐代,臻于極盛。唐代是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鬼詩的高潮出現在唐代,似亦與詩歌發展的歷史同步。后世鬼詩之作仍不絕如縷,但大都追隨唐代鬼詩之后塵,亦步亦趨;特別是鬼詩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征,大都在唐代鬼詩的范圍內兜圈子,無甚新的突破。因此,欲探鬼詩之奧秘,只需著重解析堪稱鬼詩典范的唐代鬼詩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煌煌巨編《全唐詩》卷八六五及卷八六六中,薈萃了整整兩卷鬼詩。這些詩的作者,據載都是陰間的鬼,但其生前身份各不相同。其中不僅有知名的南唐后主李煜、春秋時越國美女西施、孟蜀妃張太華、唐代女詩人薛濤等;也有不知名的巴峽鬼、介胄鬼、甘露寺鬼、巴陵館鬼、長安中鬼、河湄鬼、河中鬼、九華山白衣、虎丘山石壁鬼等;還有無名鬼、無名女鬼……真可謂林林總總,五花八門。
若論鬼詩內容,也是各顯其妙。有河鬼所作感謝舟人投食其枯骨的《愧謝詩》:“我本邯鄲士,祇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勞君行路悲。”有隔窗鬼所作怨恨其游魂思家難歸的《題窗下詩》:“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有李煜所作不堪為臣虜、傷心念故國的《亡后見形詩》:“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鐘山。”還有原本生活于春秋時代的西施,為鬼后居然與時俱進,會熟練創作后世成型的七言絕句:
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
高花巖外曉相鮮,幽鳥雨中啼不歇。紅云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
云霞出沒群峰外,鷗鳥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地,夢魂不到虎丘山。
綜觀鬼詩,不難發現,作者多以已逝者的姿態現身,用過來人的身份抒情。詩之內涵,大多感傷今昔之變,哀嘆生死之異,抒發繁華易逝、萬念俱空、生命短暫、及時行樂的思想感情。可怪的是,作者雖已為“鬼”,但作詩無非四言、五言、七言,也講究平仄和韻律,在語言運用和感情表達上大多類同凡人,看不出有什么特征足以證明這些詩作竟是來自另一個世界。
令人稱奇的是,鬼詩還有立意甚至某些詩句都相同者。如《全唐詩》卷865首載慕容垂(十六國時期后燕的建立者。公元385-396在位,死于軍中。)所作《冢上答(唐)太宗》,其小序說:
太宗征遼,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立高冢上,神彩特異。遣使問之,答以此詩。言訖不見,乃慕容垂墓也。
詩云:
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
其詩以死者與生者、過去跟今天作對比,抒發人生苦短、今昔滄桑的感嘆,勸誡世人不要貪求榮華富貴。
無獨有偶。同卷末載掌管陰司的鬼頭趙所作《獻高駢(唐僖宗時任淮南節度使)》一詩,其小序說:
駢筑羅城,多發掘古冢取磚。有一冢上鬼夜嘯,自稱冥司趙獻書,略曰:一介游魂,叨掌冥司。希于萬雉,免此一抔。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并附一詩于后幅。
詩云:
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此詩儼若《冢上答太宗》之翻版。這就奇了怪了,莫非陰間死鬼作詩也興抄襲?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些所謂“鬼詩”,其實都是活人所作;扯起“鬼”的旗號,乃是糊弄人的。有詩為證:
世上本無鬼,活人作鬼詩。分明陽世語,假冒陰間辭。情事隨牽扯,時空任挪移。幽幽白日夢,荒誕化神奇。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