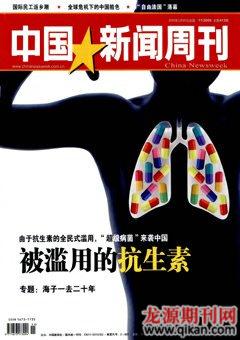讓看守所脫離公安機關
看守制度改革已不容拖延。至于改革的方向,法學界已達成共識,那就是把看守所劃歸各級司法局管理。這也是多數國家的通例。
云南“躲貓貓”事件之后,媒體又報道了兩起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死亡的案件:
2008年12月24日,河北省順平縣東五里崗村29歲的村民翟軍保,因涉嫌盜竊被順平縣公安局刑事拘留,今年1月3日被執行逮捕,羈押在順平縣看守所。2月16日,翟軍保死亡。據法醫學鑒定書顯示,翟軍保死于大葉性肺炎(化膿性)合并感染中毒性休克。平時身體相當壯實的翟死亡時體重為76斤,嚴重營養不良,體表及面部有散在表皮剝脫、結痂、皮損等,部分上前牙缺失。翟軍保家屬與公安局交涉,也曾經被關押。目前該看守所所長已被停職。
今年2月28日,陜西丹鳳縣公安機關以涉嫌今年元宵節一起殺人案件,傳喚丹鳳中學高三(10班)學生徐梗榮。3月8日,本來身體健康的體育特長生徐梗榮在審訊過程中突然發病死亡。事后,丹鳳縣政府和徐家簽訂協議支付了12萬元喪葬、撫恤費,徐梗榮的父母和奶奶終生享受當地最高標準低保。該縣公安局紀委書記已于3月16日被刑事拘留,當晚被送進了看守所,公安局相關領導也被停職檢查。
應該說,自“躲貓貓”事件以來,懾于網絡支持和輿論壓力,地方政府的反應都還是比較積極的。但是,悲劇終究已經釀成。現在最關鍵的問題,還是思考如何對看守所的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以避免看守所成為死亡所的悲劇再次重演。
官方、學界早就已經認識到,中國現行看守所制度多有不合理之處。最大的問題是公安機關合偵查權與羈押權為一。《看守所條例》第五條明確規定,“看守所以縣級以上的行政區域為單位設置,由本級公安機關管轄”。在現實中,檢察機關進行監督。但偵查權恰好就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行使,尤其是公安機關。
這就造成了一個有邏輯漏洞的制度安排:公安機關享有廣泛的偵查權,負責尋找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證據,而犯罪嫌疑人就被關押在公安機關自己管理的看守所內。公安機關一身擁有兩個身份,既為偵查機關,也是羈押機關。從理論上講,面臨破案壓力的公安機關自然可以很方便地以違法違規的行為對待自己看管的嫌疑人,以獲得證據、主要是口供。
由此就不難理解,類似“躲貓貓”之類的事件每年都有發生。有人統計過,從2001年至2008年,媒體詳細報道過的案例中,有22名嫌疑人在看守所內暴亡。比這情節稍輕的濫權行為也廣泛存在。比如,《看守所條例》第二十八條明文規定,“人犯在羈押期間,經辦案機關同意,并經公安機關批準,可以與近親屬通信、會見”,但是,公安機關完全可以以妨礙偵查、泄露案情為由。拒絕嫌疑人與親屬通信、會見。因而經常出現嫌疑人被關入看守所多天而家屬不知親人何在的怪事。
這樣的看守所體制既不人道,也有悖法治的基本精神。但其得以維持的原因在于,偵、羈合一,便于公安機關破案。這樣的思考方式是不正確的。維護社會的和平秩序當然是十分重要的價值,因而。保證偵查效率是必要的。但維護社會秩序的效率之基礎是正義。如果沒有正義,效率就毫無意義,甚至會產生巨大負面效應。偵查機關迅速破案固然是好事,但偵查機關如果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迅速破案,那就不是好事。它會污損偵查機關的形象,并令人們對整個司法體系的運轉之正義性產生懷疑,論起對于社會秩亭的損害,莫此為甚。
因此,看守所制度改革已不容拖延。至于改革的方向,法學界已經達成共識,那就是把看守所劃歸各級司法局管理。這也是多數國家的通例。
這樣的設置,利用權力分立、制衡的原理,可以較好地保護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履行偵查職能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甚至審理案件的法院,都有一種迫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認罪行的傾向,因而,不管由他們哪一家管理看守所,都可能利用這種權力以違法違規方式獲得證據。相反,司法局卻在司法體系之外,是一個比較中立的第三者。如果看守所劃歸司法局,那對看守所、司法局來說,它的唯一職責就是看管好嫌疑人或被告人,而不用操心從嫌疑人或被告人那里獲得證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要考慮到這一點,但他們要訊問嫌疑人或被告人,卻必須得到看守所、司法局的同意,而后者對于前者訊問期間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安全是負有責任的。當然,司法局也更容易安排親屬、律師與當事人會面。
司法部官員在人大會上也曾表示,支持深圳在這方面進行試點。其實,這樣的改革應當迅速推向全國。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如何對待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就是其對待普通民眾的寫照,因為,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法院判決之前理論上應是無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