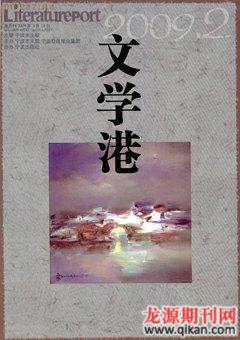發癡
趙淑萍
小巷深處,有一家理發店。門還是老式的木板,那墻已蝕跡斑斑。春天,墻上的綠藤綴幾朵嫩黃的花。秋陽下,狗兒慵懶地摸著眼睛,偶有幾片葉子枯蝶一樣落在檐前。年輕人是不上這個理發店理發的。那個年老的理發師,只給一些上年紀的男人或小孩理發,現在不斷翻新的發式,他大概也不會吧。
生意不咸不淡,一到下午,他就把門一關,誰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
人們叫他“發癡”,意即他一見頭發就癡迷。發癡年輕的時候是一個英俊的小伙子,話不多,一操起梳子和剪子,就來了精神。他修理幾下,就往鏡子里看一陣。大體完成后,他會貓著腰,和主顧面對面,凝視著他(她)的頭發,那目光就像審視自己的一件雕刻或繪畫作品,目光冷峻而挑剔。他精細到對任何一根發絲都不肯放過。最后,倒是主顧坐不住了。“你快點兒,這樣已經蠻好了。”顧客催他。從他店里出來,人人都煥然一新,神采奕奕。“發癡”的外號也就那樣取出來了。理發店旁邊是個中學,一些老師常到他這里理發。一位老師還建議這個店掛個招牌:一絲不茍。發癡沒當一回事。
“文革”開始了,造反派們來攛掇他,要他帶上剪子去給挨批的老師剃陰陽頭。發癡開始借故推托,可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他干脆就從鎮上消失了。讓他剃陰陽頭,在發癡看來,那不啻于讓他下地獄。理起發來如癡似醉的他,鋪蓋一卷,悄悄返回他鄉下的老家去了
后來,“文革”結束,發癡回來了,就不是一個人,他還帶來一個水靈水靈的女人和一個男孩。男孩長得像母親,清清秀秀。發癡躲到鄉下去,結果,一個上海知青給他做了老婆。上海女人白凈、優雅。發癡是很疼她的,什么活都不讓她沾手,甚至女人要幫忙給主顧洗頭,他都不肯,唯恐她白嫩纖長的手指會粗糙、腫大。他每天清早生爐子,不讓女人接近,等煙散了,水開了,他才讓她灌灌開水,同時看住孩子。他們的生意非常好,可晚飯后,發癡就絕不營業,而且關上大門。“他們在做什么呀?”人們交換著疑惑的眼神。
有一天,一個厚臉皮的光棍透過門的縫隙往里張望。他看見發癡正在給他的女人盤頭。那女人穿著雅致的旗袍,發癡不僅給她盤高高的春山一樣的髻,還給她修眉。消息馬上傳開了。“怪不得,那女人的眉毛彎彎的,細細的,像裁出來的一樣。”女人們滿懷羨慕地說。發癡的女人一露面,還是平常的發式,穿著平常的衣裳,那旗袍,怕是只穿給男人和她自己看的。
接著,政策下來了,知青可以回城了。發癡的女人,在家又是獨女。“把你老婆看住,別讓他跑了。”發癡在理發時,好多位主顧提醒他。
發癡的女人還是回上海了,是發癡主動提出離婚。(下轉第108頁)
(上接第106頁)發癡很愛孩子,上海女人把孩子留給了他。父子倆相依為命。那孩子也真乖,他父親理發,他就一個人在理發店里看小人書或在一個竹匾里玩彈珠。
孩子中學畢業,成績出眾。發癡咬咬牙,把他送往上海他母親那里去。畢竟,大城市里的教育質量更好。
發癡成了單身漢。他的話更少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發癡再也不打理時尚的發型了。鎮上別家的理發店門口掛起轉動的彩條燈,櫥窗邊貼出一個個頭發油光可鑒的模特兒的照片,他的理發店還跟二十年前一樣。姑娘、小伙自然不上他的店去。鎮上上年紀的人卻無一例外都到他這里理發。他一如既往地認真,只是,一到下午,他的店就關門,雷打不動。開始有一陣,有人叫門,要理發,他硬是不開,后來人們就習以為常。
人們猜疑,發癡關門,一個人在里邊做些什么?門內沒有什么響動,傍晚,門開了,發癡站到街頭,望那逐漸亮出來的星星。月亮升起來了,他蹲在地上,眼神癡癡的,好像胸中就只有一個月亮,街巷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一天下午,一個小男孩的一顆彈珠滾進了他木門檻下的縫道里。孩子伸手去撿,卻撿不到。那可是一顆嵌著花紋的彈珠,小男孩大聲地叫著,幾乎帶了哭腔。發癡竟然心軟,破例來開門,還帶他進去一起找。
這時,小男孩看到了那一幕:發癡的屋里居然有一個新式的頭模,那上面是盤了一半的頭發。那個發式,非常漂亮,就像新嫁娘的那一種。旁邊還放著一朵絹質的紅玫瑰,還有許多發夾。
孩子回家后,比劃著把看到的情景講給他母親聽。旁邊的祖母悠悠地開了腔:“當初,他就是那樣給上海女人盤頭的。”祖母還說:“發癡要推出這樣的發型,生意肯定熱火。哎,放走了女人,他落得一場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