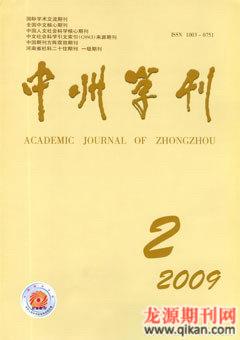分蘗與聚合
鄭 鏞
摘要:由河南光州固始分蘗出的閩南族群對中原文化有特殊的記憶。唐初陳元光隨父“出鎮泉潮間”,平定“蠻獠”嘯亂,并奏請建置漳州。中原文化開始在閩南大范圍的傳播。陳元光的開漳之功受到閩南民眾的稱頌,他本人則被神化,成為闖臺共仰的開漳圣王。陳氏及其他開漳將士族裔逐漸形成有地域特征的“族統”觀。光州固始作為文化符碼也被閩南族群所體認,成為文化聚合中的重要標識。
關鍵詞:中原文化;閩南族群;光州固始
中圖分類號:K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09)02-0165-05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菲力浦·漢·博克在論及人類社區的增長時認為有三種選擇方式:穩定、分裂和聚合。至于選擇何種方案取決于自然和文化力量的影響。以其理論研究漢晉以降中原地區向閩粵邊地的移民,當有啟發意義。與其采用“分裂”表述人類社區變化,筆者以為不如用“分蘗”一詞更為確切。由此地向彼地進行規模性的人口移徙,可認定為族群分蘗。分蘗一詞源于生物學,指禾木科植物在地下或近地面處發生的分枝,通常在稍膨大而貯有養料的分蘗節上產生。中古時期中原地區向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今閩南地區的人口移徙可視為典型意義的分蘗。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分蘗——穩定——分蘗在不同的空間中往復發生,但文化上的族群認同卻一步步地走向聚合,并在聚合中產生了富有標識意義的文化符碼——光州固始。
一、分蘗——在移徙中完成
就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及結構考察,中原文化一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原或稱中州尤其是其問的河洛地區在歷史上被稱為“天下之中”。李學勤先生在為《河洛文化與殷商文明》一書所做的序言《河洛文化與中原文化》指出:“中原地區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重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地理位置上占全國的中心,從文化內涵上能吸收和容納周圍甚至邊遠地區的文化因素。”從文化學意義上可以這樣理解;吸收、容納和凝聚各種文化因素是一種“聚合”,而文化的向外傳播輻射和影響則為“分蘗”。換言之,分蘗是文化的有效擴散,聚合是文化的群體性認識。當然,在傳統社會中文化的“分蘗”與“聚合”主要還是由移民的規模運動來完成的。
今福建地區原為西漢王朝藩屬閩越國的領地,居住著“百越”中的一支——閩越族。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統治閩越的余善起兵反漢失敗后,漢武帝盡徙當地居民于江淮間,東越地遂虛。這一地曠人稀的空間氣候溫濕,四季常青,溪河縱橫,沖積平原土地肥沃,海岸線綿長,富有海鹽之利,是人類理想的生存之所。因此,遂有北方漢人陸續南下。
西晉末年,中州發生“永嘉之亂”,此后兵連禍結,動蕩不安。許多門閥士族紛紛舉族南下,逐漸遷至福建木蘭溪流域、晉江流域和九龍江流域。至唐代前期,九龍江流域已聚居了相當數量的漢人,由于與當地土著居民發生矛盾,爆發了所謂的“蠻獠嘯亂”。總章二年(669),朝廷派歸德將軍陳政出鎮泉、潮二州之間的故綏安縣地(今漳浦、云霄一帶)。當時,陳政率府兵3600多名,從征將士自副將許天正以下123員人閩。陳元光以鷹揚衛將軍的身份,隨同父親陳政領軍赴閩。儀風二年(677),陳政病故于軍中。其子元光以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銜代領兵眾,時年21歲。永隆二年(681),陳元光打敗“蠻獠”主力,泉潮間的“嘯亂”日趨平定。
陳政、陳元光的率兵入閩,是一次具有移民性質的進軍,對漢民在閩南地區的開發作用甚巨。根據近人的統計,先后兩批府兵共約7000余人,可考姓氏計有60余種:陳、許、盧、戴、李、歐、馬、張、沈、黃、林、鄭、魏、朱、徐、廖、湯、涂、吳、周、柳、陸、蘇、歐陽、司馬、楊、詹、曾、蕭、胡、趙、蔡、葉、顏、柯、潘、錢、姚、韓、王、方、孫、何、莊、唐、鄒、邱、馮、江、石、郭、曹、高、鐘、汪、洪、章、宋、翟、羅、施、蔣、丁。另外,還有隨軍家眷可考姓氏者40余種,其中除與府兵將士姓氏重復者外,尚有18種姓氏:卜、尤、尹、韋、甘、寧、弘、名、陰、麥、邵、金、種、耿、謝、上官、司空、令狐。以上府兵將士與軍眷姓氏可考者合計近90種。當然,這些姓氏是否全部都是來自北方的漢民,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但就整體情況而言,以上所統計當時開發九龍江流域的近90種姓氏,大部分應是從北方隨軍移民而來的。這數十姓府兵將士及其家眷,繁衍生息,形成了唐代開發九龍江流域的骨干力量。
垂拱二年(686),朝廷應元光之請,在泉、潮之間置漳州,并以漳浦、懷恩(今云霄一帶)二縣歸隸之,委陳元光任漳州刺史。漳州建立之后,為進一步穩定局勢,陳元光“奏立行臺于四境,四時親自巡邏,命將分戌”,把所屬軍隊分布于閩南各地。于是,北至泉州、興化,南逾潮州、惠州,西抵汀州、贛州,東接沿海各島嶼,均為陳元光部屬的守戌地和開發地。從漳州建州到唐末的200余年間,雖然中原地區有過不少戰亂,但福建一帶尚屬安定,這給陳元光及其部屬的后裔們在漳州各地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因此到了唐代后期,漢民在漳州的開發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逐漸縮小了與泉州等地社會經濟發展上的差距。
唐代前期陳政、陳元光父子率領府兵入閩守戌開漳,是北方漢民遷移福建的一個高潮期。但并不是說唐代的其他時期就沒有北方漢人入遷閩中。事實上,從唐初直到唐代后期,北方漢人入閩幾乎是不間斷的。隨著福建與北方地區聯系的加強,唐代其他各個時期都有不少漢民遷移而來,只是數量有多有少,規模不如唐前期陳政、陳元光率眾人戌那樣集中,遷居的地點比較分散而已。
唐代后期,中原戰亂加劇,軍閥各據一方,民不聊生,北方士民再次南遷,形成了漢人入閩的又一次高潮。其中尤以王潮、王審知兄弟率部入閩的數量為巨。王潮、王審知原為河南光州固始縣的農民,王氏兄弟乘黃巢起義之機組織鄉兵渡江南下,轉戰于江西、廣東。景福二年(893),王氏部隊攻進福州,閩中各地紛紛降服。當時的唐朝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各地的有效控制,唐昭宗只得任命王潮為福建觀察使,盡領閩中五州之地。王潮死后,其弟審知繼任。907年,唐朝滅亡,王審知被后梁太祖朱晃封為閩王。審知死后,其子延鈞于933年正式稱帝。改國號為閩。
閩國是中原移民在福建建立的第一個地方性割據政權,對于促進北方漢民的人閩影響很大。閩國建立后,王潮、王審知的部屬絕大部分都定居于福建。宋人陸游撰《傅正議墓志銘》云:“唐廣明(880-881年)之亂,光(州)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今多為士家。”《崇安縣新志·氏族志》記述:丘氏,唐僖宗時有丘禎、丘祥、丘福兄弟三人由固始隨王潮入閩,居崇安之黎陽。張氏,“唐廣平(明)間,張威偕兄感,弟咸由固始入閩,威居建陽,感居三山,咸居浦城。威孫義贅于本邑會仙里……遂留居于此。其子孫散處于下梅吳屯及大渾之西山”。這班追隨王氏兄弟入閩的部屬,因王氏在福建的得勢,大
多也成了一方新貴。他們利用政治上的優勢,各自在福建尋找合適的地點定居下來,從而成為地方上的顯姓。
當時隨王氏兄弟入閩的中原人士,除了軍隊之外,還有眾多落難的政客、士子、文人等。當時中原有名的文人、學者,如李洵、王滌、崔道融、王溧、夏侯激、王拯、楊承休、楊贊圖、王倜、歸傅懿等,“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從之聲齊袁、白,甲乙升第,巖廊韞望,東浮荊襄,南游吳楚,謂安莫安于閩越,誠莫誠于我公(指王審知)”。這班文人才子相聚于福建,有了安身之地和發揮才能的空間,故五代是福建文教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清末陳衍曾評這一時期福建的文化事業說:“文教之開興,吾閩最晚,至唐始有詩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詩人時有流寓入閩者,詩教乃漸昌,至宋而日益盛。”這一評述反映了福建地區的正統封建文化教育發軔于唐代前期,至唐末“中土”士人大量南來,漸成規模,至宋而興盛的基本史實。由于王審知父子在福建全境設立了比較完整的政治體制,因此,這一時期入閩的北方漢民,在福建地域上的分布要比以往幾次更為廣泛,可以說基本上遍及福建各地。同時,在漢晉以來的移民大多占據自然條件比較優越的閩江下游流域、九龍江流域、晉江流域等沿海地帶的情況下,這一時期入閩的漢民,有逐漸向偏僻山區拓展的趨向。
至宋代,北方漢人特別是人口較稠密的中原地區漢人已完成較有規模的向福建的移民,這一移民過程也是中原文化向中國東南沿海的傳播過程。東晉南遷漢人帶來的中原文化與生產技術可從出土文物得到證實。陳政、陳元光率軍平亂更是注重恩威并施,特別是“創州縣,興庠序”,建置了中國最早的書院之一——松州書院,聚生徒而教之,此后“民風移丑陋,士俗轉醞醇”。至唐貞元八年(792)龍溪周匡業明經及第;唐元和十一年(816)其弟周匡物進士及第,越二年,漳浦潘存實又登科時距漳州建州已有130年,實現了當年陳元光“縵胡之纓化為青衿”的預定目標。唐末五代閩國建立后,除大量文人士子來附外,一大批僧侶也慕閩國主好佛之名紛至沓來,佛教在閩地廣為傳播,至南宋人稱泉漳二州為“佛國”,謂“此地人稱佛國,滿街皆是圣人”。
以上史實說明族群文化分蘗后,離開母本的分株異地植根、生長、開花、結果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然后再衍發為一種既保留母本的若干文化基因又有別于母本的新的文化生態。
二、聚合——在認同中強化
其實,自東晉到唐末五代時期,遷徙入閩的北方漢人雖以中州士民為主體,但并非全都是中原人士,更不是全來自光州固始,而混雜了其他北方各地的四民百姓,“王彥昌,其先瑯邪人,自東晉肅侯彬遷于閩,居龍溪后析龍溪置漳浦,遂為漳浦人”。瑯邪為西晉時山東膠南縣名,可知王氏的一支是由山東入閩。陳政人閩后,也在泉、潮之間“乃募眾民得五十八姓,徒云霄地,聽自墾田,共為聲援”。這58姓應是唐代前期之前陸續入閩定居的各地漢人,甚至可能含有被同化的當地土著。唐末五代亦復如是:“自五代亂離,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賈,多避亂于此,故建州備五方之俗。”
至于陳政、陳元光的籍貫,學界爭論不休,自有其史料上的稀缺不全,也有認識的各執一端。目前,有三說,一是“嶺南首領”說,導源于唐人張鷟的筆記小說《朝野僉載》和明人黃佐的《廣東通志》,前者云“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后者直稱陳元光為廣東“揭陽人”,但后面一句是“先世家潁川”,值得治史者玩味。二是“河東說”。最早、也較可靠的史料見諸唐人林寶的《元和姓纂》,該書“諸郡陳氏”曰:“司農卿陳思問、左豹韜將軍陳集原、右鷹揚將軍陳元光、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陳雄,河東人。”宋人王象之《輿地紀勝》“循州威惠廟”條載:“朱翌《威惠廟記》云:陳元光,河東人,家于漳之溪口。”明人林魁等所纂修的《龍溪縣志》中也沿用“河東說”云:威惠廟“在城北門外,祀唐將軍陳公元光。公河東人。父政,以諸衛將軍戌閩”。同一時期的蕭廷宣所撰《長泰縣志》也云“威惠廟,敕靈著順應昭烈廣濟王,姓陳氏,諱元光,系出河東”。崇禎初梁兆陽主修的《海澄縣志》“儒山廟”更引宋本《淳佑清漳志》曰:“靈著順應昭烈廣濟王,姓陳氏,諱元光,系出河東。”三是“光州固始說”。明末何喬遠《閩書》卷四十一“君長志”記陳元光為光州固始人。魏荔彤康熙間主修的《漳州府志》載:“陳政,字一民,光州固始人。父克耕從唐太宗攻克臨汾等郡,政以從征功,拜玉鈐衛翊府左郎將,歸德將軍。”嘉慶間董詰總裁的《全唐文》曰:“元光字廷炬,光州人。”明清間的諸多姓氏宗族譜也都認為陳氏一脈來自河南光州,潁州為之郡望,如漳州地區的《潁川開漳陳氏族譜》、廣東海陽宋朝人許君輔所編《韓山許氏族譜》皆載陳元光為“光州固始”人。
南遷漢人為抬高門第附會冒籍的做法由來已久,五代北宋時出于功利的需要,相當一部分姓氏攀附王潮、王審知光州固始籍,這一現象被南宋的福建莆田人方大琮所詬病,說:“王氏初建國,武夫悍卒,氣焰逼人。閩人戰栗自危,謾稱鄉人,冀其憐憫,或猶冀其拔用。后世承襲其說,世(祀)邈綿,遂與其初而忘之爾,此閩人譜牒,所以多稱固始也。”著名史學家鄭樵亦說:“今閩人稱祖者,皆光州固始。實由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兄弟以固始之眾從之。后緒與宗權有隙,遂拔二州之眾人閩。王審知因其眾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氏譜者,皆云固始。其實謬濫云。”至明代同安洪受甚至還寫了篇頗有影響的文章《光州固始辨》,力議閩南族群并非來自光州固始。說明南宋末起,這種否定性的觀點甚有影響。
其實陳政、陳元光一脈的陳氏家族并不屑于攀附王氏。陳氏軍功世家,自陳政起,后陳元光、陳坰、陳酆、陳謨五代守漳,自總章二年到元和十四年(819)經營閩南達150年之久,家族、部眾勢力之強,門第之顯赫眾所周知,入漳時間又遠早于王審知家族。陳氏子孫完全沒有理由去攀附王氏而改其籍貫。根據陳政、陳元光家族唐初的移徙變遷,陳氏籍貫的三說均有采信的理由,可綜而析之。據《元和姓纂》陳政一脈“系出河東”應無歧義。此為祖籍地,而光州固始則為陳政父陳克耕從唐太宗平天下后奉命率部駐扎之地,并由此出鎮潮泉之間。嶺南首領說也不能輕易否定。這是幾乎與陳元光同一時代的文人對其南下后身份的認定。據兩《唐書·地理志》和《元和郡縣志》以及宋人吳輿的《漳州圖經序》載因陳元光奏請建置的漳州很長一段時間劃歸嶺南道。漳州自初建至天寶元年的50多年間隸于嶺南道。天寶十載,漳、潮二州又從福州都督府治下分出,劃歸嶺南通。張鷟將陳元光當作“嶺南首領”——漢人軍事集團的領袖人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筆者贊同清代康熙年間學者莊亨陽等所纂《龍溪縣志》對祖籍、出生地、生活區域的處理方法。該志“唐列傳”首列“陳坰”曰:“陳坰,字朝佩,先固始人,祖政,父元光,開漳因家焉,遂為漳州人。”陳坰
既可稱“漳州人”,陳元光長年率軍赴潮平寇稱為“嶺南首領”也無不可,但“嶺南首領”決不能誤認為是“嶺南土著”。
概言之,筆者認為陳氏家族的籍貫三說可以并存統合:河東是其祖籍地,光州固始是其駐扎家居、奉詔出征地,嶺南為其征戰戍守地。唐以來陳元光的后人為何在自家宗族譜上認定是光州固始人?陳氏隨行部將后裔亦大都認光州固始籍,如漳州龍海洪岱蔡氏祠堂楹聯曰:“濟陽衍派,上溯周姬分固始;鴻山發跡,遐思祖澤啟清漳。”漳州方姓奉隨陳政入閩的隊正方子重為肇基始祖。云霄縣陽霞村建有“昭德將軍方子重祠”楹聯日“輔王師,出固始,萬里戎機安閩粵;傳衍派,播漳州,千秋業績啟云陽。”誠如清乾隆《龍溪縣志》所指出的:“陳元光,光州固始人,王審知,亦光州固始人,而漳人多祖元光與泉人多祖審知,皆稱固始。”甚至漸被同化的閩越土著后裔也追隨人閩漢人改稱自己的祖先來自光州固始,這是值得關注的社會文化現象,其中蘊藏著族群遷徙、文化傳播若干密碼。通常情況下,由分蘗而遷徙的族群習慣于對先輩遺傳下的歷史文化信息進行篩選,而后進行重新組合和認同。閩南的陳氏家族以及其他相當一部分氏族不論是否為唐初隨陳政、陳元光入閩,大都在族譜上鄭重標明是來自中原(中州),來自光州固始,并非全然受唐末王潮、王審知入閩建國的時尚影響,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一種典型的族群認同,更確切地說是對中原文化的認同。造成這一認同的原因有三:
(一)中原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中原在很長時間里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從中國文明形成的唐虞,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城大都在這一地區。其實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已經比較細致地講過:“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現代考古學的田野工作對此做出了證明,經發掘研究有可能屬于唐虞的山西襄汾陶寺,可能屬于夏初的河南登封王城崗,夏代的偃師二里頭,商代的偃師尸鄉溝、鄭州商城等遺址,都在晉南豫北,環繞河洛地區。周人本立都于陜西關中,灃水沿岸的豐鎬,伐商后在今洛陽建立東都,形成宗周、成周兩都相峙的局面,以及橫貫中原的王畿區域,為此后漢、唐的長安與洛陽兩京奠立了基礎。中原也是北宋以前中國經濟的中心。中州素為“天下之大湊”,是貿易往來、通達四方的樞紐。同時,中原地區是文化的中心。洛陽、開封等均是中古時期文化薈萃之地,河圖、洛書,學術、巫術,交融激蕩,輻射八方,蔚為大觀。
(二)程朱理學的價值取向。明清時期的家譜、族譜多為族中的文人士子所編纂,在有關族源史料稀缺的情況下,其文化價值取向關乎氏族來源。中華文化主干儒家學說至宋演化為理學,廣義上說有濂、洛、關、朔、蜀、閩和陸九淵的心學。源于河南洛陽的二程的洛學代表理學正脈。朱熹在系統整理二程遺說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性闡發,同時又博采周敦頤、張載、邵雍等部分思想精華,建立了完整的閩學體系。閩學或確切地說是朱子學在閩南學人中被尊為正統。朱子曾任職過同安主簿、漳州知州,被稱為“大儒過化之地”并漸為“海濱鄒魯”,從學緣上看,從洛學到閩學是中原文化播遷、演進的結果。學術上的道統經知識分子的傳播、轉型成為閩南族群的“族統”認同。族統是一個或多個族群對其族源的共同認知和集體記憶,在閩南具體表現為:在修纂族譜、家譜時有意識地如實記載或“矯正”族源出處,并集中地指向中州大地。明清時期這種情況普遍發生。族統在某種程度上往往超越血統,成為族群的共同歷史記憶,成為族群的精神紐帶,并長期、廣泛地產生影響。
(三)陳元光將軍的神化。北宋慶歷年間曾任漳浦縣令的呂璹《威惠廟》詩云:“當年平賊立殊勛,時不旌賢事忍聞?唐史無人修列傳,漳江有廟祀將軍。亂螢夜雜陰兵火,殺氣朝參古徑云。靈貺賽祈多響應,居民行客日云云。”傳遞出唐代漳江畔已有廟祀陳元光將軍的信息。北宋余靖《武溪集》中《宋故殿中丞知梅為陳公墓碣》文中載陳坦然曾于天圣年問(1023-1031年)任漳浦縣令,“邑西有陳將軍祠者,郡圖云:儀鳳中勛府中郎將陳元光也。年少強魂,邦人立廟享祠甚謹,日奉牲瞥無算。歲大旱,遍走群望弗雨。公(陳坦然)乃齋潔詣祠下,禱云:‘政不修者令之負,禱無驗者神之羞。國家崇祀典所以祈民福也。祀茍不應,何用神為。即錀扉與神約日,七日不雨,此門不復開,縱祠為燼矣。行未百步,霾風拔巨樹,仆于道。俗素信鬼,及是,吏民股戰神之怒。公徐日,民方嗸,何怒之為?乃援轡截樹而去。果大雨,田收皆倍。邑人刻詞以紀其異。”這一史料的發現說明北宋初漳浦即有陳將軍祠,且香火鼎盛,信眾甚多。可與南宋紹熙元年(1190)知漳的章大任所撰《威惠廟記》相印證。該記曰:“靈著順應昭烈廣濟王廟食于漳,歷年數百,祭皿未嘗一日干也……”自宋代起,被當地土著酋首襲殺而歿的陳元光將軍,屢屢“顯靈”并很快轉化為一尊官民共祀的保境安民之神。所以素信神鬼的漳人“多以為祖”,祈求庇佑。這一閩南民間習俗至明清還衍化為男性嬰幼兒認神明為義父求其護佑的民俗。民間信仰的最大特點是禳災祈福。與神明的同族、同源當是百姓的精神慰藉的需求,是重血緣、亞血緣關系的生動體現。由敬仰陳元光的開漳之功,進而崇拜陳將軍神靈,再到攀附陳元光的族源出處,便成為文化聚合的一種消除地域差異,實現天地神人和諧的獨特景觀。
經歷了1300多年的風霜雪雨的磨洗,許多歷史信息在傳遞中消隱、失真,而一些具象征意義的文化符碼卻逐漸浮現、凸顯。至遲到明清時期,光州固始在閩南族群中已成為了無可替代的文化符碼。文化符碼的浮顯與確認在某種程度上比局部的歷史真實更為重要,因為有了符碼,族群的文化基因方可遺傳,歷史記憶才不會在歲月長河中流失。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隨著閩南族群向臺灣的遷徙,“光州固始”的文化符碼被進一步放大,可以說,當今約一千八百萬祖籍閩南的臺灣同胞,原鄉為福建閩南,祖地則是河南光州固始。正因為族統觀的影響與作用,中華民族的文化聚合也在族群認同中得到不斷強化,并轉化為生生不息的民族凝聚力。
責任編輯:王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