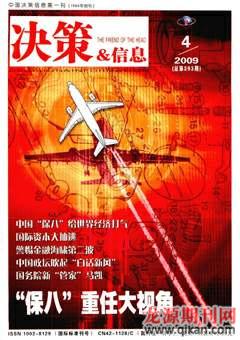國際資本大抽逃
張 銳
與發達國家一樣,新興市場國家正在承受著金融危機的侵蝕和煎熬。特別是在全球信貸緊縮的宏觀背景下,這一經濟體內國際資本的明顯回流與逆轉不僅構成了對其金融體系的重大沖擊與干擾,而且使實體經濟所需貨幣的短缺程度雪上加霜。更加嚴重的問題在于,如果這一趨勢進一步惡化,則可能形成全球范圍內的又一輪金融沖擊波。
新興市場遭遇“抽資”劫
借助良好的外部條件和寬松的國內政策,新興市場國家在2002~2007年世界經濟的景氣周期中敞開大門接納了滾滾而來的國際資本,從而造就了長達5年的資本流入盛景。資料表明,截止到2007年底,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流入總量占到了GDP的7.5%,5年時間流入規模翻了5倍,并且這一繁榮的景象一直延續到2008年年中。然而,金融危機的發酵和肆虐不僅打亂了世界經濟成長的步伐,而且也快速地更改了國際資本的流動方向——曾經高歌踏入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資本正在大規模地掉頭回撤,并可能在整個2009年愈演愈烈。
一般而言,國際資本流動主要有直接投資(FDI)、證券投資(包括股本證券和債務證券)和國際信貸(包括私人借貸、官方借貸)。目前三項指標均顯示新興市場國家里國際資本運動的不樂觀。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預測,新興市場經濟體的FDI將在2009年減少40%,而據世界銀行預計,2009年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流入規模將降至5300億美元左右,這一數字將是2007年的一半。更有甚者,國際金融協會預計,新興經濟體2009年僅能吸引到1650億美元的資本,這一水平僅相當于2007年的1/5,其中流向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投資預計將比2007年減少82%。
歐洲和亞洲新興市場板塊可能成為資本流出的“重災區”。由于歐洲新興市場國家的外部資本需求占到了新興世界外資需求總額的近50%,而提供資金供給多為西方銀行,在如今這些金融機構紛紛“班資回朝”的沖擊下,歐洲新興經濟體遭遇了空前的“抽資”之苦。由全球最大銀行組成的行業組織國際財務協會指出,2009年流入歐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預計僅為300億美元,大大低于2008年的2540億美元和2007年的3930億美元。
相比于歐洲地區而言,亞洲新興經濟體的FDI流出速度比較遲緩,但證券資本的外逃卻顯得高度活躍。據對沖基金研究公司Eureka hedge的數據顯示,在整個2008年中,已經有93億美元的對沖資金流出亞洲(除日本之外)市場,外資凈賣出亞洲證券規模達277億美元,創出了自2001年有此數據以來的新高,流出規模甚至高于2001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及2003年非典期間的流出規模。而據匯豐銀行對各大基金公司資金流向進行的調查顯示,亞太區(不包括日本)的股票基金2008年錄得的資金凈流出相當于代客管理股票基金總額的31%。
俄羅斯和韓國成為了亞歐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出的典型國家。據俄央行的資料,2008年俄羅斯僅外國私人資本凈流出額就高達1299億美元,而且這種情況在2009年繼續存在,預計2009年俄資本凈流出額將達到1000~1100億美元。無獨有偶,據韓國證券交易所提供的數據,2008年海外投資者持拋售韓國股票1000億美元之多,刷新了累計拋售額歷史的最高記錄,海外國投資者在韓國市價總額中所占比重創下了2001年交易所開始統計相關數據以來的最低值。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全球信貸高度緊縮的金融生態中,國際資本尤其是信貸資本的撤離具有 “羊群效應”。以英國為例,由于受到愛爾蘭和冰島銀行撤出的沖擊,英國銀行體系放貸能力大大削弱,在此情況下,英國政府決定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重點轉向國內貸款,并正在準備撤出亞洲等海外市場。顯然,這種“羊群效應”的傳遞將使得全球范圍內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逆轉愈演愈烈。
觀察發現,目前從新興經濟體流出的國際資本主要進入到了三大領域:很大一部分回到了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以償還貸款;一部分被投資者用于購買美元資產以避險保值;還有一部分短期資金進入到了大宗商品期貨市場。就在一部分資金進入到美元資產市場、購買美國國債的同時,另有一部分短期游資不甘于微薄利潤,在從金融衍生品市場退出之后,再度進入到了期貨市場。前者造就了過去數月外匯市場上的美元牛市,后者則在國際市場不斷推高部分期貨品種的價格。
信貸緊縮的并發癥
金融危機產生的嚴重后果之一就是全球流動性收縮,由于西方銀行風險厭惡程度在金融危機中得到了無限的強化和放大,導致金融機構間拆借利率與日俱增,并迅速回籠投向市場的原有貨幣,正常的貨幣供給渠道快速收窄,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由此出現了流動性嚴重不足的局面。作為貨幣市場的另一面,流動性緊縮必然導致國際資本的回流。這種回流表現為三種狀態:
第一,“緊急救助式”回流。受次貸危機的沖擊,西方市場各類金融機構出現了空前虧損,這些機構由于需要作出巨額撇帳,只有 “舍車保帥”,出售包括在新興經濟體投資的各類資產,以挽救國內市場,而且只要未來金融經濟形勢方向仍不明確,這類資產的甩賣或延續將加劇。
第二,“財政擴張式”回流。為了應對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債券,結果必然對新興經濟體信貸市場融資形成“擠出效應”的同時吸引部分資本回撤。資料顯示,2009年發達國家將發行3萬億美元的政府債券,規模為去年的4倍,其中僅美國就將發行約2萬億美元的政府債券。在美國等國銀行信貸收縮、私人投資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其國內國債投資力量似乎有限,國際資本成為其資金供給的主要來源。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美國國債一直維持“AAA”的級別,且金融危機中的投資者的風險偏好發生了劇烈轉變,即不再片面關注投資工具的比較收益,而是更多地關注債券的安全邊際收益,美國國債自然就成為了首選。與此相反,出于對融資環境和國際原材料(新興市場經濟體主要以出口原材料為主)價格持續下跌的憂慮,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對新興市場國家債券的信用評級,其中,拉美國家政府債券級別被穆迪公司調低至8年來最底,俄羅斯和韓國等國國家債券信用等級被標準普爾調至10年來最低。由此引發了國際資本對新興市場國家債券的大規模拋售。
第三,“杠桿弱化式回流”。對沖基金杠桿融資往往是新興市場經濟體資金供給的重要來源之一。但在信貸收縮和融資環境趨緊的市場中,對沖基金特別是固定收益方面的對沖基金的杠桿水平日趨降低,杠桿規模也逐漸變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分析報告指出,2008亞洲市場中對沖基金的平均杠桿已下降到1.4倍,而2007年為1.7倍。因此,在2008年中,活躍于亞洲國家的對沖基金共有71只對沖基金破產,而2007年全球對沖基金破產數量僅為46只。在市場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和“去杠桿化”倍顯疲弱的狀態下,對沖基金最終選擇的只能是逃亡和撤資。
金融資產價格相悖運行
不同國家金融資產價格的起落狀況對于資本的運動方向具有最直接的誘導力,尤其是在現代開放式金融體系中,貨幣匯率和股票價格構成了資本跨境流動的重要風向標,特別是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這兩種力量的作用格外明顯。
一方面,美元的加速升值形成對國際資本的“眼球效應”。
美元匯率變化是國際資本流動的重要風向標。從歷史上看,美元匯率每次重大的變化都對應著國際資本流動的大幅變化。自 2001年以來,美元對幾乎所有主要貨幣都在穩步貶值,并持續推動了大量資金流向新興市場。但從去年8月之后,美元扶搖直上,并從前期最低點彈升了24%。由于美元持續貶值,其從低位開始攀升本身就顯示出了投資的“洼地效應”;更加重要的在于,美聯儲已將基準利率降至了0至0.25%的歷史最低區間,美元升值的“預期效應”昭然若揭。同時,由于美國政府長期執行美元弱勢政策,美國貿易逆差如今正顯著得到解決,在外部失衡狀況得到改善之后,市場對美元信心開始增強,從而推動美元升值。
與美元升值相反,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匯率卻日漸走軟。彭博資訊跟蹤的26個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匯率變動狀況表明,這些國家的貨幣相對于美元的升值幅度其實從2007年起就開始下降。其中2007年下降了8.2%,2008年下降了9.3%。由于長達5年的升值牛市,新興市場貨幣已經在國際資本眼中出現了“見頂效應”,“去美元化”現象日漸明顯。不僅如此,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升值時段正是食品、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飚漲之際,由于食品和能源在新興市場國家價格指數構成中所占比重大,由此在全球投資者眼中形成了強烈的“通脹效應”,相應地,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的貶值預期也被加倍放大。一方是美元的升值和樂觀預期,一方是新興市場貨幣的貶值和悲觀判斷,在兩類貨幣匯率明顯失衡的情況下,國際資本棄新興市場貨幣而取成熟市場貨幣也就順理成章了。
另一方面,股票價格的強弱分野對投資者產生“加框效應”。
盡管在金融危機中全球股票市場哀鴻遍野,但與新興市場國家相比,發達經濟體的股市卻顯得相對堅挺。觀察發現,在2008年全球股市跌幅榜上,排在前5位的國家都來自新興市場陣營。其中,歐洲新興市場國家冰島OMXI15指數以全年94.49%的跌幅排名第一,俄羅斯以76%的跌幅排名第二,緊追其后的越南,全年最深幅度下跳達74.29%,而“金磚四國”中的另外三國——中國、印度和巴西,股市全年跌幅都超過40%甚至高達60%。與此相對照,盡管美國股指遭遇了1931年大蕭條時期以來最大跌幅,但2008年美國標普只跌了39.35%,英、法、德三大股市的跌幅都在四成以內。對投資者而言,如此顯著的反差自然就形成了歐美股市安全邊際和收益邊際的“加框效應”,撤出新興市場而轉投歐美股市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新興市場國家的顫抖
應當承認,國際資本對新興市場經濟體持續5年的大規模介入不僅培植出了當地日趨活躍的金融肌體,也打造出了經濟增長的繁榮大勢。正是如此,當今金融資本紛紛從新興市場體撒腿撤離時,其對相應國家金融和經濟造成的壓力和變數就非同尋常。
第一,誘發資產價格的巨幅抽搐,并釀造泡沫破滅風險。
前幾年國際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無疑促發了該地區經濟的空前增長,但也同時驅高了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價格,并積聚了相當厚重的價格泡沫,而現在新興市場經濟發生逆轉、大量國際資本紛紛出逃時,必然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并進而釀造區域性金融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盡皆如此。專家指出,如果國際資本抽逃新興市場的態勢得不到有效控制,韓國、越南、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可能重蹈金融危機的覆轍。
第二,驅動新興經濟體的貨幣貶值,深度沖擊國家金融秩序。
不論國際資本流動采取銀行信貸還是采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形式,都涉及貨幣的兌換,從而對外匯市場產生影響。在國際資本大量流出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必將發生大幅貶值。而一國當局為了挽救本幣幣值,中央銀行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動用外匯儲備買進本國貨幣。由于中央銀行使用外匯買進本幣,該國貨幣供給量在短期內勢必出現收縮,從而導致本國貨幣利率的上升,進而對該國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產生抑制作用。以俄羅斯為例,由于該國內外的銀行都面臨現金短缺的困境,國際資本開始大規模做空盧布,盧布走勢在過去幾個月里急劇逆轉,盧布兌美元創出了11年低點。而自去年8月以來,俄羅斯花出了巨額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以上干預匯市,俄曾有約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現在還剩下約3850億美元;與此同時,俄羅斯央行也上調基準利率。盡管如此,至今仍然沒有阻止盧布的跌勢。專家認為,如果盧布繼續下跌,必然引起進口價格的上漲,并導致消費的急劇萎縮,同時政府調控經濟的機會成本將大大增加。
第三,打擊新興市場國家的產業與福利。
如前所述,國際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幾乎是與該經濟體大宗初級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同時發生的。初級產品牛市所帶來的收益也把這些國家推向了“荷蘭病”的詛咒:欣欣向榮的初級產品及其相關產業汲取了過多的資本、人力等資源,以至于制造業等部門相對萎縮,乃至出現絕對萎縮;初級產品出口迅猛增長所造成的本幣升值進一步重創其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如今,在國際資本競相流出新興市場國家時,制造業和服務業所需要的正常資金供給被打斷,其萎縮程度進一步加劇。另外,新興市場最近幾年主要通過經常項目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先前一部分已經又回流到美國,主要購買了美國的債券,從而為美國的貿易逆差提供了融資。這種被稱為“斯蒂格利茨怪圈”的資本循環在國際資本如今加大流出新興市場的條件中被進一步強化:新興市場國家在以較高的成本從發達國家引進的過剩資本,又以購買美國國債等低收益形式和資本獲利回吐的被剝奪方式倒流回去。在這個過程中,新興市場國家損失了大量的福利。
第四,收縮新興市場的還債能力,并可能引爆債務危機。
由于全球信貸的嚴重緊縮,依賴跨境融資的新興經濟體金融機構壓力增大,而因為信用等級的被低估,這些國家利用信貸市場融資的機會被邊緣化。在國家資本陣營紛紛撤退的打擊下,新興市場許多國家原本脆弱的國際還款能力大大削弱。瑞銀集團的研究表明,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克羅地亞、烏克蘭、匈牙利等歐洲新興經濟體以及阿根廷、巴基斯坦外匯儲備較少的國家,其外債違約風險很高。而荷蘭國際集團的數據顯示,新興市場的政府和企業2009年需要償還約6.865萬億美元的債務,其中包括債券、貸款、利息和貿易融資。在失去了穩定資金供給的情況下,這些債務的償還前景無疑充滿懸念。
屏蔽“金融重商主義”
縱橫捭闔于全球各個經濟角落的國際金融資本永遠不會駐足于一個地方。伴隨著未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復蘇以及市場投資價值的再現,國際資本也許還會回流,但正是這種大出大進的資本運動方式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和金融市場的風險。另外,美國既然能夠通過美元貶值釋放貿易逆差的壓力,那么他也完全可以通過驅動美元升值籠絡國際資本的回流。這種被2009年達沃斯論壇上諸國國家領袖嘲諷為“金融重商主義”的做法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警覺。因此,無論是試圖減輕國際資本流動的風險還是消除金融貿易保護主義,對于新興市場國際資本的異動不可小覷。
第一,強化IMF的作用。在全球經濟下行的條件下,為了更好地振興本國經濟,主動將外在的金融勢力向國內收縮,以便更好地為國內經濟運行服務,降低信貸短缺的危害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不約而同的選擇。阻止這種以鄰為壑的行為僅靠新興市場國與發達經濟體的對話與協商遠遠不夠,必須充分發揮IMF的作用。可以考慮讓IMF收緊并擴大對其185個成員國的審查,或者IMF可以與金融穩定論壇協作進行調查,以便充分釋放IMF裁斷金融領域糾紛的能量。
第二,改革與修補全球金融監管體系。研究表明,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西方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新興市場國家的控制之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發達國家的利率每增長1%,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3%。伴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漸恢復,西方國家將進入新一輪的利率上升通道,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可能還會更大規模地流出。為此必須通過金融監管,包括對一些金融機構的跨境交易行為進行限制,以避免未來發生金融危機;通過數量控制——規定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稅收(如交易稅)或類似稅收(不給國外借款的儲備金支付利息)的辦法,強化對資本流動的管制。
第三,阻止保護主義政策。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范圍尤其是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蠢蠢欲動,其基本手法是強制資本投資本國產業和采購本國產品。貿易保護主義必須依賴于金融保護主義,即只有獲得充足的流動性支持,投資與售買的“本國化”政策才能實現。顯然,最大程度消除貿易保護主義是保證全球資本有序流動和金融市場穩定的基本前提。
第四,加強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市場的力量遠遠超過了國家,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既要求國際范圍內國家之間加強資本流動管理政策的協調,更要求新興市場國在地區范圍內加強聯合。尤其是新興市場資本流出主要通過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地下錢莊等渠道流出,而對于非法資本流出渠道,惟獨加強合作才能收到控制的效果。
第五,推動經濟的迅速康復與上行。盡管目前新興經濟體貨幣財政當局掌握了近5萬億美元的資金,一定程度可以減緩國際資本流出中的貨幣供給壓力,但卻并不能抗逆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沖擊力。按照比較經濟學原理,在經濟危機之后,新興市場經濟恢復的速度要慢于發達經濟體,前者資本流出的風險會隨之加劇。為此,新興市場國家必須通過超常的反周期貨幣與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經濟加速復蘇,盡可能培植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
中國可以說“不”
作為新興市場的重要成員之一,中國同樣明顯存在著國際資本流出的事實,這種判斷基于以下幾項指標變動:(1)國際金融資本大量拋售在華資產。自去年年底至今,已有摩根士丹利出售了上海100多套酒店式服務公寓,瑞士銀行減持了33.78億股中國銀行H股,美國銀行拋售了56億股中國建設銀行H股,摩根大通分別減持中國石化、中國鋁業和招商銀行的港股股份,總涉資達8.75億港元。(2)利用外資額度減少。自2008年10月以來,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連續同比負增長,當年12月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562家,同比下降25.7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5.73%。(3)外匯儲備增幅下降。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增加4178億美元,同比少增441億美元。而從去年10月開始,外儲不升反降,預計2009年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或繼續縮水。
不過,國際資本的流出并不會給中國造成太大的影響,中國既不會出現如同俄羅斯那樣的貨幣貶值壓力,更不會發生如同越南那樣的金融危機。作出這種樂觀判識的理由在于:(1)中國資本項目并未完全放開,監管當局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控制國際資本的流出節奏。(2)中國具有高達1.9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龐大的“蓄水池”足以實現對匯率市場的靈活調控。(3)中國有高達2萬億美元的儲蓄,市場流動性充足,資金供給充分。(4)中國的資本流入主要是FDI,FDI的性質決定其投資期限更為長期,更穩定,短期集中流出存在困難。(5)中國經濟仍處于高速增長階段,資本回報率超過所有國家。
但是,國際資本流出中國所產生的隱憂也不可忽視。一方面,我國境內存在著高達1.75萬億美元的國際熱錢,如果其中1萬億美元在未來短期內集中離境,就相當于中國短期內增加了以7萬億元人民幣計的股票、樓房等資本品的供應,股價、樓價和中國企業的資產價格將經受暴跌的風險。另一方面,中國持有6500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國際資本驅動美國國債泡沫的破滅將對中國形成最大考驗。
因此,對于國際資本流出中國這一新現象,應高度重視,積極應對。宏微觀政策應當側重于:(1)保持經濟增長的相對穩定以使得資本流動可持續;(2)完善監管體系,強化對外匯指定銀行和外貿企業的業務監管力度,加強結售匯管理,嚴防資本混入經常項目外逃。(3)構造全口徑外匯收支的及時預警機制,研究制訂防范發生資金流動逆轉的應急預案以及相應的外匯檢查應急預案,防止異常資金繞道規避監管。(4)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最好控制在1%~2%之間。
在弱化和控制美國國債風險方面,可以通過一攬子組合政策達到減少美國國債的持有量,具體做法是:(1)增加貿易伙伴國之間出口與進口商品的互換。(2)通過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減少國際貿易中美元的結算和支付。(3)通過提供人民幣貸款并讓對方用人民幣向中國購買美元的方式向亞洲和非洲等地區出現國際支付困難并需要中國援助的國家提供資金援助。(4)適當增加黃金、石油和礦產品等硬商品或戰略資源的國家儲備。
(作者: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