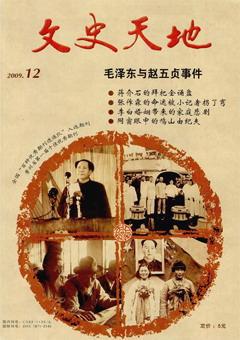蘇軾與經濟危機
馬化福
稍有一點文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蘇軾蘇東坡是我國北宋時一位偉大的文學藝術家,是一位全才,詩文詞賦無所不精,音樂書畫無所不能。他的詩民間都有“韓潮蘇海”的說法,意思是說:韓愈的詩如錢塘潮水,蘇東坡的詩像大海一樣寬廣。他的文正如他自己所說:“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揮灑自如,特別是文賦,南宋的王炎評他的赤壁二賦是“賦到此翁無人”,至于詞,蘇軾開創了豪放一派,《念奴嬌·赤壁懷古》簡直可以說雄視千古,他精通音律,能制詞牌,是音樂家;他擅丹青,是畫家;他的《黃州寒食帖》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是大書法家。但他在處理經濟危機的一些措施卻鮮為人知,現舉幾例以饗讀者。
北宋元豐二年(1079)正在湖州任太守的蘇軾因“烏臺詩案”被捕下獄,那年八月十八日被押送至京城汴梁,經過四個多月的反復審訊,至十二月二十七日,神宗皇帝終于降下圣旨,將蘇軾奪去官職,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停發官俸,不得簽書公事。十二月二十九日文書下達,正月初一便得起程。于是就在舉國歡慶的元豐三年(1080)大年初一起程。蘇軾由長子蘇邁陪同,在御史臺差人押解下趕赴黃州,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蘇軾父子終于到達黃州。由于蘇軾是犯官身份,沒有官舍居住,初到黃州的蘇軾只得暫時借住在一座山間舊寺定惠院里。兩個月后,蘇軾的妻子王閏之(續弦,已故夫人王弗的堂妹),丫環王朝云,次子蘇適,三子蘇過,在被貶為筠州(今江西高安)監酒的弟弟蘇轍的護送下也到了黃州。小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蘇家這么多人,對文名遠播的蘇軾十分景仰的黃州太守陳君式把蘇氏一家安頓到長江岸邊的一個水驛臨皋亭。住處暫時是有了,但因為官俸停發,蘇軾在職時是個清官,家中并無積蓄,所以一大家人的吃飯頓時成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不過蘇軾畢竟是蘇軾,在這生死存亡的嚴重危機面前,蘇軾不等,不靠,不乞,不要,而是采取了兩項克服時艱的措施。
蘇軾的第一個措施是量入為出。他把夫人王閏之離京前變賣的些許家產換成銅錢,每月初他取出四千五百錢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掛在住所屋梁的三十顆鐵釘上,每天早上用畫叉挑下一串做當天的生活費,然后將畫叉藏起。據蘇軾說,當時黃州米價約二十錢一斗,他家日用米約二斗,每天需要米錢約三四十錢,剩下一百余錢用來買菜買魚買肉也可以了。當日倘有盈余,則丟進另行準備的一個大竹筒里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或招待賓客。這對黃州一般百姓來說,小日子還算可以的,但對蘇軾來說,以前有官俸祿米,賓來朋往,花錢如流水,這樣緊巴巴的日子那可真是“痛自節儉”了。
蘇軾的第二個措施是生產自救,自食其力。在黃州安頓下來后,蘇軾就向黃州太守請求能劃給一塊無主地給他耕種,經反復交涉,繼任太守徐君猷將黃州城東緩坡上一塊營防廢地劃給了他。那哪是什么“地”呀,那是一塊荊棘瓦礫之場。蘇軾別無選擇,于是帶領全家老小清除瓦礫,刈割荊棘,深挖細整,終于整理出五十畝田園,又因地制宜冬種麥,夏種稻,還種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春食苗,夏食葉,秋食果,冬食根”,全天然無公害綠色食品,他還自我安慰,“怡然享受著,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白居易在四川忠州刺史任上,曾在城東緩坡上種花栽樹,公事之余,在花叢樹影間追尋往事,感嘆今生,稱該地為東坡。蘇軾景仰白居易的詩文人品,感慨自己的坎坷經歷,于是也將這塊田園戲稱為“東坡”,元豐三年冬,蘇軾在坡地廢基上蓋起了五間房屋,房屋竣工時下了一場大雪,蘇軾在居中明間堂舍四壁畫上雪景,就將這房子取名為“東坡雪堂”。白居易晚年居香山,遂自號“香山居士”,蘇軾住“東坡雪堂”,食東坡田園產的糧食蔬菜,于是也學著白居易,自號“東坡居士”。從此,蘇軾在這里,煮“東坡羹”,做“東坡肉”,釀“東坡酒”,撰“東坡長短句“。東坡居士名揚天下,民間甚至有不少人只知蘇東坡而不知他就是蘇軾。
蘇軾就這樣憑著自己的節儉和勤勞度過了黃州四年的經濟危機,復職后,他還憑著自己的超人的智慧和才華,幫助寒門學子及小企業主度過了經濟危機。
元佑四年(1089)春,太皇太后高氏降旨,任命蘇軾為杭州知府。據說,那年秋天,杭州的稅務官抓來一個欺詐漏稅的犯人交給蘇大人發落,那時,理刑斷案是政府負責人即知府的本份職責。待人犯及贓物被帶至公堂,蘇大人一看人犯舉手投足都不像坑蒙拐騙的奸猾之徒,穿著打扮倒像一個鄉村學究,贓物是兩大包行李,人犯稱是麻紗。行李包上收件人姓名官銜是“京師竹竿巷蘇侍郎收”,發件人姓名官銜是“翰林學士知制浩蘇軾寄”。乍一看真像是假冒蘇氏兄弟名義的偷稅案。蘇軾長臉一沉,不怒自威,厲聲問道:“你是何人,竟敢冒用本官名義干不法勾當?”跪在堂下的人犯這才明白,端坐大堂之上的大胡子才是真正的翰林學士知制浩蘇軾,用現在的話說是李鬼撞上李逵了,知道不說真話難逃嚴懲,只好一五一十地說明原委:原來此人是南劍州(今福建南平)人,名叫吳味道,因要進京應試,只因家中貧寒,沒有盤纏路費,鄉鄰見其可憐,湊些錢給他可還不夠。這位書生就用鄉鄰門湊的錢買了些當地土產建陽紗帶到東京變賣,以作在京城近一年的花銷。可是這些建陽紗如果作為商品運輸,一路上重重關卡,賦稅繁重,如按規矩繳納則所剩無幾。他素知蘇氏兄弟不止有文名,還有善心,于是便盜用他倆名銜,以便逃稅。若真被查獲,同是文人的蘇氏兄弟可能會惺惺相惜,法外施恩。誰知這名人效應也真管用,這吳書生的行李從福建到浙江杭州還真像上了綠色通道,一路放行,無人收稅。由于信息閉塞,吳味道卻不知道蘇軾已出任杭州知府,而杭州的稅務官又太認真,致使這吳味道一下就撞到槍口上了。蘇軾聽罷,(心想窮苦人家孩子讀書讀到這樣不容易)既贊賞吳書生的經濟頭腦,又同情寒門學子的困難處境,更為寒門學子的眾鄉鄰們的一番愛心所感動,決定也幫幫這位寒門學子,讓他好度過危機。聽完敘述就命人揭去行李上的舊封,親筆寫上己弟地址、官銜、姓名,落款處再寫上自己新銜新址,并附短信一封,叫吳味道到京后交給蘇轍,讓蘇轍予以關照。有了蘇軾的親筆題款,這樣的好結局使吳味道驚喜莫名。接下來吳味道更是一帆風順到了京城賣了建陽紗,第二年秋天還真考上了進士。這個吳書生真可謂是“時來風送滕王閣”。
對讀書人是這樣,對小企業主,蘇軾也是能幫即幫,讓其度過危機。
就在蘇軾任杭州知府第二年夏天,一場經濟官司又擺在蘇大人面前。原告是綢緞商,雖是商人卻沒有奸猾習氣,也不像欺行霸市之徒。狀告被告一年前賒去價值兩萬錢的一批綢緞,牙齒就是合同,三個月后本息一起還清,可過了一年,被告分文未付,只得對簿公堂,不求利息只求本金。蘇軾聽原告所說也不是得理不讓人,便叫被告說說欠錢不還的原因。被告是個青年人,也像個厚道人,他承認原告說的事實。他是個做綢扇的,算是小企業主,他說一年前從原告購來的價值兩萬錢的
綢緞全做了團扇,只是前一年大旱,造成饑荒,人們性命尚且不保,哪有錢來買扇子。今年又是陰雨連綿,涼爽異常,人們無需買扇消暑,扇子還是賣不掉,加上父親病故,一家妻兒老小三餐都難以為繼,實在沒錢償還積欠。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原告說的是天理,生意難做,生存難繼,被告說的是實情。可惜,那時封建國家沒有銀行能貸款給企業主,幫企業主擺脫困境,更沒有鼓勵消費,擴大內需的措施和政策。旱澇相繼,災荒頻頻,民生多艱。小業主度日尚且如此艱難,無業無藝的草根百姓日子一定更是難上加難。愛民如子的知府蘇大人在天理和實情之間很有些犯難,在大堂之上踱起步來,苦苦思索,想找一個能解決問題的良方妙策。他猛的一抬頭,忽然看見公堂上懸掛的自寫的“廉明方正”四字榜書,心里頓然有了主意,平聲靜氣地問扇商道:“你靠做團扇為生,扇子做得怎樣?”被告道:“我是祖傳手藝,全杭州城都有名,若不是天災,湖州、蘇州、嘉興、寧波都有商人來進我的貨。”蘇知府便說道:“拿二三十把扇子來我看看。”年輕的扇商回去抱來一堆扇子。知府大人一看,果然選料精良,做工精細,不止是驅暑良具,還是可觀賞的雅致之物,蘇軾不看便罷,一看興致頓起,欣然拿起案上湖州名筆,蘸上下人磨好的濃墨,在扇上圈圈點點,涂涂抹抹,遠山近水,茂林修竹,假山怪石,花鳥蟲魚,扇子上頓時出現了各種悅目圖畫,然后知府蘇大人還題上幾句或古或今的詩詞名句,最后題上自己名號,要知道蘇軾的書法在大宋朝可是第一名家,有蘇黃米蔡之評價排列。他的楷書肥厚豐腴但不臃腫,飄逸清秀但不浮滑,行書前面已提到“黃州寒食帖”是天下第三,所以不論是書還是畫,都是傳世珍品。書寫完畢,大人把筆一放,對扇商說:“你去把這些扇子賣了,一千錢一把,用以還債吧。”堂上原被告都頓時明白,蘇軾蘇大人詩文書畫名滿天下,他的真跡墨寶誰不愿珍藏。年輕的扇商抱起扇子出了知府衙門,片刻工夫就滿頭大汗氣喘吁吁空手跑了回來,稟告知府大人,扇子被一搶而空,一千錢一把一文不少,不但還清了原告的兩萬錢陳賬,還有一些余資可維持生計。這位小業主的經濟危機就這樣被蘇軾用他的驚人才華輕輕松松地化解了。
上面的幾件事只是蘇軾為自己為別人應付經濟危機的小作為,他在杭州知府任上解決饑荒才是這位文人政治家應對經濟危機的手筆。元佑四年(1089)夏,蘇軾出任杭州知府,還在上任途中,他就聽說杭州百姓正飽受干旱煎熬,糧食大幅減收,糧價如錢塘潮水陡漲不停。蘇太守七月初抵杭州時,米價才六十錢一斗,才到十一月仲冬時節杭州城米價已是九十錢一斗,因此上任頭一件大事便是救災。蘇軾上任伊始,就開始謀劃年冬年春的救災工作,他上書朝廷要求從上運朝廷的漕糧中留下二十萬石救災。經過反復申奏,朝廷終于同意了蘇軾的要求,這些糧食他也不用來設棚施粥,而是在十二月就投放市場,平抑糧價。蘇軾之所以這么做,也是根據杭州的經濟情況決定的。饑饉之年,杭州人雖然缺糧,但不缺錢,只要選好時機,有糧賣給饑民,饑民有糧可買,糧價立馬就降下來了,到元佑五年正月,糧價就降到了七十五錢一斗,接近蘇軾頭年七月初到杭州時的水平,老百姓用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的糧價,可以到官倉和米商那里買到度荒的糧食。朝廷不但省去了漕糧來回數萬貫的運費,還回收了十五六萬貫糧錢,官民兩利,皆大歡喜。元佑四年冬至五年春的這場嚴重的饑饉就這樣有驚無險的被蘇軾解決了,當然這些措施斷了貪官和糧商的財路,蘇軾難免也有結怨。但不管怎樣,這是蘇軾蘇東坡三十多年的為官生涯中幾項大的民生工程,只因蘇軾在文學上的大師光環太耀眼奪目了,這些本來值得大書特書的德政卻少有人知了。
(作者單位:安徽省六安市順河店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