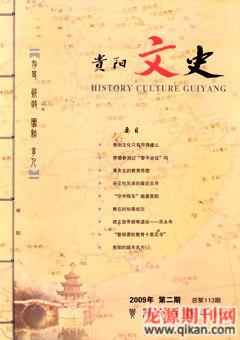學校易名念先賢 身世浮沉志不移
吳照恩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沿海地區學校內遷。大夏大學原設立在上海梵皇渡(今華東師范大學)。校長王伯群,系貴州興義人(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學校內遷時,他即決定將大夏大學遷到貴陽。并開設文學院、理學院、法商學院、教育學院及師范專修科。
當時貴陽各中學多疏散在鄉下。伯群校長考慮到,大夏教育學院及師范專科畢業生需要有個實習園地,同時也可為大學部輸送生源。遂于1938年6月,增設了大夏大學附中。
最初附中男子部設在講武堂。女子部租用樂群學校校址。1939年秋,南寧失守。原大夏大學校友在南寧創立的大夏中學部分師生遷到貴陽。學生分別插入附中各班。為節省開支,又將男女兩部合并至講武堂。全稱仍為“大夏大學附屬中學”。
時局艱難辦附中
三苦精神創聲譽
當時因避日機轟炸,貴陽城內各中學都疏散在鄉下,尚未遷回。附中在城內成了唯一的一所中學。所以招生時報考的學生非常踴躍。錄取新生都按五比一的比例。授課老師都是大學部的教授、講師以及大學部畢業的學生。本著苦干、苦教、苦學的“三苦”精神來辦學。又依靠大學部的圖書及物理、化學以及生物實驗室的優越條件,擴展和深化了學生各方面的知識。故教學質量較高。每年參加全省中學會考,無論個人或集體都獲得過優良的成績。
王校長為了照顧淪陷區來的流亡學生以及一些家庭貧困的青年,采用免費就讀、獎學金及特殊補助等種種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學習和生活問題。學生大受感動,養成良好的學習風氣,熱愛學校,在社會活動中常為學校爭得榮譽。貴陽市組織召開的抗日宣傳千人大合唱,以附中大夏合唱團為領唱,唱響了貴陽。合唱團還配合貴州省政府軍樂隊在貴陽舉辦了大型音樂會,其中包含管弦樂隊的演出,在貴陽市首開先河。凡貴陽市舉辦的中學生籃球、足球比賽,附中必獲冠軍。
王校長每年“六·一”校慶都要在附中組織檢閱式,他親自主持檢閱。當王校長出現在檢閱臺時,全場歡呼,掌聲如雷,那喜慶熱烈的場景,讓人終生難忘。
我們在1944年開辦了商科,惜乎大學部的校舍限制,我們無法擴大招生。王校長策劃另建校舍。通過努力,已獲貴陽市政府撥給次南門外豬拱坡(即現在的省總工會一帶)約兩百畝的荒墳地,準備開始興建。不料黔南事變后,校長因操勞
過度,病逝于重慶。未能
實現這個計劃。
大夏大學遷黔后使用的講武堂校舍,是貴州省政府撥給大夏暫時使用的。1944年因黔南事變。大夏大學再遷赤水,貴陽市政府立即收回講武堂校舍,并指定作難民收容所。此時由歐元懷先生繼任校長。大學部面臨種種困難,無暇顧及附中。原來附中經費全靠學雜費收入。不敷之時,都是靠王校長設法解決。現在王校長去世了,附中失去了主要的精神支柱和經濟支柱,面臨停辦之勢。
我自1938年從大夏大學畢業,蒙王校長親自選用留校,到附中工作已六七年。時任附中部主任之職。校長臨行時又特別囑咐過我:“大學部遷赤水,附中部留貴陽。你要盡力保護好這個學校,繼續把它辦下去。”而現在,一旦停辦,無論是面對校長的重托,還是個人對大夏的感情,都是難以接受的。
白手起家辦夏中
各方支援打基礎
當時大學部總務長竇覺蒼先生未隨大學部遷赤水。我特詣請指示。先生要我先找大夏大學校友會理事長何縱炎先生商量。(何是大夏大學第一期畢業生,大夏大學最初在上海籌建時,還是他去找到伯群校長贊助的。)我找到了何先生。他問我:“你想怎么辦?”我說:“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個存放校具的地方。也就是作為校址的校舍;其次是籌措辦學經費。這兩個問題,經我反復考慮,倒有兩個辦法。但是否能行,只有去試試看。”何立即說:“我支持你,你盡管去辦,需要我的時候,給我講一聲就是。”我又告訴他:“大學部遷走后,附中這個名字已不能再用,需要改名。我想改為大夏中學。但按教育部規定,私立學校要先成立校董會,由校董會報請立案。這個工作只有請先生出面來主持了。我來找先生之前。已先找過竇先生,他要我先找你談一下有關的情況。組織校董會的事,先生可否找他商量一下?”縱炎先生慨然答應了。我隨即將情況轉告了竇先生,以后組建校董會就由二位先生去商辦了。
因我原在平剛先生(老同盟會員,曾任孫中山先生秘書)創辦的樂群學校工作過。與平老比較熟。我去拜會他,說:“樂群中學停辦后。校舍租給一些私人居住。貴陽疏散的時候,這些人都跑光了。現在房子空著,若不設法利用,恐怕難民擠占進來就會遭到損壞。”平剛先生微笑著,似乎已看穿我的意圖。他說:“那你說怎么辦?”我接著說:“現在大夏大學遷赤水,附中失去了校舍,正面臨困難。我看不如由附中向樂群租用校舍,其所交租金還可補貼樂群小學的開支,”平先生很爽快地回答說:“好的,就這樣辦。你就連樂群小學一起負責吧。”平剛先生對我這樣高度的信任和支持。使我非常感動。連連向他道謝。校舍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緊接著我著手解決經費問題。
其時,我同上誨銀行姚經理比較熟,又是鄰居。我還知道大夏大學在上海建校時曾得到該行總經理陳光普先生的贊助。我去找姚經理談:“我想向你們銀行借點錢作辦學經費,以后我用學生學雜費來償還,你看可不可以幫我這個忙?”姚經理也很爽快,當即表態:“可以,我們銀行為你收學雜費就是。”學校的經費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我把解決以上問題的經過報告給何縱炎先生。他非常高興。連連稱贊我說:“你很有辦法”何還告訴我:“楊森省主席的夫人汪德芬是大夏校友。我通過她邀請楊主席任校董會名譽董事長,主席已答應了。汪德芬還準備將主席的子女約五,六個送進大夏念書,我給她寫了介紹信,可能她會來找你。另外傅啟學先生是現任教育廳長,又曾任大夏大學訓導長,他也答應任校董。杜惕生是何總(何應欽)的秘書長,現賦閑在家。請他任校董,他也答應了。楊秋帆你是知道的。另外還找了個商界的劉熙乙。再加上歐元懷校長,共七個人。你去行文呈報備案。”最后確定董事會成員組成如下:
名譽董事長:楊森
董事長:何縱炎
董事:歐元懷傅啟學竇覺蒼楊秋帆杜陽生劉熙乙
大事已定,遂積極組織搬遷,籌備招生。附中正式改名為大夏中學。于1945年3月1日按時開學上課。6月1日舉辦校慶時,省主席楊森還親自蒞臨會場講話,這在當時是對大夏中學很有力的支持。
在此我要特別提到的是,大學部遷赤水后,貴陽市政府收回講武堂校舍作難民收容所。一時大量難民紛紛涌入校舍。時值數
九寒天,難民們為了取暖和做飯,把教室門窗拆下,把課桌凳砍了當柴火燒。此時保護校具就成為首要任務。由于師生員工均已疏散,我一人孤掌難鳴。正焦慮時,碰巧附中的毛克昌校友由金沙回來。見面后談及學校的艱難處境,克昌毅然為我承擔起護校工作,使我得以分身,在外求援解決校舍和經費問題。說到保護校具,談何容易。一方面,難民們的悲慘遭迂確實令人同情,其拆燒行為或亦出于無奈,但學校財產亦需保護,不容破壞。如何兩全,真是費盡心力。當時大學部的門窗課桌幾乎全被燒毀。惟獨附中部分,由于克昌夜以繼日地同難民反復交涉,又通過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協調,終于完整地保存了附中部的全部課桌凳及其它校具。為后來學校復課創造了條件。
我落實好樂群校舍后,他立即雇車雇工把全部校具,圖書,課桌凳運到樂群學校。并修繕教室,籌備招生復課。另外,他還把部分校具運到大學部留給附中的花溪校舍,準備以后高中部遷花溪時使用。又支援一部分校具給應屆畢業生籌辦伯群小學。他一直幫助我辦完招生并開學上課后才趕去赤水大學部報到上課。克昌對大夏中學的設立功不可沒。
大夏中學建立后,我常考慮,為作長遠計,需解決永久校舍的問題。
抗戰初期,原中央大學附中(后稱國立十四中學)在貴陽馬鞍山建有校舍,1945年抗戰勝利后,十四中隨中大遷回南京去了。所有的房地產,由貴州省政府撥給防空學校使用。該校的黃教育長與我相熟。在一次宴會上,我談到大夏中學的永久性校址尚未解決。他馬上告訴我:“我校現在使用的十四中校舍,是省政府劃撥的。我們不久就要搬走。你可以找關系去活動一下,請省政府劃撥給你們使用。”我知道這個內情后,趕緊去找楊森夫人汪德芬。我將這個情況告訴她,希望她能給主席談談,試探一下主席的口氣。汪很直爽的告訴我說:“用不著我去找主席。你先去準備一份申請劃撥原十四中校址給大夏中學的報告,在早晨八點以前去六廣門體育場,待主席打網球休息時面交給他,并說明情況,主席同你見過面,他是知道你的。”我按照她的指點回去準備了一份申請書,在次日早上8點鐘去到六廣門體育場。果見楊森主席正在打網球,趁他休息時,我立即去見他,說明來意。他接過申請,并未多問,就把申請交給他身邊的衛士。并說:“你將這份文件交給李秘書長,要他在星期五例會上提出。”又回頭告訴我:“此事要經省府例會通過,你在星期六看貴州日報就知道了。”楊森主席處事這樣爽快,令我大出意料之外。內心欣喜萬分。我隨即將此事向傅啟學廳長談了。他說:“主席是名譽董事長。由主席提出最好。”過了三天,已是星期六。我迫不及待的去買了份當天的貴州日報。只見頭條載有關于省府例會的報道。其中就有:“大夏中學請撥原十四中校舍使用一案已經例會討論通過。另行文交大夏中學。”我當時真是大喜過望。一直等到文件下達后,就立馬去看望防校黃教育長,向他表示感謝。黃又告訴我:“防校擬于1946年底遷走,待決定后我會通知你。”
1946年10月,黃教育長通知我,防校己決定于11月搬走。我隨即積積準備,并親赴馬鞍山校址查看學校設施。當時核實,學校占地約有三千多畝(不包括荒山),有辦公樓一座,教室14間,圖書館一座,還有一座能容納五百多人的大禮堂,以及男女生宿舍兩棟。還有一座飯廳(加廚房)以及抽水機房等。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校的硬件設施已基本齊備了。
(待續)
責任編輯: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