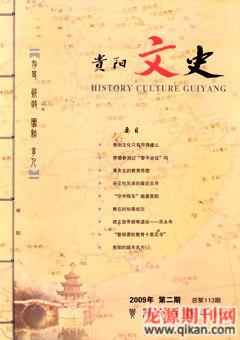上天入地董加耕
王明明
董加耕生于1940年,1961年高中畢業后,回到江蘇鹽城縣葛武公社務農,立志建設新農村,成為全國知識青年學習的榜樣和著名勞動模范。多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1999年4月16日下午,一場特殊的捐贈活動在鹽城市鹽都區圖書館舉行,捐贈者是一位戴著過時黑框眼鏡的老人,捐贈的是800多件獎章、證書、老照片等珍貴史料和文物,他一出現,現場便響起了雷鳴般掌聲。這位老人就是董加耕。
上世紀60年代,我國成千上萬青年高唱“學習董加耕,立志干革命”的歌曲,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上山下鄉洪流中,董加耕更激勵和影響了前蘇聯、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千百萬青年。時光流逝,當年那個“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腳踩污泥,心憂天下”的董加耕早已淡出人們視野,已過花甲的他近況如何?近日,記者在他的老家鹽城采訪了這個當年的風云人物。
放棄北大扛起犁耙
實際上,早在1961年,剛高中畢業的董加耕就應該“一飛沖天”了。在這之前,他是學校學生會主席、團支書,還被推薦入黨。那一年,他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學哲學系。脫離農村到城市上大學,是多少農村孩子夢寐以求的夙愿啊,更何況還是中國第一學府!但董加耕此時卻作出了一個驚人決定:放棄北大,回鄉務農,并將名字“董家庚”改為“董加耕”,意為加倍努力耕耘家鄉。在家人、老師、同學、社會的一片譴責和質疑聲中毅然扛起了犁耙。
完全出于當農民的一片赤誠,做夢都沒想出名的董加耕卻轉眼間成為叫響全國乃至世界的人物。1962年8月8日,《新華日報》以《目標始終如一》為題,率先報道了董加耕放棄北大回鄉務農的事跡。1964年初,共青團江蘇省委、中共江蘇省委先后發出學習宣傳董加耕的決定,隨后,《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紛紛發表文章和社論,充分肯定了董加耕的壯舉。其中《人民日報》指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就是毛澤東時代知識青年所應該走的路。”隨后,董必武、鄧小平、薄一波、彭真等也號召向董加耕學習。在耀眼的光環中,董加耕也由生產隊長躍為不脫產的共青團鹽城地委書記、全國人大代表、團中央委員等,一直坐到第三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和執行主席的位置上。
于是,在董加耕、邢燕子等那個時代著名知青的影響下,成千上萬知識青年投入到上山下鄉的歷史洪流中。
主席壽筵頭號客人
新中國成立那年,毛澤東56歲,從那時起到去世,毛澤東只給自己過過一次生日,那就是1964年的71歲生日。這一天,他用自己的稿酬張羅了3桌還算豐盛的壽筵。盡管是個特殊的日子,但毛澤東甚至沒有請自己的子女,而是將董加耕、邢燕子、陳永貴、王進喜這些當年的楷模列為貴客,并和自己同桌。40多年過去,董加耕回憶起當年的場景仍激動不已。那一年的12月26日,正值三屆全國人大召開會議,那天散會前,服務員通知董加耕、邢燕子、陳永貴、王進喜4人,會后就地稍等。待大會代表和其他主席團成員逐漸離去,周總理從后臺上來,走到主席臺后面的一個休息室,不一會又和朱德總司令帶領4人來到大會堂一個小宴會廳,宴會廳里呈“品”字形放了3張餐桌。稍后,毛主席在周總理的陪同下,容光煥發地來到宴會廳,這時大家才想起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主席坐定后,周總理把董加耕拉到主席的左邊,和主席膀子靠膀子坐在了一起。主席的右邊坐著邢燕子,同桌的還有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羅瑞卿等人。大家坐定后,毛主席說:“今天既不做生日,也不祝壽,而是用我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我的孩子沒讓來,他們不夠資格,今天不僅要吃飯,還要談話嘛!”主席首先問董加耕:“讀了幾年書?”董加耕回答說:“讀了12年,高中畢業。”主席說“好!”隨后,毛主席和董加耕從讀書看報紙談到鹽城的“二喬”(指胡喬木和喬冠華,兩人均是鹽城人——記者注),席間,主席不停地囑咐董加耕:“你是農村來的,要多吃菜。”
這次主席壽筵,董加耕被人稱為“主席壽筵上的頭號客人”,也被人視為董加耕光輝的政治頂點。1976年9月9日,一代偉人毛澤東為共和國走完了光輝的人生歷程,董加耕作為治喪委員會成員,被唯一特許在主席身邊守靈7天7夜!
五起五落榮辱不驚
董加耕沒有想到,在耀眼光環的背后,一場暴風雨正在襲來。1966年5月,董加耕當選為共青團鹽城地委書記,不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色風暴”席卷整個中國。剛剛上任的董加耕成為“造反派”們鎖定的目標,誣陷董加耕是劉少奇培養的“黑標兵”,縣里還成立了“董加耕問題聯絡站”,外面還有“五湖四海調查團”,董加耕也成為當時鹽城年齡最小、職務最高的“走資派”,而“造反派”給他網羅的罪名有100多條,編成了“反毛澤東思想100例”,“造反派”們不停地讓董加耕背“毛主席語錄”,終于有一天,董加耕背錯了一個字,給“造反派”們留下了把柄,將他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在深挖“5·16”分子運動中,董加耕再次受到沖擊,被稱為“鹽城地區‘5·16反革命陰謀集團頭子”,家中被抄,全家被隔離審查,他被監禁了27個月,跨了3個年頭!在這次審查中,董加耕被罰站了整整18個日日夜夜,小腿腫得發亮!
“文革”十年,董加耕被整了4次,羅列的罪名有“劉少奇的黑標兵”、“走資派”、“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等。“四人幫”被粉碎后,董加耕才在汪東興的過問下,回到鹽城任縣委副書記。而就在這時,董加耕又被人“盯”上了,在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時,他又因曾是“文革”中團中央籌備組負責人和曾經被江青“深夜召見”等原因,被隔離審查了13個月,直到1994年中共江蘇省委撤消了對他的錯誤結論,并重新任職。
總之在那個時代。只要運動一來,就有董加耕的“份”,但從不勝寒的高處跌落下來的董加耕依然很樂觀:“我還是那個董加耕。我沒問題,不怕整!”5次被整,3次關押,時間長達5年零8個月。1974年,周總理詢問董加耕在“深挖‘5·16”遭迫害的情形時,董加耕平淡地說“不能以錯對錯”,周總理禁不住夸道:“不愧是小董!”
患難夫妻相濡以沫
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董加耕始終以一種進取的姿態不斷前進,這與他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分不開。他與愛人郝鴻鸞是同鄉,結婚幾十年來,他倆相互尊重,互相體諒。
60年代初,國內宣傳董加耕到達高潮,他的事跡被越來越多人所熟知,董加耕,一個20歲剛出頭的小伙子,頓時成為
無數青年人心中的偶像,通過各種方式向他求愛的人也絡繹不絕。但和認準了棄學務農的道理一樣,在對待感情問題上,董加耕也相信自己認準的人。董加耕找對象的標準是傾向于能吃苦會干活的農村青年,但要有文化。這個時候,鄰村的一位姑娘進入了董加耕的視線,她就是郝鴻鸞。18歲的郝鴻鸞是小學教師、民兵教導員。但此時董加耕的母親認為郝鴻鸞是農村人,不太同意,而郝鴻鸞的父母認為董加耕不讀大學做農民,太傻,以后肯定會過苦日子。雖然兩人互有好感,但關系一直不敢公開,只是將心中最重要的位置給對方留著。那時,不僅在國內,越南、前蘇聯等國外女青年的求愛信也絡繹不絕,都被對郝鴻鸞忠心不二的董加耕“頂”了回去。1965年10月,董加耕劃著小船,拖著個大木箱,將郝鴻鸞迎娶回家,開始了兩人風風雨雨的人生。
即使在董加耕多次受審查期間,兩人的愛也從沒有過一絲動搖。在深挖“5·16”期間,董加耕被監禁起來,那時,郝鴻鸞正懷孕待產,董加耕在監獄中省吃儉用,將省下來的20斤糧票托人帶給妻子增加營養。而郝鴻鸞也不時帶著鴨蛋去探望小董。現在,董加耕和郝鴻鸞生活在鹽城市區純化路一幢普通的居民樓里,家中的設施也很陳舊簡單,有些家具甚至還是60年代購買的。董加耕告訴記者,他只想和老伴一起過平靜的日子,因為過去幾十年,他們經歷了太多的風雨起伏,有時感覺對不起郝鴻鸞。而郝阿姨對記者說:“這輩子嫁給老董,我不后悔……”
昔日楷模余熱正旺
董加耕對名利看得很淡。他曾從全國人大常委到一名普通農民,后來落實政策當上了公社副主任。董加耕開玩笑說“這相當于從副部級‘升到了副科級”。記者了解到,他2000年從鹽城市鹽都區政協副主席崗位退了下來,現在享受副處級待遇。有人跟董加耕開玩笑:“人家官越做越大,車子越坐越小,你怎么官越做小,車子卻越坐越大?”董加耕笑著說:“何為大,何為小,黨和人民最偉大。計較個人得失最渺小。”
由于董加耕是名人,多年來,來找董加耕做“形象代言人”的企業或個人絡繹不絕,還有人請他做銷售策劃,甚至還有人許諾重金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個公司,都被他婉言謝絕了。在政府分房時,按條件董加耕完全有資格分到一個最大的,但他卻要了一個最小的房子。這就是他的“大小”觀!
也正因為如此,董加耕至今還是不少人心中的榜樣和偶像。1998年,大豐市一位患了絕癥的病人專門寫信給董加耕,說自己從小就學習董加耕,榜樣幾十年不倒,很難得,在不長的人生中,想見董加耕一面,探討人生,感受榜樣的力量。
董加耕退休后,他自告奮勇擔當起鹽都區關工委副主任和老區扶貧開發促進會副主任,幾乎每天還在為青少年教育和老區人民脫貧致富忙碌。他仿佛還像一團火,依然煥發著青春的活力。
時隔幾十年,董加耕仍然初衷不改,經歷了大起大落的他思維清晰,談鋒甚健,豁達開朗。面對董加耕,透過他一副款式過時的黑邊眼鏡,記者可見其眉宇間充滿不斂的笑意,言談間時不時一串打油詩或順口溜,令人捧腹開懷,咀嚼有味。
“他好比今天的劉德華”
3月29日,重慶氣溫陡降。南山某知青山莊,氣氛熱烈,近百個來自重慶、成都、云南、上海的老知青在歡迎他們曾經的“偶像”——董加耕。
在一片掌聲中,董加耕在長桌圍成的一端坐下。他的身后五幅巨大的畫像,從左到右依次是,恩格斯、馬克思、毛澤東、斯大林、列寧。周圍墻上的玻璃壁框里,掛著無數的老照片,上面的年輕人英姿勃發,甚至。還掛有一面鮮艷的寫著字的紅旗。現場全都是些五十開外的人,他們手里幾乎都拿著一本書——《知青心中的周恩來》。董加耕是該書的作者之一。正是因為該書,這些來自天南海北,四十多年前分赴黃土地、黑土地、紅土地的半百之人聚在一起。
1961年,“董大哥”是江蘇鹽城縣龍岡中學的高三學生,還用著“董家庚”的名字。用現在的眼光看,當時的董家庚確有“偶像”的資格——一學生會主席、團支部書記、中共預備黨員,并獲得保送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資格。
更資格的是,董家庚畢業時決定不上大學,改名叫“董加耕”——意為加倍努力耕耘家鄉——回到家鄉葛武公社董伙大隊第四生產隊務農。
隨后的3年中,《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分別以社論、長篇人物通訊等形式報道董加耕的先進事跡。
“你知道的,當時,這就是最大的偶像,好比現在你們年輕人心中的劉德華。”坐在記者旁邊的一位女士說,“大學不上了,到農村搞了個大豐收:毛主席親自接見,扛著鋤頭的宣傳畫貼遍全中國。那個號召力和影響力不得了!”現場所有人都拿著書讓董加耕簽名并合影。閃光燈頻閃,無數的手在緊握,還有人大聲唱起了那個年代的革命歌曲……
“那時的農村窮死了”
請董大哥來重慶并不容易,之前,董加耕曾向本次活動組織者之一的潘正國表示:“可不可以不去?這么多年過去了,有些往事就不要提了。”
為此,潘正國和另一個組織者——當年云南兵團知青大返城請愿活動組織者丁惠民一再邀請:“董大哥。天下知青是一家。你來重慶,實際上就是參加一個全國知青的世紀大聯誼。”
最終董加耕在猶豫中答應了邀請。在和記者的交談中,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那時的農村窮死了”:
“我家當時在全村最窮。100多戶人的村莊里面,我們家是唯一的茅草房,吃飯有時候都成問題。1953年,我考鎮上的高小時,父親就不同意,為什么?我去讀書了,家里面就少了一個勞力,農活就少一個人做,少掙了公分,就更窮了。”
“上個世紀60年代初,全國都在經歷特大自然災害。一次。我母親不小心把能照得見人影的一碗米湯灑了,竟不顧一切地趴在地上,用舌頭舔了又舔。這些讓我揪心不已。我既然讀了高中,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就有責任用自己學到的知識,改變家鄉的面貌。”
說起當年自愿回農村當農民的激情,董加耕滔滔不絕。在那個年代,一名新中國培養的高中畢業生,應該算是非常稀罕的“高級知識分子”了。
“我是一支鹽蒿”
與很多中國人的命運一樣,在文革期間,董加耕也遭遇過紅衛兵審查和批斗,“最惱火的一次,被罰站八天八夜,腿腫得有茶瓶那么粗”。最長的一次審查,持續期長達3年,回家后,他竟然不知道自己走之后出生的小孩是男是女。
審查結束后,在周恩來總理的過問關心下,他當過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大會執行主席,第九屆團中央委員,第十屆團中央籌備組副組長,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
“那些事,都過去了了。”董加耕擺擺手說,“現在回過頭去看,我認為那是對我的考驗。有的人比我的遭遇還慘,比我的命運還要跌宕。有什么呢?都過去了。反正,我還是那句話,青春萬歲,無怨無悔!”
“對那段歲月你沒有一點感觸?”記者追問。董加耕沉默著想了想,拿起筆在記者的采訪本上寫下這樣一段話:我是一支鹽蒿——一種生長在黃海灘涂邊生命力極強的灌木植物,漲潮時淹得要死,退潮時干得要死。最終沒有死。逢到雨水豐盛,會長得更旺盛。
寫完后,董加耕反問記者,“你是怎么看那段歷史的呢?”沒等記者回答,他自言自語地說,“漲潮退潮都是要死,可我有理想,沒死成。現在好多了。我這么老了不是還在為農村做事情嗎?”
“這就是理想的延續”
幾十年前,因為各種各樣的背景,幾千萬知青懷著激情和理想來到農村,灑下汗水,甚至鮮血和生命。直到1979年,絕大部分知識青年回到城市。
然而,30年后,2008年,中組部等有關部門聯合發布的一份文件再次引發世人關注:從今年開始,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為新農村建設培養骨干力量。
“這就是我當年理想的延續。”對這項決定,董加耕想了想說:“中國農村從來都缺少有知識的青年,當年我不讀大學回家務農,也就是想用自己的文化知識改變鄉村的貧困面貌。現在,中國廣大農村仍需要有知識有理性的青年去改變,特別是西部地區。”
他表示,現在的知識青年下農村,還是應抱有“當時我們下鄉時的理想和熱情,真正對農民、農村有著深厚的感情。不是去鍍金,也不是去觀光,而是踏踏實實地改變落后的面貌。這既是物質的改變,更是用自己的知識改變農村農民的精神面貌”。
不過,他對現在的農村有些擔憂:以前的農村鄉情淳樸,但農民的生活非常苦;現在,農民不用擔心溫飽問題,但是更多的人都盯著錢。年輕一代普遍缺乏當時知青那種樂于奉獻、吃苦耐勞的精神。“孝悌”二字也不那么神圣,“有些人,連孝順父母都不知道了”。
記者要離開的時候,董加耕撫著自己花白的頭發。似乎陷入沉思:“作為老知青,不管如何評價過去的歷史,但我一直記著一句話——青春萬歲。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但任何時代都需要英雄,需要溫家寶總理說的仰望星空的人!”
責任編輯:王師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