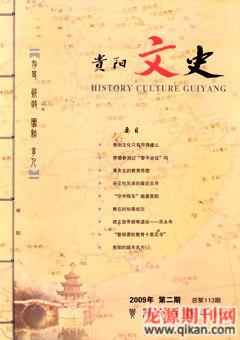走出來的作品
周 靜
有人說王大衛的作品是走出來的,恐怕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他52歲就從仕途上走了出來;二是他在《天地無極》和《尋找那些靈魂》寫作過程中分別深入到云南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并流區域和云貴烏蒙山區徒步尋訪的時間竟達一年之久。
云南報業集團《大觀周刊》總編輯楊鴻雁在采訪王大衛時說:“我覺得你的內心世界是非常復雜、非常豐盈的,如洛桑益世活佛所說,‘蘊含的東西太豐富了”。
A、走出紅塵
王大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就從我退休后談起吧,那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王大衛2000年新世紀伊始提前退休。比法定退休時間提前8年,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早在青年時代,他就有了一個夢想、一個做寫作者(作家)的夢想。但他的選擇,并沒以他的意志為轉移,他最后被命運顛簸到了仕途上。既然走上仕途,他也認命了,在仕途上認認真真、盡心盡力。然而經歷了十多年仕途生活后,他越來越覺得不適應仕途生活,先是萌生退意,繼而果斷做出抉擇。于是,他于2000年毅然離開了生活十多年的“圍城”。同年,他對自己10多年的仕途生活做了個總結一出版了《追趕生命》。這是他的第一本書。而王大衛認為,“比這本書更重要的是身心自由了、輕松了、清靜了,有屬于自己的空間了,可以有時間有精力有條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也許是“天音”成全他,從2001年到2008年這七、八年間,他先后出版、再版了4本書。第4本書出版時,正好是他的“法定”退休時間。王大衛說,“這一天,我心泰神寧,甚至洋溢著一種喜悅感;我為8年前那個明智、果斷的選擇做了一個深長的禱告。”
王大衛在《追趕生命》里說:“我的人生在路上,天堂也在路上。”所以,他要堅執去尋找他的天堂。他的第二本書,就叫《尋找天堂》。
外表平靜內心熾熱的王大衛究竟要尋找什么樣的“天堂”呢?他說:我寫作,很大程度上只是完成一個內心的使命,了一個夙愿。因此,他對題材選擇十分審慎,甚至尋尋覓覓、風雨兼程去尋找。他說:“我尋找、選擇的題材,必須是對人類歷史、文化、教育、精神等領域有杰出貢獻的人物,簡言之,就是對人類文明有杰出貢獻的人物。人類文明需要志愿者、需要有使命感的人共同去構建、推動。”
王大衛認為,寫作是一種與讀者的知識、思想、心靈交流,既然是一種交流,就應當把真善美的信息、思想及其理念傳達給讀者。他說:“好的作品是對人類文明的啟迪和助推。好的作品就像是在幽暗巷道里點亮的一盞明燈。”也許是認真讀了王大衛的書稿,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國際納西學學會會長白庚勝親自為王大衛的《天地無極》寫了數千字的序言“與天堂同在”。
我在采訪王大衛前,閱讀過他的三本書,每一本書,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乃至令我產生一個巨大的疑問:王大衛怎么從未獲過獎?
王大衛大概看出我的疑問,平靜地說:“我不獲獎是正常的,獲獎反而不正常了。首先,是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決定的;其次,我從未送作品去參加評獎;其三,我的作品不僅是非主流的,而且內涵了所謂‘敏感思想。”
出于某種意念,記者問王大衛:面對社會生活,有什么感慨?近期還有何寫作計劃?
王大衛沉默一會后說:我用心理和精神“元素”,構建了一個屬于我自己的、遠離塵世的生態環境,一個屬于我自己的精神家園。心態平靜了,情緒亦平靜下來。于是我又開始尋找題材。我想尋找一條江、一個人的歷史來反映大歷史大社會,抑或說,讓一條江、一個人來見證一段歷史一段社會命運。目前,我正在收集相關資料,天氣好些后,就會出行。我認為,好的作品,是行走、體驗、感動的結果,是文學、思想與理論綜合的結果。純粹的文學寫作,完全形象思維的寫作,很難出有深度有生命力的作品。
王大衛是我所采訪的“影響力人物”中唯一沒有獲得過任何獎項的作家,但這并不妨礙他的《尋找那些靈魂》和《天地無極》成為央視電視片的文本,也不妨礙他的圖書在北京、上海、浙江、云南、深圳、香港等地區有不少的讀者。在北京王府井書店、北京國際書店乃至在麗江飛機場侯機廳和海拔4000多米高的玉龍雪山景區休息大廳,都有王大衛的《尋找天堂》和《天地無極》。
王大衛應該感到欣慰,社會也應該感到欣慰。
B、生命之旅
2001年8月,《追趕生命》出版后,王大衛想休息幾天,于是,去了云南麗江。在麗江,他看見很多書店里,都有關于美籍奧地利植物學家、探險家、學者約瑟夫·洛克的圖書,便買了幾本,比如《沿著洛克的足跡走進香格里拉》、《孤獨之旅》、《馬蹄踏出的輝煌》、《靈魂居住的地方》等。每天下午和晚上,他都在古城“談世樂”客棧里閱讀這些圖書,尤其是在閱讀了洛克的《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后,他感動了,決定沿著洛克半個多世紀前行走的主要線路,深入到云南滇西北三江并流區域去。他想去發現、挖掘一些更動人、更深刻、更鮮為人知的東西,同時,以一種獨異的形態、獨異的理念來表達他認為是“深刻”的東西。
基于這一思考,王大衛在新世紀到來之際,便先后五次去了云南,總計行程數千公里,歷時近一年。除了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及其流域。還遠行到了與緬甸、西藏接壤的獨龍族人聚居地區——獨龍江流域的龍元,繡切和孔嘎。
這是一次體驗式苦旅。王大衛不僅對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區歷史、文化、自然生態進行了深入考察。對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納西族、彝族、藏族、傈僳族、普米族、獨龍族、怒族等民族的歷史文化、生活習俗、民族風情,也進行了深入采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大衛對納西族、傈僳族、獨龍族、怒族人的未來命運,投入了深摯的關切。除了對這些民族做了縝密體察之外,還為這些民族的未來發展做了思考。對生態環境的潛伏危機,王大衛也在憂慮的同時,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當他在勐臘南貢山和南臘河流域的納卓、勐伴、曼蚌看到大片的樹林被砍伐、燒毀時,竟發出了“不是恐懼大自然,而是恐懼人類自己的愚昧與野蠻”的仰天嘆惜。
在云南時,云南美術出版社旅游編輯部主任張曉源對王大衛說:“不要再拿生命去跑了,多少人為此耗盡了一生積蓄,有的甚至一去就走上了不歸路……”
王大衛說,他聽了張曉源的勸告后,眼睛濕漉漉的。他感謝張曉源,感謝他的肺腑之言。但他回答張曉源:“我的生命在路上,我的‘天堂亦在路上;離開思考、離開行走,我會感到虛空,像天邊的流星。瞬間即逝。”
兩年后,王大衛的《尋找天堂》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了,出版社給了他9%的高版稅。出版社的評語是:這是一本圖文并
茂、風格獨異、洞察深刻的記述云南滇西北歷史與地域文化的精致之作,優雅的描寫與理性的思索,令人賞心悅目、深長思之。
2005年,香港文匯出版社出版了《尋找天堂》修訂版《天地無極》(上下集,繁體版)。2006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又買斷版權在內地出版了簡體版《天地無極》。
《天地無極》(繁體版)在香港印制時,王大衛又風塵仆仆、跋山涉水去云貴烏蒙山區了。他又物色到一個具有史詩般意義的題材:一個近百年前在云貴烏蒙山區創建“文化圣地”的英國傳教士塞繆爾·柏格理。柏格理1887年3月到中國,在中國西部云南和貴州貧困地區艱苦卓絕地生活、工作了28年,1915年9月,因救助貴州威寧石門患傷寒的苗、彝族學生,溘然長逝在那片巷涼、貧瘠的土上,年僅51歲。柏格理先后在滇、黔毗鄰的昭通、彝良、威寧等地區傳教、辦學、辦醫院歷時28年。
其實,記述洛克、柏格理的圖書已出過不少,但王大衛說,他想用紀實、文學與學術交糅、整合的樣式來寫,以紀實散文為主要體例。
資料、提綱以及確認文體等準備工作完成后,他毅然拖著他那條患有股骨頭缺血性壞死的右腿,往中水、石門、彝良、昭通等地區去了。去烏蒙山區采訪、考察,與去云南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和獨龍江流域采訪、考察一樣,不僅異常艱苦,而且充滿了危險。
當我問王大衛,為什么偏偏要選擇到這樣遙遠、蒼涼的地方去?王大衛說:“我對柏格理、對那段發生在近百年前以石門為中心的文化現象的追尋,完全是基于兩個感動:為柏格理和他的同事的獻身精神感動;為含辛茹苦深入到石門和烏蒙山區去考察的中外學者感動。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他們的精神品質和生命意義,已遠超越了物化世界”。
因為這兩個感動,王大衛在50多歲的年齡段,數次深入到那片交織著貧困、苦難和神秘的高寒山區去。每次回到貴陽家里,都是心力交瘁、疲憊不堪。
也許是被王大衛的精神所感動,也許是被王大衛書稿中記錄的那段令人欲泣的歷史所感動,香港文匯出版社在出版了上下兩冊的繁體版《中國石門》后,又跟進出版了簡體版《尋找那些靈魂》。
為了寫作《天地無極》和《尋找那此靈魂》,王大衛先后在滇西北、黔西北高山大河、荒原草澤上步履蹣跚地苦行了近兩年時間。王大衛說,“其間苦樂悲歡,只有我與同行者體悟、心悟最深。這兩次追尋,這兩次生死之旅,使我對洛克、柏格理以及人類精神和人類生命意義的認識,產生了一個飛躍性的思考,乃至演進為有明確價值取向的生命之旅。”
C、天道酬勤
令王大衛“稍感欣慰”的是,他的苦旅是有結果的。他自信地認為,“每一個看了這幾本書尤其是看了《天地無極》和《尋找那些靈魂》的讀者,都會與我行走和寫作時的感覺一樣,激情、溫馨、感動地體會到審美、情感和思想的顫動。”
王大衛的自信,獲得了積極反應:
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國際納西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白庚勝在讀了《天地無極》后寫道:毫不夸張地講,作者對納西族歷史及現實的透視是空前的;作者讓我們享受了太多的雄奇: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獨龍江的風雨陽光;玉龍雪山、格聶神山、梅里雪山有靈性的生命;甘孜高原與天空是“親密融和在一起的,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觸摸到天空”;理塘的天空,“既純凈又溫柔且強烈,純凈是像藍眼睛一樣清澈的蒼穹,溫柔是飄逸的云影,強烈是太陽的光芒”……《天地無極》是我至今所見到的記述洛克、記述納西民族、記述三江流域自然與文化的不朽佳作。(《天地無極》序)
貴州省文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何光渝在讀了《天地無極》后,感慨地寫道:王大衛踽踽獨行于滇西北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并流區域納西、傈僳、獨龍、藏、彝、怒等民族世代棲息之地。這一自費進行的備嘗艱辛的旅程,歷時四年:行走、求證、核實、寫作,再行走、再求證、再核實、再寫作——單是玉龍雪山下一個小小的雪嵩村,就先后去了五次!
顯然,大衛并不僅僅只是喜歡或滿足于“在路上”的感覺。若不是全身心地去行走、追尋,這書里那些出自心靈、坦率真誠的文字、并非人云亦云的感觸和識見,怎么可能產生?怎么可能在質樸生動的文字描述和豐富傳神的圖像表現中,記錄、再現出如此豐富而真實的歷史和現實生活場景?這樣的寫作,是對歷史文化的搶救,是對民族文化的生動保存,明顯地帶有“史志”性的意義,具有非常的文化歷史價值。在這部感覺是一氣呵成的長篇紀實散文中,雖不能說是篇篇“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卻也是才情洋溢,筆墨揮灑著知行與智性。我從其間讀到的,不僅是牠的文筆、文飾、文采,更還有他的文情、文氣、文理,他的精神人格的積淀,文化旨趣的能指所指,以及對人生哲理的不舍探求。(2006年2月10日《貴州日報》)
貴州大學中文系教授黃俊杰在《憂患于天地之間的“思想織物”——評王大衛的長篇紀實游記(天地無極)》(《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03期)中說:《天地無極》敘寫如行云流水既靈巧又自然,更重要的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情境撞擊生發出多少隨緣、隨觀、隨感、隨思、隨想的心靈火花,有如不同色彩的橫線來回穿梭于這塊思想織物之上,讓讀者看到了“一片淡淡的微光已經照亮了這張思想織物的背景,它的另一端則還深鎖在濃云密霧之中”。《天地無極》以其精致的“思想織物”反作用于“本事”,讓讀者思考著“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在緩慢地改變著思想顏色的偉大運動在不遠的將來仍將會繼續么?在時間十分活躍的織布機上命運之神將在這塊織品上織出何等顏色呢?是白的?還是紅的?”——我們一時還說不上來。但在全球化語境下的憂患意識,卻充分地顯示了一位知識分子作家所擁有的時下愈益難能可貴的正直品格。
貴州民族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教研室主任喻健(子涵)教授,讀了王大衛的《天地無極》和《尋找那些靈魂》后寫到:王大衛紀實散文的詩性,是由他的“行走”而產生的。“行走”意味著“尋找”,尋找一種靈魂、一種精神、一種價值、一種信念、一種理想,這“行走”與“尋找”的本身,就充滿著強烈的詩意的壯舉。他的行走是沿著一條歷史的路徑進行的,《天地無極》是沿著美國學者洛克半個世紀前在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區生活與工作28年的歷程線索進行的。《尋找那些靈魂》是沿著英國傳教士柏格理近百年前在云貴烏蒙山區創建中國西南“文化圣地”的足跡進行的。大衛的行走是極其艱難的,但是由于心存博大的愛心,于是將艱難化為了愉悅,化為了力量。在王大衛看來,人的一生是行走的一生,“人類文明之旅,既涵蓋了痛苦涵蓋了希望也涵蓋了幸福。”他的“行走”是為了“尋找”,因此,“行走”與“尋找”,便構成了王大衛紀實散文創作的核心內容,而這種核心內容正是一種詩性精神的呈現,在自然與人的關系中,他堅信自己尋找到了一個關于生命、精神與靈魂的豐富世界。正因為有這種人文精神的支撐,所以才有苦旅與寫作的強大力量。王大衛的紀實散文也是“神圣憂思錄”,也是“大山的呼喚”,通過考察、體驗,他為文明的衰落、生態的破壞和苦難的蔓延而痛心疾首。這種體驗與思考是深刻的,這種痛心與呼喚是真誠的,作家的良知與責任不由自主地涌流出來,而其詩性也奔涌于文字,直通心靈,直逼事物的本質。(2008年4月25日《貴州日報》、2008年第8期《民族文學》)
《尋找天堂》、《天地無極》出版后,《光明日報》、《西部開發報》、《云南日報》、《民族時報》、《春城晚報》、《貴州日報》、《貴陽日報》等多家報紙及時予以了報道,并發表了相關評論文章。云南報業集團《大觀周刊》總編輯楊鴻雁對王大衛做了長篇專訪(《天地無極》訪談:關于《天地無極》的對話)。中央電視臺“發現之旅”擬定了2009年攝制紀錄片計劃。
《中國石門》(繁體版)和修訂版《尋找那些靈魂》出版后,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和香港電視臺分別做了專題片和紀錄片。
行走、閱讀、思考與寫作,已是王大衛追求的一種生命形式。我們祝福王大衛及其作品。一路好走。
(作者單位:貴州日報)
責任編輯:羅萬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