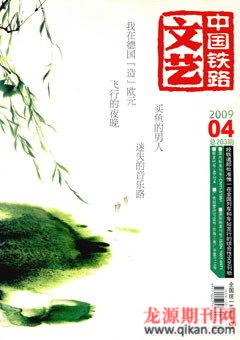春天的聲音
李 曉
早春二月,我行走在都江堰、汶川、北川、綿竹……我想在這個春天的源頭,俯下身子,屏住呼吸,來傾聽災區生長的聲音。
不管你是在千里之外,萬里之遙,你肯定會在這個春天,讓眺望的目光迢迢而來,關注祖國西南部這些崇山峻嶺,這些廢墟上的活動板房。這些大地上結痂愈合的傷口。聽啊,整齊的目光仿佛都有聲音了,在空中花瓣一樣飄舞,羽毛一樣翻飛,帶著初春的暖意,輕輕的就把祝福送達。
在方圓數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上,數百萬災區人民,剛剛度過了這樣一個永生難忘的春節。過年了,他們首先要面對的,是要在心理上過關,在心理上艱難地翻過一道坎兒。從全國各地趕來的人,也守候在這片土地上,與他們一同迎來了這陣痛之后的第一個春天。
當我仰頭望見活動板房上那一盞一盞在風中輕揚的紅燈籠,感受著空氣中哧哧撲騰的年味兒,我以為,我是回到了自己老家的村子。如果不使勁揉揉眼,我不會從這眼前這披紅掛綠的熱鬧場景中清醒過來,那一瞬間的山崩地裂,為這里命名為“災區”。
我接連走進活動板房的人家,以一個游子的身份回到他們中間去。香腸、臘肉、年畫、艷麗的羌服、紅辣椒、孩子的書包、老人的拐杖……這些生活中的道具,正悄悄返回到他們日常生活的軌道上來了。我以風一般的敏感,捕捉他們每一個人臉上的神情。眉頭是舒展的,目光是溫暖的,笑容是明朗的,語氣是感恩的。我細細傾聽山野中彌漫的聲音,正讓這個涅槃的春天涉水翻山而來。
我來到北川一戶活動板房里的人家。去年5月的那天,有兩家人,無聲無息走了7口人。一個男人的家,妻子、兒子、母親、舅舅走了。一個女人的家,丈夫、公婆、姨娘走了,留下了在學校廢墟中逃生的女兒。春節前夕,他和她組成了一個家庭。在北川,這樣的家庭正在春天到來之前,咬著嘴唇開始了艱難的重組。她的女兒仍叫他“叔”,孩子一直把父親的照片放在貼身的衣服里。他把兒子的照片放在床柜旁偶爾望一眼,她把離去丈夫的照片放在枕下偶爾流下淚。十多年的日日夜夜啊,要想把一個人扎在心里的根痛痛快快地拔出來,還是太難了。春節時,這重新組合成的一家人。去半山遺址向廢墟的北川縣城默默燃香祭拜。肅穆的空氣中,蒼涼的北川縣城沒有一絲聲音,它在一片廢墟里睡去了。
回來的路上,16歲的女兒在廢墟旁,看到一束在風中搖搖擺擺的野花,她快樂地奔向那花,把花從泥土里輕輕拔起,捧到胸前,輕輕地嗅著那花香。女兒把花捧到一家人面前。讓他們一一聞聞那花香。剛才還是一臉沉重的男人笑了,說:“呀,這花好香!”她把花捧在懷里,突然朝著他輕輕叫了一聲:“爸!”男子一下淚流滿面。
晚上,我和他們一家人閑聊著,那女人捋額前的發,她用清脆的聲音告訴我:“你知道吧,我們的胡總書記已經為新縣城取名永昌了!”說這話的時候,我看見了她眸子里閃動著亮光。她的母親,一位80多歲的老人,也在一遍一遍回憶,大年三十那天。老人踮起腳,在涌動的人群中看到了來北川過年的溫家寶總理。老人反復比劃著手說,哎,你看總理多和善,他一直沖我們笑瞇瞇地點頭吶!
在一場慰問演出中,我看見了那個在地震中截去一條腿的北川女孩,她那么優雅地站立著向父老鄉親們表演獨舞。我想走在北川一處山崖上見到的一棵樹,樹根已經在那驚天的一震中爆裂出來,然而,這棵斷裂的樹,朝另一端昂起頭,又再次落地生根了。在這個初春,它已經有了泛青的嫩芽。
這不是整個災區的最好縮影嗎?一棵樹,這片土地上的人,他們以再生的姿勢,讓你感受這處處涌動的、撲面而來的春之氣息,正匯成春天的合唱,在廢墟上迎來一個山花爛漫的季節,一個新家園的藍圖,也已經在濕潤和帶著土地咸腥味的風中,浮現出美好的輪廓。
離開那片土地的時候,正傳來一個嬰兒嘹亮的啼哭聲。這是北川一個唐姓人家,在這個初春迎來的新生命,他被改名為唐川曦。這個新生命到來的啼哭聲,讓我也真真切切聽到了災區萬物生長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