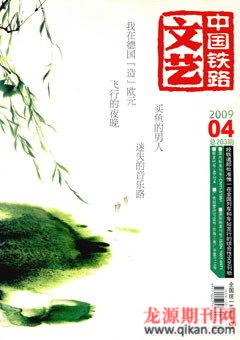漁鼓聲聲里
肖景兒
當夜幕降下所有的黑,男人們就著暮色中幽藍的光線收拾粗細家伙,拖著疲憊的身子紛紛回到家中,這時,女人則將已預備好了的晚飯端上飯桌。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王家村大多數農家餐桌的內容基本一致:一大盤紅薯,兩三碟咸榨菜,每人手里一碗蕎麥或玉米粥。家境寬裕的男人隔三差五需要一小杯米酒來填補心思,一盅下肚,迷迷瞪瞪,待到女人收拾完余下的家務活,便摟抱了女人,捻燈睡去。
在遠處的狗吠聲漸漸平息后,鄉村便都歸寂于靜,耳旁除了男人的鼾聲,便是墻角、陰溝、樹權間、田野里隱隱約約的蟲鳴。只是王家村有個例外,每個月圓的晚上,倘若你睡眠淺些,心思再細膩一點,便可聽見從村西口的那間木板房內,傳來凄婉的漁鼓聲。那種凄婉,哀怨悠長,劃過夜空,直抵達人的心坎。倘若你任憑心思跟了那調子婉轉而去,定會勾出你許多淚水。
油菜花,金燦燦,
今日個夜(ya)里把妹念
未開言,淚漣漣。
思緒千千萬。
柔腸寸寸斷
……
王家村的人都知道,唱歌的是曾家二叔,一個拒絕所有媒婆上門提親的單身漢。我離開故鄉已經整整二十八年了,曾家二叔的模樣在我的記憶中已經非常模糊了。然而,他那凄婉的漁鼓聲,一直縈繞在心頭,惹得我生命沿途的憂傷馬不停蹄,反反復復。
我與妹妹難成對呀,我冒得錢財,你爺(ya)娘何該會(怎么會)將你配
我與妹妹難成雙呀,我冒得房子,你爺(ya)娘只把我往屋外面趕
我與妹妹難成婚呀,你爺(ya)娘狠心拆散鴛鴦兩地分
……
記憶中的許多月圓之夜,總是那樣伴一腔哀怨的漁鼓,在奶奶沉重的嘆息中度過。曾家二叔口中的妹妹叫胡七妹。按輩分。我應該叫她姑姑,雖然不是本家,但同是一村人,多少有點沾親帶故,所以,平日里,我們喚她為“七姑”。七姑的母親,我叫她“二奶奶”。聽村里的奶奶們說過,“二奶奶”好吃懶做,出了名的嫌貧愛富。
七姑是個瘦小且沉默寡言的姑娘。農家女孩長得黑,偏又貧窮,七姑那瘦小的身子終日被套在寬大的青衣粗布里,經常辛勞于田間活計,塵土滿面。聽小姑姑說過,七姑僅僅那么一件沒補丁的衣服,還是她們一起上山挖山藥掙下來的錢買的。不過,七姑有雙丹鳳眼,長長的睫毛又濃又密。我的記憶里,七姑的笑容燦爛得跟陽光一樣明媚。
曾家兩兄弟無父無母,曾二叔跟著哥哥相依為命,兩兄弟都生得濃眉闊口,白白凈凈。那時候的我,不過是五、六歲的小姑娘,不會評價也不會欣賞男孩的英俊與丑陋,只知道曾家兩位叔叔的模樣逗人喜愛,又加上平日里最喜歡聽曾二叔吊上一段漁鼓調,因此更覺曾二叔比別人親切些。然而,令我惑解的是,曾二叔那雙幽幽的眸子中總藏著無限的憂愁,那癡癡的神情里,總流露著無盡的惆悵。漁鼓的唱腔本來就是張口便有,詞的編排沒有嚴格的章法,也許是因為曾二叔的歌聲中揉進了那些哀怨纏綿的情調,才格外動人心弦。
記得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乘著大人們各自忙碌,我們一群孩子玩捉迷藏。玩伴冬梅悄悄地告訴我,公家牛棚的頂上堆了許多新收的稻草,是個躲藏的好地方,我便跟在冬梅的后面悄悄地爬上了牛棚里新搭建的草架。為了藏得隱秘一些,我倆一塊兒縮在一個狹小的角落里,我瘦些,蹲在里面,無法看見外面發生的事,只得用耳朵去捉摸各種聲音。不一會兒,就聽見有腳步聲進了牛棚,窸窸窣窣。起先,我認為是找我們的伙伴,于是趕緊平心靜氣,片刻之后,感覺不對勁,因為除了有奇怪的急促喘息聲,還伴著很輕很輕的呼喚聲,極度壓抑,聽不很真切。同時,緊挨著我的冬梅全身跟篩糠一樣顫抖,她的右手開始使勁抓住我胳膊,直到抓得我生痛。最后,我在無法忍耐的情況下,奮力一掙,硬生生地把冬梅從牛棚的架空頂上擠了下去。也就是那一刻,我清晰地看見兩個全裸的大人相擁在一起。一個是曾二叔,一個是七姑!那當兒,曾二叔迅速地將一件藍色外衣裹住七姑的身子抱在懷里,蹲進草堆,爾后驚恐地看著我們這兩個小姑娘。
后面怎么收場的,除了七姑那美麗的胴體、豐滿的雙乳印在我的腦海里之外,剩下的那些記憶現在已經非常模糊了。只記得后來幾天,每次碰到七姑,我總情不自禁地多看幾眼,因為我簡直無法相信那件寬大的粗布藍衣里會裝著個那么美麗的軀體。這件事過去不到三個月,一天,挨近吃中飯的時候。胡家來了三個陌生人,把三張貼滿錢的報紙很自豪地鋪在胡家飯堂里的那張八仙桌上。我從來沒見過那么多錢,趕緊跑近去看。擺在最上面的,貼的全是拾元,第二張全是伍元。最下面一張貼的是壹元和貳元的。我驚訝的目光全部在那些錢上。拾元的鈔票那么多呀!我見都很少見,那還是春節父親回家過年。在他的手里見過那么幾回。我很是羨慕七姑的娘,她布滿笑容的臉上煥發出淡淡的紅暈,七姑的爺(ya)一個人悶悶地坐在灶膛前抽著旱煙,一臉的陰沉。
我弄不明白這三個陌生人為什么要送給胡家這么多錢?轉頭聽他們談話,還是沒明白緣由,他們講的都是平時很少用的客套話。直到奶奶喊我回家吃飯,我才戀戀不舍地離開胡家。吃飯時,我不停地跟奶奶說胡家那些錢的事。奶奶一個勁地搖頭嘆息:“咯雜老耄親(這個老太婆),真要這樣活生生拆散兒女!哎!這樣做,害人也害己呀!”
見奶奶那樣嘆息,我更是疑惑,忍不住反復追問奶奶為什么胡家有人給送錢?可奶奶很不高興地呵斥我:“小姑娘家不可以總關心這種事,趕快吃飯吧,別磨磨蹭蹭。”
幾天后,來了一隊敲鑼打鼓的迎親隊伍,他們抬走了被五花大綁在一張竹椅上的七姑,后面跟隨著貼滿紅喜字的籮筐和小板車。
自此,每個月圓之夜,都能聽到村西頭曾二叔在自己破舊的木屋里哼著悲傷的漁鼓。
記得那日妹要嫁,堂前聘禮堆成山
記得那日妹遠嫁,一溜嫁妝光鮮鮮
妹妹呀,你哀怨成冢淚流干
聲聲來把哥來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