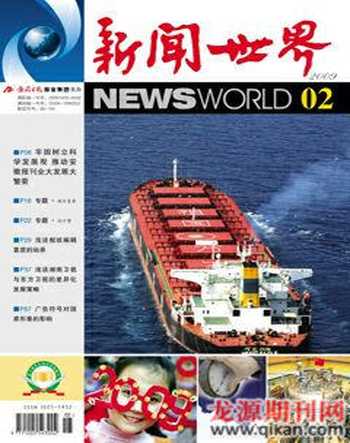網絡媒體的傳播優勢和局限
劉文章
【關鍵詞】網絡媒體 優勢和局限
因為有了互聯網,世界越來越像麥克盧漢預言的“地球村”。網絡媒體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個突出產物。它實現了傳統媒體的電子融合,涵蓋了傳統的文字、圖片、影像和聲音傳播的特點和優勢,統一了過去各自獨立的傳播形式,最大化地滿足網民的視聽需要。相對于報紙、廣播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網絡媒體一般也被稱為“第四媒體”。網絡媒體改變了既有的傳媒格局,關于網絡媒體取代傳統媒體的言論一直不絕于耳。
網絡技術的優勢帶來了信息傳播和公眾交流的新的可能性,也塑造了網絡媒體公共性的特征。網絡的“公共性”一直是學者研究網絡媒體的熱點。技術樂觀主義代表美國學者托夫勒就認為,生活在網絡時代的公民可以借助網絡就公共問題直接向政府發表意見或投票表決。他對網絡媒體的公共性功能充滿自信和贊譽。他的觀點得到了NBC新聞前總裁勞倫斯·格羅斯曼的回應。格羅斯曼說,技術和信息公路孕育了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
網絡媒體果真像以上描述的那樣有這么強大的力量嗎?
網絡媒體的技術優勢與不足
網絡媒體是互聯網上的主角之一。新媒體技術使網絡媒體形成了不同于傳統媒體的傳播特征:
首先,網絡媒體突破了報紙版面的局限和廣播電視的時段限制,可以大容量地傳播新聞信息,使公眾知曉信息的數量和選擇信息的范圍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第二,網絡媒體突破了傳統線性時間觀念的束縛,一方面可以以直播的方式,同步報道新聞事件,沒有時間的滯后和間隔;另一方面,網民可以在事后任意時間重新閱讀當時的新聞,回顧當時場景,重回歷史現場。
第三,網絡媒體突破了傳播空間的地理劃分,不受地域的限制,只要鍵入網名,一般來說就可以找到這個網站。比如,輸入英國BBC的英文網站名,就可進入BBC網站,就能同步收聽BBC的英文節目。傳統媒體目前無法實現無限制的跨地域傳播,因為地域隔離而造成傳播隔離的現象仍然相當普遍。
第四,網絡媒體突破了單向線性傳播的模式,趨向于網狀的多向傳播。傳統媒體主要是線性傳播,傳播的路線是從媒體到受眾,受眾處于接受者的角色。網絡媒體技術改變了這種僵硬的傳播模式,不僅網民與媒體之間真正實現了雙向傳播,而且網民之間也可互相傳輸信息,構成了傳播的網狀結構。
面對網絡的這種傳播優勢,默多克進行了冷靜分析。他認為,新的傳播技術在賦于表達和交流以新的可能性的同時,也設置了新的限制和新的社會隔離。互聯網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所有人是否都能夠進入互聯網,是否所有人都能獲得這些新技術提供的服務。而現實是,互聯網要受到年齡、文化程度的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受眾對新設備和新節目的支付能力。
據2008年1月發布的《第2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我國網民盡管數字過2億,但只占全國總人數的16%。網絡傳播提供的公共話語空間還很有限。
網絡媒體實現
公共領域功能的可能性
20世紀60年代,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最后一位批判理論家,德國大學者哈貝馬斯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開創性地提出了“公共領域”的概念。哈貝馬斯認為:國家和社會之間可以存在一個公共空間,市民們假定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言論,不受國家的干涉,這便是公共領域。他認為,公共領域是大眾傳媒運作的空間之一,大眾傳媒自身就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大眾傳媒實行公共領域的功能也是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重要途徑。按照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中國網絡媒體具備了提供公共領域功能的可能性,表現為:
第一,由交互技術帶來的網絡交流形式,使網民能夠就某一個話題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文字的公開性使開展網上文字辯論和參與討論成為可能。哈貝馬斯在分析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型時認為,公共領域因為遭受國家和社會力量的介入,導致公共輿論不再真正是公眾討論后的共識,而成為了大眾傳媒操縱的結果,只代表少數人意見。網絡媒體的交互傳播技術因為改變了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模式,每個人都能站出來代表自己發表意見,因而也就能有效避免觀點被媒體劫持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網絡媒體就像勞倫斯·格羅斯曼所描述的,其民主性很強。
第二,提供了討論的場所。網絡媒體設立了新聞評論區、網絡論壇和虛擬社區等電子區域,為網民的討論提供專門的平臺。網上社區“天涯”就是中國一個著名的網上討論區域,至2007年底,注冊用戶近2000萬。社區內討論議題由網民來掌握和主導,有意愿參與評論的網民可隨時發貼。“天涯”社區已吸引到了不少有思想、愛發表意見的網民,這些人愿意時不時對當下的新聞和社會現實發表見解,因此天涯網民的代表觀點也常常成為新聞從業人員參考的一種民間聲音,經常被直接引用到報紙和雜志上。
第三,網絡空間的開放性保證了每個網民都有機會參與討論,討論的參與者地位和機會平等。那些在社會現實中很少有話語表達權利和機會的人群,在網絡空間尋找到了表達的出口。他們通過網絡交流、建立博客、播客等方式,傳播他們的社會立場和生活感想。
第四,能夠形成網絡輿論,按照哈貝馬斯的分析,在公共領域中討論者獨立于市場力量和科層機制之外,具有思考的主體性,因而討論具有批判性,批判性的結果就是能形成公共輿論,表達公眾的聲音。近年的網絡媒體傳播實踐表明,中國的網絡輿論已顯現了強大力量。2003年,網絡媒體強烈關注孫志剛案件,廣泛傳播《天堂里沒有暫住證——紀念孫志剛君》等文章,引起網民積極參與討論,最后在網上形成了強大的輿論聲勢,一邊倒地對實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抨擊,導致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關注和應對網絡輿論,并最終終止了上述的這個《辦法》。
中國網絡媒體的這些特征,體現了網絡媒體實現公共領域功能的可能性,但并不是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全部。
網絡媒體實現公共領域功能的局限性
就像任何新興技術均有其兩面性一樣,網絡技術在幫助網絡媒體實現公共領域功能的可能性的同時,也埋下了設置局限的種子,這些局限表現為:
第一,網絡討論很少能夠形成最后的一致意見,網民很少達成共識。沒有共識和統一的網絡輿論就不能在政治領域有實踐的意義。2003年孫志剛案件,網絡輿論意見高度一致,才導致一項政策的終結,但這種現象在網絡媒體中極為罕見。多數情況是網民們意見不一,沒有最后的統一認識,無法合力形成凝聚多數人力量的網絡輿論,也就不構成對政府的壓力和推動力。按照哈貝馬斯的分析,處于公共領域內的公眾,無論是在古代的廣場上,還是在近代的咖啡館里,開展的是一種面對面的交流。只有這種形式的交流,才能引起辯論的深入,最后才能有一個聲音勝出成為代表意見。而網絡媒體提供的恰恰不是面對面交流。
第二,網民雖然是平等地開展討論,但因為他們的身份無法確定,他們的意見可能隨時改變,無法用身份來保障意見的有效性,導致彼此之間無法真正地認同。網民觀點的易變性,也對統一的網絡輿論的形成造成障礙。即使網民以視頻的方式討論,卻也只能確定討論者的形象,無法確認身份,而且,視頻方式目前還無法提供網民大規模同時參與討論。
以上兩點的局限是由網絡交互技術的特點所直接決定的,是網絡媒體的先天性不足。
第三,網民話語空間過于分散,導致話語沖擊力不強。網絡媒體把過去集中、同質的大眾化傳播內容細分到各種欄目、社區和頻道之中,網民根據愛好、城市位置、政治傾向、文化品味分散地聚集在被細分后的領域中。他們因為某些共同的相似性走到一起,后來的加入者的觀點表現更多的是對前面觀點的認同和贊成,結果就缺乏不同觀點的針鋒相對,因而缺乏批判的力度和討論的建設性。此外,因為網民分散聚集,話語的影響力也僅限于該討論部落,使得公共話語和公眾輿論被瑣碎化,喪失了成為網絡輿論的機會。
另一方面,網絡媒體自身盡管有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但因為政策的限制,沒有刊登自己采寫新聞的機會,無法用觀點吸引網民,沒有媒體立場。
第四,代表國家力量的政府和代表商業力量的市場全面滲入中國的網絡媒體。政府對網絡媒體實施監管是全球的普遍作法。在我國,在經歷了2003年網絡輿論的風起云涌后,在目睹到網絡媒體中商業資本力量的橫沖直撞后,政府監管選擇了同管理傳統媒體一樣的政府主導模式。政府以監管的形式介入了網絡媒體,并把政府宣傳的任務也交給網絡媒體。行政力量的滲透,一方面可以積極引導輿論,另一方面對網民參與討論的公共空間也構成了干預。
國外媒體的現實告訴我們,網絡媒體正迅速地屈從于已經控制了商業傳統媒體的商業力量。中國網絡媒體的市場化正在加劇。不管是由私人資本建立的完全商業化的網絡媒體,比如新浪、搜狐,還是由政府主辦、出資的網絡媒體,比如人民網、新華網,都在不同程度地經歷市場的挑戰。商業力量對網絡媒體公共空間的侵襲,使得公共空間失去了運作的獨立性,并且使網絡媒體不再把網民當作參與討論的公眾,而是當作了消費者。這種現象最有力的例證就是商業網絡媒體傳播不再根據受眾的需要(need)展開,而是按照受眾的需求(want)而進行。網民就像俄國評論家米哈伊·巴赫金所描述的,人性中隱性的一面被揭示并體現出來。受流量和廣告影響的網絡媒體需要網民的高點擊率,很快體察到了網民的這種“隱性的一面”,他們只需看看哪些新聞和信息的流量較大就可判斷。正鑒于此,暴力、挑逗甚至色情等吸引眼球的內容充斥著商業網絡媒體的網頁。
默多克在分析西方公共廣播機構的市場化時認為,以廣告為代表的商業主義和消費主義話語已對公共話語造成了侵蝕,在公共話語空間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媒體主導的這種商業和市場關系將公共利益等同于消費權,扼殺了對公共事業的其它可能的想象,媒體的受眾由公民轉變成為消費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商業網絡媒體只是在吸引和發布商業廣告的同時,推出一系列“副產品”,比如說博客、虛擬社區,這些產品以“公共空間”為外衣,讓公眾誤以為他們從中獲得了更多的話語表達機會和更大的言論自由。
在網民和網絡媒體的力量對比中,作為網絡輿論載體的網民處于較弱的位置,他們的言論可被網站刪除,他們的討論空間可被網站關閉,而且,他們還得忍受網絡空間中越來越多的商業話語。政府的傳聲筒和市場的賺錢機器,這是當代中國網絡媒體的雙重角色,也是對它們最恰當的形容。網絡媒體無法完全實現公共領域的功能。■
(作者單位:新安晚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