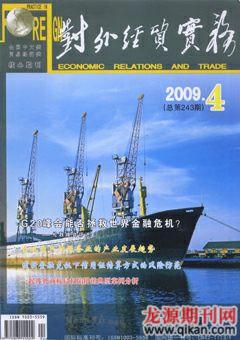一則案例下FOB若干問題的思考
婁 鈺
一、案件回顧
我國某省興貿進出口有限公司于2006年5月15日與新加坡某公司簽訂了一出口精銅管合同,其中價格術語為FOB,裝運港為青島港,目的港為新加坡。興貿公司7月15日向船公司訂艙,7月20日自費報關將貨物裝上船,7月21日船舶由青島港啟航。同日,興貿進出口有限公司向船公司傳真去了提單補充材料,并要求船公司出具提單。在7月23日,興貿進出口有限公司突然收到船公司的傳真,船方告知興貿進出口有限公司,海洋運費及港口所有費用新加坡公司已經出具,并且新加坡公司已經告知船公司它不轉賣此批貨物,要求貨到目的港后船公司電放提單。興貿進出口有限公司強烈抗議,船公司不予置理。8月3日船公司通知其在新加坡的代理電放貨物。由于興貿進出口有限公司向新加坡方追索貨款未果,遂于9月初向青島海事法院起訴船公司,要求其承擔由此帶來的一切損失。
二、案例引發的問題
該案后雖經法庭調解雙方達成和解協議,船公司承認其做法不妥,由船公司賠償興貿公司部分損失,但值得思考的問題很多,其意義遠遠超過案件的本身。
其一,在國際貿易中,買賣雙方到底誰應該為托運人?在FOB情況下,船方到底該把提單簽署給何方當事人?另外,國際貿易發展委員會于2008年6月通過了《聯合國全程或部分海上國際貨物運輸合同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Contract of International Carriage Wholly or Partly by Sea)草案,該草案對提單的簽署問題做了明確規定,雖然要各國批準此公約尚需時日,但賣方在新公約草案下該如何控制物權也是實務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二,什么是電放提單?在什么情況下船公司簽發電放提單?電放的操作程序是什么?電放提單的法律性質是什么?它和一般的紙質提單有和什么區別?電放提單有無相關的法律或慣例來規制它?這些問題都是實務界亟需了解的。
三、對問題的思考
(一)公約草案下只有買方才可以成為托運人
在本案中,雖然船公司承認其向買方電放提單做法有些不妥并賠償了賣方部分損失,但是承運人根據與他簽訂運輸合同的對象把買方作為托運人并向其電放貨物,承運人的做法事實上并無不妥。眾所周知,目前規范提單的國際公約有三個,即1924年的《海牙規則》、1968年的《威斯比規則》和1978年的《漢堡規則》。在《海牙規則》和《威斯比規則》中,雖然多次出現托運人用語,并為其設置了諸如提單請求權等多項權利,但都沒有明確界定托運人的定義,更沒有指出托運人的類型,至于承運人應把簽發簽署給賣方還是買方,其規定是不明確的。
據此,在FOB條件下,如果提單簽發給賣方,且賣方為提單持有人,則賣方可以是托運人;如果簽發給訂艙或租船的買方,且買方取得提單持有人身份,則買方也可為托運人。這種規定不利于對賣方利益的保護,如果賣方的提單不到,他就可能失去物權,他的買賣合同下的獲得貨款的權益就得不到保護。為了保護賣方的權益,《漢堡規則》對托運人下了明確的定義,即托運人是指由其本人或以其名義或代其與承運人訂立海上貨物運輸契約的任何人,或是由其本人或以其名義或代其將海上貨物運輸契約所載貨物實際提交承運人的任何人。它把托運人分為兩類,即與承運人訂立運輸合同的人(契約托運人)和將貨物實際交付給承運人運輸的人(實際托運人)。
在FOB條件下,買方屬于第一類承運人(契約托運人),賣方則屬于第二類托運人(實際托運人)。這種界定雖然明確把賣方劃歸為托運人,意圖在客觀上保護FOB下賣方的利益,但是在提單的持有權上卻造成了混亂,承運人到底該把提單交給哪個托運人,公約并沒有明確的界定。我國《海商法》秉承了《漢堡規則》的規定,但是仍然沒有解決提單的簽署對象問題,我國《海商法》在第72條第1款《海商法》規定:貨物由承運人接收或者裝船后,應托運人的要求,承運人應當簽發提單托運人。此規定雖然明確指出承運人應簽署提單給托運人,但到底簽署給哪個承運人并沒有明確規定。而在國際貿易實踐中,在FOB條件下買賣雙方為了各自的利益都愿意控制物權,都會向承運人提出索要提單的申請,這就造成了承運人困惑,從而也就造成了提單簽署對象的混亂。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案中的船公司把貨物電放給進口方并非完全沒有法律依據,只是法律規定并不太明確。興貿公司的租船訂單行為屬于代理性質,屬于實際托運人,進口方支付運費和港口費用,屬于契約托運人,在現有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承運人該把提單簽署給何人的情況下,船公司電放貨物給新加坡公司并沒有任何過錯。
為了解決因《漢堡規則》設置兩種托運人而引發的FOB下提單簽發問題,在2008年6月國際貿易發展委員會通過了《聯合國全程或部分海上國際貨物運輸合同公約》(草案),此公約把托運人定義為與承運人訂立運輸合同的人,而把貨物交給承運人的人,公約稱其為交貨人。運輸公約草案的第37條規定:承運人或履約方接受貨物后,( )交貨人有權從承運人處取得證明承運人或履約方接收貨物的運輸單證或電子記錄;( )托運人有權從承運人處取得可轉讓的運輸單證。如果在公約草案的法律框架下再審視本案的話,興貿公司為交貨人,新加坡公司為托運人。興貿公司有權獲得貨物收據,新加坡公司有權獲得提單。船方把貨物電放給了新加坡公司就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既然現在的運輸公約草案明確規定了在FOB條件下船方應把提單簽署給買方,那么作為出口方該如何操作才能規避提單風險呢?如果仔細閱讀運輸公約草案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公約草案對賣方的利益還是有所考慮的,它增加了一個“單證托運人”的概念,它在第1條第(10)項規定:“單證托運人”是指除托運人外,同意在運輸單證或電子運輸記錄中被指定為托運人的人。據此,如果賣方想得到提單,可以設法使自己成為單證托運人。根據多年的國際貿易實踐經驗,筆者認為如果興貿公司想規避公約草案下的風險,可以采取以下具體措施:
1.在合同中訂明提單收貨人抬頭為憑興貿公司或開證行指示轉讓,這樣提單背書轉讓的權力就保留在興貿公司或者開證銀行的手中,對方不付款或者不承兌很難得到興貿公司或開證行的背書,從而無法僅憑正本提單去辦理提貨手續。當然,如果興貿公司對開證行有懷疑的話,可以與新加坡公司在在合同中訂明提單收貨人抬頭僅憑它的指示。
2.在合同中訂明提單簽發給興貿公司。買方指定的承運人應為它可接受的船公司,如果買方堅持指定境外貨代,興貿公司應在合同中訂明境外貨代的提單必須經商務部批準的貨運代理企業簽發。這樣興貿公司就可以避免船方與買方串通來欺詐自己,從而順利掌握提單物權。
3.可在合同中訂明由興貿公司自己租船訂艙,并在收貨人一欄,把自己列為托運人,但運費和其他費用由買方支付,這樣興貿公司和承運人之間就存在一個運輸契約,承運人理所當然地要把提單簽發給它。或許有人會對此種做法提出質疑,懷疑這種操作辦法是否與《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的規定相背離,其實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2000年通則只是國際貿易慣例,國際貿易慣例按照其法律性質,當事人是可以選擇適用的,也可以在雙方當事人意思一致的情況下對其規定做一定修改和添加。
4.興貿公司最好要求買方在信用證項下支付貨款。在采用信用證支付方式時,通知行有嚴格審查開證行資信的義務,如果開證行誠實可信,則可以預防開證行和申請人一起聯合欺詐的情況發生。這樣在興貿公司提交的單據符合信用證及其相關慣例的情況下,開證行就會向賣方支付信用證下的款項,從而保證貨款的及時回收。
5.另外,在匯付和托收支付方式下,興貿公司也可結合國際保理或出口信用保險來規避提單下的風險。
(二)電放提單是海運提單使用的一種特殊情形
本案中船公司通知其在新加坡的代理電放了貨物,實際上電放提單屬于使用海運提單的特使情形。電放是指承運人根據托運人的申請,在托運人向承運人提交保函的情況下,承運人以電訊的方式通知其在目的港的代理,貨物無需憑正本提單即可放貨,收貨人只憑蓋有收貨人公司章的電放通知單,換取小提單即可結關提貨的一種放貨方式。
一般情況下,發貨人是通過銀行提交提單或由發貨人直接將提單寄給收貨人,由于提單是貨物所有權的憑證,因此收貨人只有拿到正本提單后才可以提貨。但在近洋運輸中,由于船期短,如果通過銀行或郵寄提單,就可能出現貨已到港而提單卻還未到的情況,為不影響及時提貨,收貨人會要求發貨人將提單電傳、傳真或E-mail到發貨人,收貨人不需要正本提單,貨物到港后憑提單傳真件就可以提貨。因此所謂電放就是憑電子的、電傳的或傳真件放行的意思。事實上,電放貨物海運提單是使用的一種特殊情形,屬于無單放貨。本案中,船方就是根據新加坡公司的申請,并由新加坡公司出具保函后,通知其在新加坡的代理電放貨物的。
根據貿易實踐,船方辦理電放的程序是這樣的。在辦理提單電放時,托運人應先與船公司聯系,通知其提單需要電放。這時船公司會要求托運人出具一份保函,保證由電放引起的一切責任由托運人承擔,然后托運人需要向船方繳納100~200元不等的電放費,這樣船公司就可以通過電訊指示目的港的代理機構憑提單傳真件放貨。在實踐中,電放手續最好是承運人在未出具提單前辦理;如果承運人已經出具正本提單,則托運人需要將全套的正本提單交回船公司,然后船公司才會辦理電放提單的手續。由于電放后發貨人將不再掌握貨權,電放對賣方而言容易造成錢貨兩空的局面。雖然電放對發貨人而言風險巨大,但在近海貿易中由于往往出現貨到單未到的情況,故在現代國際貿易中電放單的運用還是常見的。
雖然電放提單解決了“貨到提單未到”的問題,但電放提單在法律上的地位卻是十分尷尬的。按我國《海商法》規定,提單應當具有三項功能: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承運人接收貨物的憑證和目的港交貨憑證。電放提單卻并不完全具備以上三項功能,電放提單是由收貨人憑提單的傳真件提貨,它本身并不是承運人據以交付貨物的依據,它不具有物權憑證功能,也不具有可轉讓性,雖然“電放提單”也是在托運人要求下由承運人簽發的,其簽發時間跟傳統提單是一致的。“電放提單” 本身不是合同,它的的存在僅能夠證明托運人與承運人之間存在著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起一種運輸合同證明作用,由此可見,電放提單和紙質提單有著本質的區別,它并不完全具有紙質提單的全部功能。
至于電放提單的法律規制,目前仍然是法律的盲點。我國法院在審理電放貨物案件時,基本上都是按照民法的基本原則,把其歸結為船方無單放貨,無單放貨者要承擔侵權責任。由于目前電放單的使用越來越廣,這種審理辦法是否妥切有待商榷。我國及國際上應及時出臺相關的法律制度來規制電放提單問題。
在目前未有相關立法的情況下,筆者建議有關當事人在適用電放時應慎之又慎,在近海不得不使用電放時,賣方應要求買方出具銀行保函,或者在合同中規定如果需要電放提單的話,須經賣方同意并向船方申請,否則就可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本案中如果興貿公司在與新加坡公司簽署的合同中,如果加入相關條款,并把合同的副本提示給船方的話,就會避免船方電放貨物給新加坡公司以致于貨款不能收回的風險。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此案例引發的問題遠遠超過案件的本身,如果對此案件審慎思考,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對我國的國際貿易實踐是大有裨益的。▲